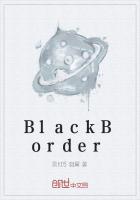“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好!”一曲四座皆惊,噼噼啪啪掌声一片,叫好声云起。一位满身绫罗绸缎的公子恐怕是喝的多了,满面通红,“砰”地捶响玛瑙圆桌,晃得那酒盏当场摔了个“狗啃泥”,脑浆四溅。
她低垂粉颈惶然地盯着地板——虽说不敢奢望那轮江波中的皎月,但也不愿瞧着那一金碧辉煌。可惜她还是看见了地毯——鲜红得似乎能流出腥味来。
“王大人,您还真厉害,坐享如此佳人,怎么不敬献给圣上呢?”一客半调侃半认真地问,手里依然握着一杯酒,“祝您——寿比南山、财源滚滚啊!”
王道钦纵声狂笑,让她想起自己在家门口见到的一只乌鸦:“哈哈,老兄啊!难不成连你都不理解王某?”说着与客碰杯,一口酒猛灌下去,“圣上后宫粉黛三千,哪有闲暇顾及这贫贱之女?我看这妞儿弱不禁风地,可别被娘娘们弄坏了才是。”言罢,一席皆大笑。
王道钦圆桶般的身躯兴奋得发抖,只见他信手从玉盘中抓出一把铜板子来,掷到她跟前:“今天老子心情不错,特意赏你的,拿去吧!希望你不负恩典!”
“晃当晃当”的铜板一落地,她就能感到火辣辣的目光如千军万马般袭来,吓得她不敢抬头看。酸涩的泪水在眼眶中滴溜溜地打着,她紧咬双唇,弯下腰去捡起那堆铜板,顿觉如芒刺手。
几个贪眼福的客人盯住她不停地看,直到她弓着腰疾步退入大厅一侧的红帷幔为止。
直到夜色惨淡,一切才冷清下来。
她愤然褪下大红金丝莲裙,换上一身旧得泛白的粗布衣衫。木盆里的水浑浑地沾满了厚重的胭脂色,隐隐绰绰显现出一张晃荡的、叠满皱纹的脸庞。施丽无声地叹了口气——唉,她应该不会这么丑吧,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佳人”之称?
正当她呆呆出神之际,倏听得耳旁一声雷响:“狐媚子!哼,磨磨蹭蹭地,当你是西施啊!”施丽转头一看,原是那个满身肥肉的“母夜叉”,那副狗仗人势的样子让她心里一阵不爽,眼神里不由得充满了怨毒。
“给我快点!呸,还有人呢!”幸得“母夜叉”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物,只是习惯性地瞪了她一眼,接着便像捧宝贝似的捧起那华丽的衣衫,甩开帷幔出去了,彻底消失前还不厌其烦地丢出一句:“给我快点!”
施丽白了一眼帷幔,才接着拔下头上的坠珠碧玉簪,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到一个红木盒里。随后,她又扯出一节灰头绳,细细地在偏右侧处编了一个小发花。处理完毕后,便毫不犹豫地掀开另一处的布帘走出了更衣室。
她步入了一条昏暗的走廊硬邦邦的布料拖着她沉重的步子,在地面磨出撕哑的、亢长的叫喊。走廊里像阴间地府般寒冷,只有一架老态龙钟的烛灯勉强亮着,如一簇将息将灭的鬼火,正幽冥冥地指示她走向那熟悉的门口。“若是将此处喻为地狱的通道,那是再妙不过的了。”暗暗想着,她便已走到了门口两位看守大人的威容前。那两个看守虎背熊腰、身材魁梧,凶神恶煞地各掌着一把巨斧镇守门前,那副神态还真像极了那青面獠牙的厉鬼,恶狠狠地瞪着她。“一个夜叉配两个厉鬼,真是妙极了。”她冷冷地掏出木质令牌,塞到其中一人手中。看守像进了水的机器人一般打开了那扇生了锈的铁门,放她走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小得似乎连巴掌都容不下。天花板死皮赖脸地粘着一块又一块的灰尘。墙是由纯天然的岩石砌成,墙面就像老人的脸,坑坑洼洼地满是时光划出的沟槽,虽然有几处已禁受不住苍老凹陷了下去,但大体上还是安然无恙,并且身后还有好几堵“扶持”着,所以整堵墙依然顽强地屹立着,很坚固,很结实,唯一的洞口便是一扇半开的小窗,中间横着栏杆。地板也是纯天然的岩石构造,坎坷不平地如穷家子弟的仕途之路。一张铺着薄薄的一层被单的木床放在窗口下紧靠墙角,但还是几乎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整个房间虽小、虽破败,但却整洁干净(天花板除外),显然住的是女性,并且住了三个。
施丽径直走到破旧的木床前,怕弄散架,轻轻坐下。坐在她身旁的于落桐淡淡地问候了一句:“回来了。”
蹲在一旁的闫清抬起头问,“赏钱有没有?拿出来玩玩。”
施丽一歪嘴,狠狠地扯了一下袖子:“哼,你怎么整天都以为天底下会有这等美事?更衣的时候就连着衣服一起还回去了!”
于落桐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大哈欠,蜷在床上睡去了。
三人都沉默无语,空气一时间有点冷。
闫清终是好动,只见她站起来爬上床去,床上重量突然大增,吓得木板“吱——”地一声大叫。
“吵死了!能不能轻点……”于落桐有气无力地怒斥道。
“我,我,我,已经最轻了……”
于落桐没有吭声,“吱嘎吱嘎”地一个转身,面对着墙睡去了。
闫清战战兢兢地悄悄瞟了一眼施丽,见她脸上并无怒容,心里不禁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见她慢腾腾地站起来,努力踮起脚尖,将下颚费力地支撑在窗台上,整个身体顿时拉得长长的。
“看到什么啦?”施丽见闫清的脸几乎都要对着天花板了,觉得怪有趣的。
“……看到了烛光……一点……我们对面原来有一支蜡烛耶,你看那火苗摆呀摆呀摆地,好可爱哟……哎呀!不好!没事了,风过了……哎呀我得下来了,疼死我了。”说着闫清后退了些,将头低了下来,不停地揉着她发红的脖子,“哎呀,那石头真是粗死了。”
施丽叹了口气,也爬上床来,把闫清按倒在于落桐身旁:“好啦,都睡一会儿吧,几个时辰后便又要干活了。”说罢吹熄了身旁的烛灯,四周立即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慵懒的清晨,空气又湿又重。天空里似乎装的都是水,只要轻轻捏一下,就能挤出一大堆来。密雨如针,细细地织起了层层银幕。起伏的人声掺和着哗啦哗啦的脆响,显得尤为扑朔迷离。小街上的青砖像疏于厨艺的厨师切的菜,参差不齐、大小不一,还坎坷不平。远处的一点红色,原是一面迎风招展的酒旗,如今被雨水打得耷拉下来,硕大的一个“酒”字被叠得不成形状。
一位身着布衣的年轻少妇,撑着一把圆伞的胳膊挎着一个装满物品的竹篮,另一只胳膊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女婴,慢腾腾地走着,娇柔的身躯已经累得娇喘连连。
不行,受不了了!于是练薇儿转向一处酒楼走去。
由于是下雨天,店里早已是人满为患。练薇儿叹了口气,离开酒楼,又向旁边的一个茶馆走去。可惜一进门,却又是生意兴隆,塞满了避雨的人。
练薇儿已经累得不想再换地方了,于是走到掌柜面前,娇声问道:“请问店家,您还有位子么?”
那掌柜见是一个如画美人伫于眼前,早已是魂醉骨酥,明明满员了却还傻乎乎地应和着:“有!有!当然有啦!”说着走到一位衣着粗简的客人面前使了个刀子般的眼色,意为“赶紧滚蛋!”
练薇儿不禁脸色一沉,对掌柜道:“算了,不用了。”说着便转身欲走,急得掌柜连忙劝阻:“啊,没事没事!区区一个乞丐而已,小姐不必在意!”
练薇儿冷道:“如此说来,此店是没位了。”说罢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看着练薇儿眨眼间便消失了,掌柜后悔不已。唉,自己也真是笨,这么漂亮的一个妞儿就这样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可惜呀……
练薇儿起先还凭着一时的怒气硬是撑着走了一段路,但渐渐地酸麻感越积越多,最终她还是索性蹲在地上,把篮子放在膝头,腾出一只胳膊来抱婴儿,舒展那只疲惫不堪的胳膊。低头看婴儿,只见她胖嘟嘟地、牛奶般光嫩洁白的小脸蛋泛起粉红,可爱极了,一双眼睛微微闭合着,睡得正香。
什么时候,她也该为小女起个好听的名字了。
不过她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再找一个歇脚的地方。
于是她站起身来,却忽然感到腿上酸酸地一阵抽搐,“哎哟”一声,又不得不再次蹲下来。
正当她无可奈何之时,只听得背后忽然传来一句清朗的话音:“小姐,您需要帮忙么?”
练薇儿愕然回首,原是一位身披牙色长袍的俊美男子,眉间一点红瓣,打着一把硕大的荷叶遮雨,正微微含笑凝望着她。“是否需要我搀扶一下?”他的目光如朝阳般和煦暖人。
练薇儿最讨厌多管闲事的人,但男子和善的面容却丝毫不使人厌恶,反而使人倍感温暖;况且她如今也的确需要帮助,便成全了此人的一番好意,允许他将自己拉了起来。
“小姐您要去哪?”
练薇儿如实道:“走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
“如今下雨天的,恐怕各处店铺都满员了。”
“可不是么?”练薇儿苦涩一笑——这让她想起刚才的情景来,“算啦,谢谢您啦,我随便找个台阶歇歇便是。”
白袍男子双眼盯着前方略一沉思,忽然眼前一亮:“没事,您跟我来吧。”
练薇儿望着白袍男子飘扬的长袍,忽然发现袍底有一块殷虹的印迹醒目地呈现在自己眼前。
白袍男子领着练薇儿来到一处茶馆门前。
推门一看,只见茶馆古朴醇厚地颇有韵味,就只可惜人还是太多,但偏偏且还留有一个空位。白袍男子往后一瞅,见练薇儿身后也有一人要步入茶馆,便身影“呼”地一闪,还没等练薇儿反应过来便坐到了位子上。练薇儿不解地看着他,只见他向店小二摆手吆喝道:“来杯铁观音!”
店小二急匆匆地应和着赶到,见了白袍男子,脸上略显惊奇之色:“客官,您刚才不是已经来过了么?”
“来过了来过了。”白袍男子一面不耐烦地应付店小二,一面笑吟吟地起身离座,向练薇儿道,“您可以上座了。”
店小二满脸惊愕地看着满脸惊愕的练薇儿迟缓地坐到藤椅上:“谢——谢——您——啊……”她将声音扯得很长很长很长……
“没什么没什么,一点小帮助不足挂齿——这铁观音多贵啊?”
“不贵不贵,三十个铜板子,不贵。”店小二这才反应过来,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
白袍男子和练薇儿都不约而同地瞟了一眼那只小得‘比芝麻还小’的杯口,又瞪了一眼店小二。
店小二满面通红,忙讨好道;“二,二,二十五……”
白袍男子冷笑道:“哼,谁要你的二十五,十个来三杯!”说罢,便将手探入袖中取钱,却被练薇儿一把拦住:“您不必啦,让我出吧!”
谁知白袍男子却不依不饶:“不用您出了,您可得省着钱养孩子呢!”说罢不由分说地取出了三十个铜板塞给店小二,“行了,钱也拿了,你可以走了。”
店小二忙知趣地退下了。
白袍男子也不给练薇儿答话的时间,便朝她莞尔一笑:“您好好歇息一会儿吧,我先走了。”说罢,足下一轻,还没等练薇儿说个“谢”字,便飘悠悠一阵白风似的刮得无隐无踪了,只留下身后的一阵叹息。
练薇儿伸出两根葱指,夹住一个陶土茶杯,轻轻抿了口茶。她的手虽干过不少活儿,但不仅丝毫无损它的美感,反而更使其具备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她的手是一种浑然天成的、不加修饰的美,就像这陶土杯里赭色的清茶,散发出朴实醇厚的芳香。她也并不否认自己的手可以比得上深宫中的后妃,心底下还想着:“小女的手如今还是胖墩墩一节一节地呢,不知何时才能比我长得还好看呢?”想着想着,禁不住低头瞧了瞧怀中沉睡的婴儿,望着那如嫩藕般的小手,感到一股暖流浸入心底。
忽然,店外一袭黑衣缓缓飘入——犹如寒冬腊月的冷风。那硕大如翅的黑袍轻软的半悬空中,铺天盖地之势显得尤为可怖;袍领遮住了男子大半张脸,高耸的发冠孤傲地立在头顶。
四周一片冷冷的死寂,冷得几乎要掉出冰块来。
“滴!”——屋檐上的一滴水滴落在地,迸出了刺耳的响声。
耸的袍领转过头来,环顾四周,练薇儿恰巧看见了那雕塑般过于精致而缺乏情感的五官,当然还有一双锋利无比的剑眉和寒光闪闪的瞳孔,看上去终是有了活人之感。
莫子千云淡风轻的一乜反而唬得众人大气都不敢出,生怕那乌黑的袖口里会倏然放出几枚暗器来。只觉得心生憎恶,嘴角微微勾起,顿时一阵凌厉黑风刮到掌柜鼻子尖:
“把你们店里的所有茶都给我上一遍。”
“这……”掌柜先是犹豫了一下。
“你就照做是了。”莫子千一双眼睛钢刀般的逼视。简直就是一“客官”变成了“坐堂大人”。
“好好好,全上、全上……”
练薇儿毫不掩饰地圆睁双眼,此人如此嚣张的气焰着实令她惊怒交集!只可惜自己也只有无可奈何干坐的份了。
莫子千一回头,便恰好被练薇儿“烧着”。
练薇儿见了,急忙垂下眼帘。眼角余光瞥见那一抹修长的黑缓缓飘到自己这边来……
莫子千在众目睽睽之下,泰然自若地站到桌子的另一侧,嘴角勾起一丝诡异的笑。
“完了完了,不知道上辈子干了什么坏事,竟被贼人要挟!”练薇儿只感到眼前天昏地暗、走投无路,勉强咽了口口水,道:“你要……”
莫子千冷冷道:“放心,你只需把你手中的那张红纸给我就行了。”
练薇儿一惊——自己手上怎么会有“红纸”?!
莫子千示意她找找袖子。于是练薇儿将袖子掀开一脚角——
一片圆形的大红色薄纸正正地扣在她手腕上,过于鲜艳醒目的颜色似乎是满纸的血。
练薇儿不知从何而来的一阵惊惧,纸片那么一抖,荡荡悠悠落下,正巧落到莫子千的手心里。
“很好。”那雕塑般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血色,轻轻的一笑,使目光也柔和了许多。此时一杯杯茶像赶集似的陆续接了来,俨然一个茶铺。莫子千不耐烦地给小二甩出足足一锭银元,然后,掏出一包鲜艳的绸缎,三根剑指递给练薇儿:“把里面的事物泡到茶里,再把茶叶拿出来,可成为包治百病的良药。“
练薇儿嘴角抽搐地接下,只见那绸缎光亮洁白如同晴天雪色,还透着缕缕清香,”哼,也不知是什么骗人的,不过……还是留着吧……“正自思忖间,眼前那修长的身影却早已消失了。最近果然时运不顺呐……
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见三个看似身手不凡的壮年男子忽然间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店门,甩开店小二,直向掌柜扑去。有两个稍微健壮的人想拦住他们:“喂!喂!你们……”可话还未说完便被其中一个心不在焉地各踹了一脚,当场像离弦的箭般射了出去,“哎哟!”一声双双被踹到了墙上,脸上的线条疼得紧紧地扭在一起。这一下子众人都着了慌,茶馆里的人群顿时就像被点着了火的蚁窝一般迅速溃散,开始向门口挤去。练薇儿抱紧婴儿,也顾不得竹篮和伞了,一心要随着人流逃出,却见门口的人都停滞不前。正惊疑间,忽听得门外一声虎喝:“把里面的人全都堵住了!一个都不能漏!一个都别想逃!”命令一下,便有两三个身手不凡的同伙气势汹汹地守在了门口。众人陆续知趣地退至墙角,脸上皆神色惶恐,心里定是直叫“千刀杀”。
练薇儿怀中紧紧抱着婴儿,贴在墙角直发抖,一面悄悄探出头来看。只见几个暴徒(可以这么称呼)摩拳擦掌地逼近白发苍苍的老掌柜,恨不得马上将其撕个粉碎。
掌柜早已被吓得面如土色,两只手像被风猛刮的老枯树般不停地颤抖着:“你,你们要,要干嘛……”
“老子今天不高兴,要把你炖来吃了。”一人脸上露出邪恶的奸笑。
“你……你……你……”
那人也等不来掌柜啰嗦,直接快刀斩乱麻,张口堵住了下一个“你”字:“绳子拿来,把这老头子给我捆个结结实实!”
其余两人面露喜色,一大截麻绳马上抛出,眼见便要下手了。
“大,大侠饶命啊!各位,各位,救命啊……”
于是乎,三人一拥而上,像包粽子般,将掌柜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掌柜张口想喊救命,但却被粗鲁地塞住了嘴:“老东西!看你怎么叫嚷!”
“喂!?!”不知何时,这个多灾多难的店门又闯入一个浮华骄横的年轻公子来,”老头子!死哪去了!“公子见好久没人应答,便粗暴地怒问一句,身旁还有好几个虎背熊腰的手下。
他是王道钦的小儿子王骄世,惹是生非、四处游荡、招花惹草……已经是家常便饭。其实他是有事可做的,就是不愿用功读书,凭着一副好相貌、好口才,父母便宠他而置之不理了,除非他又摊上了什么麻烦事,王道钦便以高权重之名拿几个钱出来搞定。
那几个暴徒见了他,当即跪下齐声道:“少爷,那老头子已经被小的们绑起来了,看样子是不会反抗的了。”
王骄世一声冷笑:“哈哈,这店还挺旺呵……”一脸猥琐地阴笑,“哼,本公子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说着恶狠狠地瞪着掌柜:“老头子,记得本公子么!哼,你再不给本公子那绿松石如意,本公子今天就宰了你!”
掌柜怎么不会记得,他曾经气势汹汹地以他父亲的名义威胁他交出绿松石如意?这绿松石如意原是掌柜一日在一家铺子前花高价买到的,原是想给老父母寿辰一个贺礼,谁知由于放在店里,便被闲游的王骄世盯上了。王骄世前几天得罪了父亲,为了给父亲赔礼,也为了让自己能继续逍遥下去,他四处搜寻宝物,正巧便碰上了掌柜的绿松石如意。他想以他父亲的名义花几个钱买下,谁知掌柜非但死不松口,还毫不客气地将他赶出了店门。这一下王骄世彻底恼了,第二天便集结了一群小混混找上门来。想来他王骄世骄横一世,怎能这样就被一个老头打得败下阵来?
“老头子,今日本公子若不拿到如意,你也就别想活了!”
“老大,如意不在柜台上!”
“你们都给我搜!”
于是乎,可怜的茶馆惨遭袭击,气得掌柜青筋暴跳,却又因堵着嘴巴而无可奈何。旁边的众人实在是看不过,纷纷出来劝架。但像王骄世这一类人是根本不会听的,这样做只能煽动起他们的怒火——王骄世手一挥,命令那些乌合之众道:“谁碍了你们的手脚,你们就揍他!”
“喂!哪有你这样的?!狗仗人势欺负人!”
“说谁呢!”王骄世气得脸色青紫,哪怕他是狗也不会仗人势!“你们把它揍一顿!叫它知道本公子的厉害!”王骄世绞尽脑汁想到用表示某种物品或动物的“它”,可惜刚出口就后悔了——语言表达并不能显现出它骂人的意谓来,自己好不容易想出的大炮只能遗憾地报废了。
几个手下一拥而上,那汉子想反抗,却早被控制住了手脚,数不清的拳头炮弹般击打在他的身上,直打得他毫无反抗之力、鼻青脸肿、气若游丝才肯罢手。这一类人都是人类中的变异品种,与狼相近——都有“浑然天成”的嗜血天性。
几个妇人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纷纷背过脸去;练薇儿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婴儿的眼睛,也许已经忘了这么小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大汉惨不忍睹的样子,再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不舒服。但是王骄世却十分得意地哈哈大笑,仿佛看到那浮肿的身体感到赏心悦目。只听他说教式地把脸转向众人说道:“你们谁敢对本公子有异议的,下场跟他一样!哈哈……”好不容易止住了那令人作呕的狂笑,又补充说明道,“你们好好呆在一旁别管闲事就行了!”又吩咐两名手下道,“你们两个,看谁啰嗦就给谁一拳头!”
一边在搜寻,一边又有两个夜叉一样的“看守”盯着,练薇儿惊讶地发现这个店竟连续出现好几个坏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坏。练薇儿原本出自富贵之家,但自从她出嫁后,变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家族中最重要的老父去世,接着又是女儿的父亲早逝,紧随其后的便是官府的抄家,府中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后来又起了一场大火,只剩她一个人带着孩子逃出来,一时间无法在城中待下去,便住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村落里。这天她出来购物,正巧经常照顾女儿的张大妈生了病,女儿还这么小她不放心给别人照看(毕竟整个练氏家族就只剩她一个苗儿了),便千辛万苦地把她带出来了。她从小到大从府内的贪污小人到江湖大盗坏人见多了,却倒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连环”的坏人出现。罕见呀。
更令她心里发毛的,是一个“看守”盯着自己不怀好意的目光。
时间是这样的漫长,特别是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下。
她盯着墙上斑驳的霉印,百般无聊地发现它呈海岛状。她想像着有一股大水从“海岛”白色的“沙滩”掀起,怒吼着、撕咬着、吞噬着那可怜的小块陆地,直到绿意完全浸没在茫茫波涛中。岛上人们的呼喊声还不断从水底闷闷地发出……
“走人!”那个骄横的公子朝他的手下一声大喝,充满慵懒的满足感。
练薇儿好似大梦初醒,还没回过神来。但只见人群再一次骚动,争先恐后地往门外逃,她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店里而不在岛上,思绪猛地恢复过来,抱着婴儿挤过去。
“嗯哼?”王骄世眯眼盯住练薇儿,“你说的便是她?”
手下笑眯眯地道:“是的公子,就是她了。您把她献给王大人,定能讨得其欢心!”
“嗯,长得不错是真的。
她心里无限地恐慌,紧紧搂住婴儿生怕一不小心弄丢了,却反而把婴儿给疼醒了,澄亮地睁着。练薇儿倒也顾不得了,正急急忙忙的要跨出门槛,却不知有谁突然在自己身后用力一挤,重心不稳,脚下一滑,“哎哟”一声跌倒在门栏前,忙扶着一旁的墙壁勉强站起,踉踉跄跄地垮了出去。
“你们快去将她拿住了,注意隐蔽!”
“是!”两个手下应声而去。哈哈,赏钱定是有了!
练薇儿一路上头也不回便进了深山。广茂的野木恍若天罗地网,掩住天光。
“啊——”忽的一声鸦啼乍起,“啊——啊——啊——”余音袅袅,山石皆颤。
漆黑的片羽荡悠悠地落下,瞪着她。她心里莫名地窜起彻骨的冰寒,于是——
于是她回过头去——
两双铁钳般的大手突然夹住了她的肩膀,她顿感肩上一阵灼痛:“啊哟!你,你们要怎么样?!”
可那两个绑匪不由分说,夺过她怀中的婴儿便掷于地上,幸得正巧掷进一处柔软无刺的灌木丛里,并无大碍。只可怜那小小的婴儿,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练薇儿使劲挣扎,却无济于事。两个绑匪不慌不忙地一条布堵住了她的嘴,又一条蒙住了她的双眼。她立即陷入了一片可怖的黑暗,只有婴儿的啼哭声震得她心碎,“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她想苦苦哀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留下两行泪水。
两个绑匪并不理会,挟住她欲往前行。
听着婴儿的哭声渐渐远去,练薇儿心想:“他们应该不会杀我的孩子了。”如此一想,倒安心了好些。但又转念一想,孩子还那么小便被丢弃在荒郊野岭里,便几乎是死路一条了。想到此处,又不禁黯然。“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愿我孩儿能逃过此劫!”泪水再次溢出眼眶。
一路上,她只感到冰寒彻骨,股股冷风在她耳畔凌厉地刮过。
不知过了多久,就当她觉得腰酸背疼即将散架之时,两个绑匪总算是停下了。
“都办妥了?”
“是,公子!人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