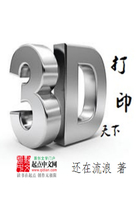1.
我有恋旧情结,所以从没敢把自己当作城里人。我一直觉得城里人应该是桀骜的、漂亮的、有未来主义倾向的,他们成群结队穿梭于立交桥上,花枝招展地奔走在摩天大楼之间,只为驱赶梦想的年轮,他们不需要怀念什么往事,也可以不屑于自己的出身。
北京西南四百千米处,是我不起眼的故乡。不起眼,源自它尴尬的地理位置,它北有省城,南有古都,南北两个邻居,将光芒揽尽。据说牛城以前也闪耀过光芒,那里烧出的白瓷,远销西域七万里,亮得足以照出女人的魂魄。可战乱一起,什么都没了,中国人创造文化的能力一流,破坏文化的能力也是一流,大兵所关注的,只有女人和金银,哪儿管什么吃饭喝茶的玩意儿,牛城白瓷自此衰落,直到今天,连个纪念碑、博物馆都没有。
中原小城,多连着村落,或唇齿相依,或隔河相望,高低错落间,挥洒着一方人气。郭家村就是这样的村子,这种地方,不存在学术定义,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统称它们为“城边村”,因为它有着标准的农村式格局——大小不一的院落、杂乱无章的胡同以及永远脏乱不堪的街道。郭家村人从不觉得自己是乡下人,他们以产业工人自诩,时时强调自己的城镇户口。计划经济时代,你可以诋毁一个人的德行,不可以诋毁人家的成分。[?
旧时代的人看重阶级成分,你可以指责对方人品有问题,但绝不能质疑对方的社会属性,比如他是工人,你就不能说他是农民,否则对方会愤怒或记恨。
]
可这一切,结束在十六年前的那个夏天,和牛城白瓷一样,郭家村的成分随着一个时代的崩塌变得支离破碎,接着什么都没了。
“什么城里人?你给我记住,咱们才是真正的牛城人!”羽爸爸把酒杯摔到桌上,红着脸说,“你以后少在我跟前说你们同学家里怎么好怎么好,城里怎么了?我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些住楼房的孩子,他们家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迁过来的,外来户,懂不懂?咱们家祖上在元朝当过官的,说出来吓死他们!”
“小羽!”羽妈妈在厨房喊,“过来帮妈收拾一下。”我放下电视机遥控器,看羽爸爸一眼,羽爸爸说:“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过去给你妈帮忙!”
我凑到羽妈妈身边,边洗碗边说:“妈,一会儿我去找明明玩。”羽妈妈扭过脸看着我说:“儿子,你爸这两天不痛快,跟他说话注意点儿,别再提你那些同学的爸爸什么的了,知道了吗?”我说:“不就是他单位那点儿事吗?”羽妈妈愣了一下,说:“谁告诉你的?”我低着头不吭声。羽妈妈说:“行了行了,别干了,去玩吧,记得十点前回来。”
郭家村北,六里河边,到处是乘凉的人。在空调没有普及的年代,清风就是飘荡在夏夜里的女神,男人们光着膀子讨论国家大事,女人们扬起蒲扇追打自己的小孩儿。岸边的树木舍去矜持,俯视着鸿沟凌乱摇摆,时而分离,时而靠近,像一对对无法倾诉的爱人。
小宁站在河堤上冲我挥手。我走过去问:“明明呢?”小宁说:“别提了,让他爸给扣家里了,他爸差点儿连我都骂一顿,那个班主任也去他家告状了。”我说:“那咱们还去那家游戏厅吗?”小宁说:“别去了,再给那个班主任逮住,去我家告状,我爸非打死我不可。”我吹吹脚下的土,盘腿坐下来说:“咱们家的老头儿都要下岗了,这事你知道吗?”小宁说:“下岗怎么了?下岗总比现在好。反正都是穷,我爸朋友多,能折腾,没单位拴着,说不定能挣大钱。”
小宁说的大钱,自然不是什么正道,宁爸爸从来就不是什么走正道的人。他是电机厂有名的刺儿头,不务正业,拉帮结派,整日被派出所民警询问。我一度好奇宁爸爸这样的工人为什么没被单位开除,羽爸爸给出解释:“你懂个屁,单位哪儿那么容易开除人?”所以,从道义上讲,羽爸爸和宁爸爸的电机厂活该倒闭,这样的企业,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不过是个混吃等死的福利院。
倒闭,在那个年代,也叫下马,实质上就是破产。没有人再买厂里生产的电机,大大小小的车间接二连三歇了工,工人们依旧按点上班,不过是围在车间角落里下象棋或喝茶水打发时间。半年,一年,又是半年过去了,没有起色,银行忍无可忍,现身讨债,并且搬出当地官员来评理,令整个厂区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大厦将倾,电机厂胖厂长勇敢地站了出来,他饮下白酒,安顿好妻儿,打开银库,清点余款,带着年轻的女会计,跑了。
电机厂最后一次职工大会结束后,所有车间的大门都挂上了铁链。那天晚上,羽妈妈一口饭没吃,盯着羽爸爸说:“二十年的工作,这就算完了?到底给不给安置啊?就算不安置,咱也不能稀里糊涂地买断工龄。”羽爸爸说:“全厂上千号人,谁不一样,你还有处说理啊?再说,都给你提出买断了,哪儿还有什么安置?”羽妈妈吧嗒吧嗒掉出眼泪来,嘟囔着说:“我本来就没个正式工作,现在你也没了,家里连块种菜的地都没有,这以后可怎么过啊,这不让人看笑话吗?”羽爸爸放下筷子说:“哎,哎,当着孩子的面哭什么?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谁爱看笑话谁看去,现在到处都这样,又不是咱们一家,你没看牛冶最近闹腾的那个劲儿?怎么?下来的都不要活啦?”
“儿子,”羽爸爸擦擦嘴说,“别吃了,给你妈拿条热毛巾去。”
羽爸爸说的牛冶,即牛城冶金厂,是与郭家村一河之隔的国企,其规模远比羽爸爸所在的电机厂大。牛冶这样的庞然大物,自然不会下马,只会改革,明爸爸就是第一批被革掉的老员工。当然,明爸爸的下岗与羽爸爸的下岗存在概念上的差异,用羽爸爸的话说,电机厂的下岗是同生共死,牛冶的下岗是始乱终弃,和同生共死相比,始乱终弃唯一的好处是每个月多出一百元的下岗补助。
但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父母的下岗并无分别,他们都是被时代抛弃的人,都是没本事的人,没人再养活他们,而他们还要养活我们。下岗,让郭家村的职工家庭第一次丧失了安全感。
事实证明,这个国度的女人永远比她们的男人强悍。为避免自己家成为笑话,羽妈妈迅速找到另一位家庭主妇宁妈妈,两人商议一个下午,隔天便蹬着自行车前往十几里外的板材厂学习板材轧制技术。而下了岗的羽爸爸和宁爸爸,拒绝任何一种体力劳动工作,他们每日窝在巴掌大的院子里晒太阳,或走街串巷下棋聊天,高不成低不就地吃起了软饭。
第一场秋雨落下时,羽爸爸和宁爸爸回到电机厂,最后一次帮厂里做事。他们执意要带上儿子,说见见世面。
杂草丛生的广场,人们围着地秤交头接耳。郭家村废品收购站的郭胖子站上秤沿,左手举起一叠大票,右手挥舞着空气,脸蛋笑得像团扭曲的粪团,他张嘴喊道:“大伙儿先说好了啊,待会儿叫价的时候都听副厂长的,副厂长数到三,拍谁,就算谁的,咱按规矩来。”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哄说:“滚下来,滚下来。”郭胖子的粪团子脸更加扭曲,咧着嘴说:“中,那咱就算说好了啊,待会儿大伙儿不能抢,我郭胖子这回是来买熟铁的,生铁我管不着,熟铁咱得按规矩来。”周围的人继续哄笑:“滚下来,滚下来。”
副厂长现身,带着债权机构与拍卖机构的人走过来,大家停止嬉闹,呼啦啦让开一条道路。副厂长走上台子咳嗽两声,整整衬衣领口说:“生铁五毛,熟铁七毛,上秤吧。”
广场西边不远处,是电机厂宿舍,墙下站着一排留守厂区的京籍老职工,他们穿着发白的工作服,提着沾满茶垢的水杯,身影被猩红的砖块和碧绿的爬山虎湮没,像一幅陈年的油画。这些老职工显然很纠结,他们渴望得到一笔钱体面地回老家养老,却又无法从心底接受这种心酸的来钱方式。他们看着那些陪伴自己半生的机器与钢材被一群乡下来的土包子一一推上地秤,难掩失落,仿佛亲生女儿下嫁给目不识丁的流氓,又仿佛自己的一生都被贱卖了。
拍卖活动结束后,宁爸爸和羽爸爸顺利拿到工龄款及厂里偿还给职工的集资款,回家继续吃软饭;买熟铁的郭胖子发了大财,盘下六里河河边一大块地,盖起更大的废品收购站;主持拍卖的电机厂副厂长回了南方老家,临行前他发给大伙儿一笔额外的公益金,并让留守宿舍的老职工们回了北京老家。据说在这次拍卖中,宁爸爸和羽爸爸还从各个废品收购商手中获取了一笔价格不菲的介绍费,只是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提。
羽爸爸将这些沾着铁锈沫子的钱悉数交给自己的老婆,告诉她等自己再弄到一笔钱就在国道旁开个酒店,那样全家就不愁吃喝了。羽妈妈略有异议,但这些钱毕竟是丈夫的,也难得他有了点儿志气,只好点头同意,之后她又带着宁妈妈去板材厂上班。
宁爸爸自始至终没告诉家人自己到底拿到多少钱,中秋节一过,他就跟几个狐朋狗友离开郭家村,远赴外地谋生,从此不再回来。据传话的人说,宁爸爸在外面做“红事生意”。所谓“红事生意”,就是用低价购买的粮食贿赂西部贫苦地区的农民,将他们的女儿嫁到东部平原,然后再向娶亲的家庭索要十倍的介绍费。对于宁爸爸的“红事生意”,整个家族里的人看法一致,觉得他这是变相拐卖人口,迟早要生大变。可宁妈妈不好说什么,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凭她在板材厂一千二的月薪,断断养不起两个上学的孩子和一个生病的父亲,她的男人再浑,再给她丢脸,还要指望他寄钱回来。穷人不是不明理,只是在理面前没什么底气。
2.
黄昏时,我、明明和小宁坐在工人路台阶上吃冰棍,牛冶下班人潮从眼前经过,整条路都是自行车链条的撞击声和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那时候,小宁是我们三人中最有钱的,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带着我和明明去街边吃零食,吃完喝完,再一起回郭家村。我质问小宁口袋里的百元大票哪儿来的,他拒绝回答,涨红着脸央求我们不要将这些钱的事告诉家族里的人。明明不依不饶,说:“我们就是想知道你从哪儿弄的这么多钱,再说我们能傻到告诉家里人吗?”小宁说:“反正我现在不能说,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明明说:“真没劲,自己哥们儿还藏着掖着。”
小宁看着明明,露出一丝愧疚。他突然望远处一眼,扔掉冰棍说:“快走,二炮子来了!”
我们拎起书包跑过马路,被二炮子的手下堵了个正着。二炮子摘下墨镜走过来,推小宁一把说:“跑什么呀你们?”小宁哆哆嗦嗦地退到墙边,说:“我们也没说走,刚才我表哥在那边喊我,可能有急事,我们过去看看。”二炮子挥手扇小宁一个耳光,说:“少给我装蒜!郭小宁,你不挺牛×的吗?怎么这回了?”小宁伸手摸脸,垂着眼皮不敢答话。二炮子接着扇我和明明两个耳光,说:“听说你们仨把我们院里一个小孩儿打得缝针了,够有能耐的啊,以后再到我们牛冶家属院来,记着跟我打,别净拣软柿子捏,听见没有?”小宁说:“听……听见了。”二炮子再扇小宁耳光,说:“听见了,听见了,我叫你听见了!”明明火起,挥出一拳砸向二炮子,嘴里骂道:“×你大爷!”
晚上,明明家,明爸爸黑脸看着我们三人肿起的黑眼圈,埋怨说:“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真有出息,上学,你们成绩倒数,街面上混,还整天挨打,你们安安生生地读书能招来这些事吗?”我含着眼泪说:“是牛冶的二炮子打我们的。上回在河堤,他们院里好几个孩子打我们三个,我们跑的时候随便扔了个砖头,结果砸中了他们中一个孩子的脑袋,他们就让二炮子在工人路上堵我们。”明爸爸说:“六里河边好几个村子,放学从工人路过的孩子多着呢,也没听说别人和牛冶家属院的孩子打架,以后不许你们再去招惹牛冶那帮孩子,放学先回家来,少给我去河对面晃悠!”羽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伸手拉过明爸爸说:“行了三哥,这几个兔崽子捣蛋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挨个打也好,让他们也长长记性,咱们进屋说咱们的事。”
明奶奶抓起一块皂色药膏挨个儿给我们往眼上抹,出于心疼,她没说一句话,明爸爸在里屋喊道:“妈,你少护着他们,都是你给惯的!”
抹完药膏,明奶奶慢慢走回自己房间,明妈妈从另一边屋里走出来,递给我和小宁两个拇指大小的布囊,说:“给你俩的,挂在脖子上,以后往好了学,别再给大人惹事了,知道没?”我和小宁说:“知道了。”明妈妈回屋后,小宁拿着布囊冲明明笑说:“这就是你们家的护身符?里面装的什么?”明明说:“里面没东西,是我妈年轻时用家里那块包佛像的布剪碎了缝的,我们家里人都戴,没剩几个了,给你你就戴着呗。”
十几年前的牛城南郊,民风比较淳朴,基本就两大阵营,六里河北岸工厂家属院住的多是牛冶的领导、工程师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六里河南岸村落居住的基本是工人或临时工家庭。由于六里河沿岸是国道,天南地北往来做生意的人也很多,村子里也渐渐入住了一些外地小商贩。
至于明爸爸这样一个在牛冶烧了二十年锅炉的老工长为什么给撸下来,必然是得罪了河对岸的人,所以明奶奶那晚的一言不发,并不仅仅出于对我们的心疼,也出于对自己儿子的惋惜。
羽爸爸在里屋大声说:“三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你一直过得不好,就因为你太一根筋。凡事不能跟气斗,那个姓郑的人品是不怎么样,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跟人家闹,怎么样?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撸下来了。现在嫂子也面临下岗,能替咱们说上话的就只有这个姓郑的,再说,他也没要求咱做什么,就是去服个软、道个歉。你也在牛冶混了十几年了,不能这点儿道理都不懂,就给他一回脸怎么了?他什么身份,咱什么身份!”明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他的脸值钱,老子的脸就不值钱?我就是死了也不求他。他什么东西?当了个破工会主席就管到天上去了,我道过一次歉,已经算给过他脸了,难道要我把脸全舍给这浑蛋吗?”羽爸爸说:“行,行,你要脸,你眼瞅着就要把全家老小饿死了,你瞧你多有脸。”明妈妈打圆场说:“你们急什么,这是商量事的样子吗?”明爸爸说:“反正我再不去求这个烂货。”
明爸爸说的这个“烂货”,是牛冶五区一个姓郑的领导,名头很响,名头响不光因为此人在仕途上骁勇,也因为其污秽不堪的生活作风,几乎每年都有车间女工或家属举报他。明爸爸和姓郑的之间的矛盾是本旧账,源于明明的妈妈,明妈妈当年号称五区之花,几乎每个目睹她芳容的小伙子都想追求她,这其中就包括姓郑的、明爸爸、宁爸爸等人。明妈妈和一个青年工程师有过一段恋爱,后来这个工程师为了调回北京工作,不惜对明妈妈始乱终弃,与同车间另一个有背景的女技术员好上。明妈妈怀了这个工程师的孩子,为了遮羞,火速下嫁给烧锅炉的明爸爸,次年在医院小产。这姓郑的本是车间职工,发迹后到生产管理部任职,之后频繁对辖区内的明妈妈进行骚扰,明爸爸不忿,带着老婆去工会举报,只得到搪塞式的回答,他一怒之下,叫上宁爸爸把姓郑的堵在巷子里狠揍了一顿。姓郑的是场面人,并没声张此事,也不敢再对明妈妈不敬,但祸根就此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