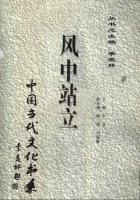文/比尔·盖茨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有一句话我已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讲出来了:“老爸,我常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此时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太棒了。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轻松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或许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佳。
不过,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Ballmer(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校园生活十分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未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连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多,并不代表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是,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忧,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出结果。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令人回味的情。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彻底地改变了我。
但是,若是现在严肃地回想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边缘。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发展。其实,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愿做的事。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无生命保障的生活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懂得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年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产业急速发展的时代,最终我们怎样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机制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到那些贫困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疾病中。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未发生过。
太让人吃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世界应把拯救他们当作头等的事来对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这般。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无法接受。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毫无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物质基础,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只言片语。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能体验出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面对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抱有信心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已经习以为常。”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繁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以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非常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会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不是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伤心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