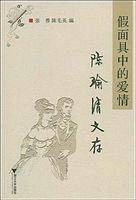文/张林杰
似乎拥有落雪的日子才让人感到冬天里的诗意……而落雪的日子终会在阳光普照的那天结束;迎来的还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季节,一些背光的老瓦房和沟坡却要拥抱一段时目的残雪来回忆着落雪往事,而冻枯的野草已在思考着另外一个世界。冬天里的一些事情很干燥,像村人们冻裂的嘴唇一样,总得用一些油质的东西去滋润,去涂抹,才能不再让人心痛;冬天里的一些幻想很清瘦,似乎要用一些老汉们熬热的羊肉白菜汤才能喂肥,幻想才暖暖地有了春情;冬天里的爱情很脆弱,似乎用村里的小伙和姑娘们相亲的红包裹包紧,才能让爱情不易破碎……男人们知道,冬天的阳光是很珍贵很短暂的,尽管他们拥有老婆通腿的热被窝(当然单身汉们的被头仅塞有暖水瓶而已),尽管他们在老瓦房内常生起一盆老树根盆火,他们还是向往阳光的。无数清冷的早晨,他们总是端着早饭,三五成群地一边晒太阳,一边吸溜吸溜地喝着稀饭,谈论着一些令人喷饭的荤话和口头流传的趣闻。女人们也一样地向往阳光,也照例端着饭碗,站在一旁拾笑。一顿饭能吃一个多钟头,只吃得结冰的坑塘里的水开了冻,吃得外村里串闲亲的客人们进了门儿,所以农村饭尤其是冬天里的农村饭有“饭十里”之说。乡下的冬天就是在男人和女人们吸溜吸溜喝稀饭之中一天天过去的;乡下的日头就是在男人和女人们咀嚼热馍就萝卜白菜中骨碌碌滚过去的;乡下的冬夜就是在男人和女人们通腿的热被窝里悄悄溜走的;乡下的月亮就是在打更的男人们的咳嗽声中惊起来的,也是在偷鸡摸狗小人的蹑手蹑脚中落西天的。
乡下的冬天是媒婆跑来跑去的日子。她们对明媒正娶的姑娘小伙总是很热心,常常为三两百元彩礼钱奔跑得不亦乐乎,常常为吹胡子瞪眼的男女双方家长使着小架,辛辛苦苦终于撮合了一对对婚姻。直到某个黄道吉日,姑娘终于坐了娶亲的小轿车,风光无限地做了乡下小伙的妻子,像她的父母一样地过起了乡下朴实的日子,此刻的媒婆吃醉酒的多皱面容上才露出了几分疲惫与无奈。说媒的干礼条是不好吃的。
严冬是老人们惧怕的日子。此时的老人们嘴上总是说着不怕死的硬实话,可又心虚地总是盘算着吃圆馍的日子。他们凭着老经验知道,一旦熬过了难熬的交九天气,打罢春他们就闯过了“鬼门关”,吃着了圆馍,在儿孙拜寿的欢笑声里,他们便有了信心再能迎来下一个严冬。可是,寒魔终会掠走某一位老人的晚年。理想中的圆馍,只能让儿孙们摆在他们睡去的那片土地上。于是,乡下的冬天的事情常常因某一位老人的突然睡去而丰富起来。村里的男人们派专人各家各户收取两元钱,凑在一起买上几条劣质烟、几挂炮、几捆火纸,一群群地去给办丧事的人家放挂炮,以示吊唁。然后议论着人生的短暂,严冬的艰难,互相提醒着也不知今死明活的人生,有了吃了喝了算了,好像都看破了红尘。几天之后,他们又各忙各的,忙忙碌碌的日子又在不知不觉中蚕食他们的生命,寒冷的冬天又在村庄里冻着他们善良结实的身体。
严冬只能在村里制造一些平常的故事和话题。这种故事和话题是在某一个村人们的喷嚏和咳嗽声中从小院里走出来的,是村人们在咀嚼麦子时品味出来的,是女人串门时倚在门框上倚出来的,也是老牛板们蹲在一起看牛倒沫时,抽旱烟熏出来的发黄的念叨——你的牛吃几筛草,我的驴怀了几个月驹。他们看惯了自己的牛吃草嚼料时的贪馋样儿,听惯了驴儿咀嚼草料的咯嘣咯嘣脆响的声音,更抽惯了他们抽了半辈子的壮烟叶子,也习惯了冬天里的严寒。烤惯了他们在牛屋里点燃的麦糠火。当落雪的日子又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定会从野地里挑回一挑挑流离干土,给他们心爱的牲畜们垫一垫圈铺,而后又烧热料水,好让牲畜们在落雪的日子里暖和一些。而他们自己往往只盖上一床很旧很破的被子——孝顺的儿媳们给他们一床新被子,他们却是不敢盖的,他们怕自己脏,污了新被子。一些有老伴的牛板们也无法享受老伴通腿暖脚的滋味,他们怕儿媳们笑话,他们怕村里人说他们“老没腔”。于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位老牛板,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冬夜,悄悄地便被寒流带去了他的生命。那时,有牛铃儿叮当叮当地给他奏响一种无韵致的歌儿……当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对一个村庄来说,少了一位老牛板,就像少了村里的一棵老弯腰树一样,没有人在意。只有老牛板的老伴儿在冬夜的一个角落里去怀念老树根一样结实的往事。这往事会发芽的,等到一个暖暖的春天,像老树根一样,会发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