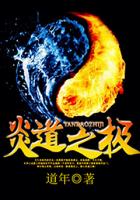里柯克
我有一个叫比利的朋友是“丛林癖”。他的本行是行医,因此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必要去野外歇宿。在通常情况下,他的心智看来是健全的。当他向前弓着身子和你说话的时候,从他的金边眼镜上方流露出的唯有和蔼与仁慈之光。像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是一个极其有教养的人,或者说,在他把教养完全忘掉之前,他是这么一个人。
我感觉不出他的血液中有任何犯罪素质。可实际上比利的反常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有一种“丛林露宿癖”。
更糟糕的是,他还经常癖性狂发,硬拖朋友们和他一块儿到丛林深处去。
无论何时我们碰到一块儿,他所谈的总是去丛林露宿的事儿。
前不久,我在俱乐部碰到他。
“我希望,”他说,“你能跟我一起到盖提诺去消遣消遣。”
“好呀,但愿我能去,可我并不想去。”我在心里自言自语,可是为了让他高兴高兴,我说:
“我们怎么去呢,比利,是坐汽车还是火车呢?”
“不,我们划船去。”
“那岂不是要一直逆流而上?”
“噢,没错。”比利兴致勃勃地说。
“我们要划多少天才能到达那儿呢?”
“六天。”
“能把时间缩短点吗?”
“可以。”比利回答说,他觉得我已开始进入角色,“要是我们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划,一直划到天黑,那我们只需五天半就可以到了。”
“天啦!要带行李吗?”
“要带好多哩。”
“为了搬运这些东西,我是不是每次得背二百磅翻山越岭呢?”
“是的。”
“还要请个向导,一个脏兮兮的地地道道的印第安向导吗?”
“没错。”
“我可以睡在他旁边吗?”
“噢,可以,假如你愿意的话。”
“上了小山头之后,还要干什么呢?”
“呃,那我们就翻越那儿的主峰。”
“噢,是这样,是吗?那主峰是不是石壁嶙峋,有三百码高呢?我是不是得背上一桶面粉爬上去呢?它会不会在山那边滚下来把我砸死呢?您瞧,比利,这次旅行真是件壮举,不过它大壮伟了,我可不敢奢望它。要是你能划一条带雨篷的铁船带我逆流而上,能用一台轿子或象轿把我们的行装运到主峰,再用一台起重机把东西放到山的另一边,那我就去。否则,那就只好做罢了。”
比利灰心丧气地撇下我走了。但是此后他又为此事和我折腾了好几次。
他提出带我到巴底斯坎河上游去。可我在下游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他要我跟他一同去阿塔瓦匹斯卡河的源头。我不愿去。
他说我应该去见识一下克瓦卡西斯大瀑布。可我凭什么应该去呢?
我向比利提了一个相反的建议:他穿过阿第伦达克山(坐火车)到纽约,再从那儿转车到大西洋城,再到华盛顿,然后带上我们的食物(在餐车里),去那儿(威勒德)露营几天,然后返回,我坐火车回来,他背着所有装备步行。
这事儿还是没有谈妥。
当然,比利只是成千上万“丛林癖”患者中的一员,而秋天则是这种病肆虐最凶的时节。
每天都有多趟火车北上,里面挤满了律师、银行家和经纪人,他们都是冲着丛林去的。他们的打扮有如海盗,头上戴着垂边帽,身上穿着法兰绒衬衫和有皮带的皮裤。他们能拿出比这些好得多的衣服来穿,可是他们不愿那样。我不清楚这些衣服他们从哪里弄来的。我想大概是从铁路上借的。他们的膝间别着枪支,腰间挂着大砍刀。他们抽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低劣的烟草,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行李车上都带着十加仑老酒。
在互相说谎的间隙,他们靠读铁路上印发的关于打猎的小册子消磨时光。从容不迫却穷凶极恶地炮制这类东西,旨在激发他们的“丛林癖”,使之愈演愈疯。对这类东西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就是写这种东西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全凭想象把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终点的一个叫狗湖的小地方胡吹了一番。那个地方作为居留地已经衰败了,铁道部门决定把它变成狩猎胜地。这种改头换面是由我实现的。我觉得我干得非常出色,我不仅给它重新命了名,而且还为这里生造了很多相应的玩法。那个小册子是这样写的:
“清澈的奥瓦塔威特尼斯湖(按当地印第安人的传说,此名意为:‘全能的上帝的镜子’)盛产各种名鱼。它们就游在水面下很近的地方,钓鱼人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它们。梭子鱼、小狗鱼、马鲛鱼、打油诗鱼和小鸡鱼可真多,在水里你挤我我挤你。它们常常飞速上蹿,一口咬住钓饵就朝岸上游来。在湖水的较深处,有沙丁鱼、龙虾、青鱼、鲥鱼和其他各种罐头鱼在自个儿悠游,显然一个个都自得其乐。而在清澈的湖水的更深处,还有狗鱼、猪鱼、傻瓜鱼和旗鱼在永不停息地转着圈儿寻开心。”
“奥瓦塔威特尼斯湖不仅仅是钓鱼爱好者的乐园。湖边的坡地上有大片大片长满古松的原始森林,经常有成群结队的熊走出森林来到湖畔——有棕色的、绿色的和熊色的——而当夜幕垂降的时候,森林里更是热闹非凡,麋鹿。驯鹿、羚羊、麝香牛、麝香鼠以及其他草食类哺乳动物的浅吟低唱不绝于耳。这些巨大的四足动物通常在晚上十点半钟离去,从这时到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整个湖滨就归野牛和水牛了。”
“午夜之后,充满渴望的狩猎者只有雅兴,可以选择任何距离、任何速度,让豺狼虎豹把他们追得飞跑。这些野兽的凶狠可是出了名的,它们随时渴望撕下猎人们的裤子,把利齿扎进他们颤抖的肉里。猎人们,注意啦!这样的历险多迷人呀,千万别错过良机。”
我见过不少人——文静、体面、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们——在旅馆的大厅里读我写的那个小册子,眼中流露出激动万分的光芒。我想准是关于虎豹之类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因为我发现他们在读那个小册子的时候,禁不住用双手在自己身上磨来擦去哩。
当然,你可以想见这类读物对刚刚离开办公室、打扮得像海盗的男人们的头脑会产生什么作用。
他们一读就疯了,而且一疯就会没完没了。
看看他们进入丛林后的情形就知道了。
瞧那个富有的经纪人,他肚子贴地趴在灌木丛里,两个亮闪闪的眼镜片像两轮马车的车灯似的。他在干什么呢?他在追踪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驯鹿。他正在“追踪”它,用他的肚子。当然,在内心深处,他本来是明白的,这里没有驯鹿而且从来就没有过;但是此公读过我的小册子,然后就发了疯。他没法不这样:他总得去追踪些什么呀。他是怎么爬行的。瞧,他爬过黑山莓树(非常小心,以致于驯鹿根本听不见树上的刺扎进他肉里的声音),接着他又爬过一个蜂窝,爬得那么斯文缓慢,就连蜂群向他发起猛攻时他都没有使驯鹿受到惊扰。多棒的森林技巧!是的,再好好观察他一下。你爱怎么观察都行。在他向前爬行的时候,你不妨跑到他后面去,在他裤子的屁股部位画一个蓝色的十字架。他决不会注意到的。他以为自己是一条猎狗哩。不过,当他那十岁的儿子把一块垫子披在肩上,在餐桌下面爬来爬去,假装自己是一只熊的时候,此公可是大大地嘲笑过一番的。
现在我们来看丛林里其他人的情况。
有人已告诉他们——我想我在小册子里首倡了这一种想法——野营就是睡在一堆铁杉枝上。我想我告诉过他们注意听风的歌吟(你明白我这个词的意思),听风在巨大的松树间浅吟低唱。于是他们大伙儿就在一堆青绿的针刺上挤着仰天躺了下来——即使是圣塞巴斯蒂安躺上去,都会觉得要命的。他们躺在那里,用充血的不安的眼睛瞪着天空,等着那浅吟低唱开始。可是看不到一点歌吟的迹象。
再看另一个人,他衣服破破烂烂的,胡子已有六天没刮过,他正在一小堆火上烤一块用棍子穿着的熏肉。眼下他把自己当成什么呢?是沃尔多夫·艾斯托里亚大酒店的首席厨师吗?是的,他是这么想,而且他还觉得那可怜的一小块肉——他是用切烟刀从一大块被雨水淋了六天的肉上面割下来——是适合食用的。而且,他马上就要把它吃掉了。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他们大伙儿全疯了。
还有一个人(愿上帝保佑他),他自以为具有当木匠的“能耐”。他正在往一棵树上钉一块又一块放东西的搁板哩。在所有的搁板掉下来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工巧匠。可也正是这个人,在他妻子要他在厨房里钉一块板子放东西的时候,曾经咒天诅地的。“该死的,怎么可能把那该死的东西钉上去呢?”他问道,“你以为我是一个铅管工吗?”
还好,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只要他们呆在那儿快活,就让他们呆着好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不在乎他们是否回来并且就露宿的事大吹特吹。回到城里的时候,他们因睡眠不足而疲惫不堪,因喝酒过多而没精打采;他们被丛林蝇叮得连皮肤都变成了黄色,还曾被麋鹿踩过,被熊和臭鼬追得在丛林里四处逃窜——而他们居然还好意思说他们喜欢这样。
不过有时我觉得他们真的喜欢这样。
不管怎么说,人毕竟不过是一种动物。他们喜欢跑出屋子到丛林里去,在夜间四处嗥叫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叮咬他们。
只是为什么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犯不着那么麻烦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们不在办公室里脱掉衣服,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并且互相嗥叫一气呢?其实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