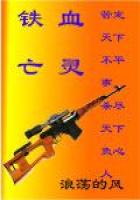杨彧随着王延宗绕过照壁与天井,又穿过一道月形小门,在一座雅致的阁楼前停下。王延宗上前与守在门口的童子见礼后轻声说了几句后,那童子皱眉看了一眼杨彧,点点头,开门进去了。
不一会儿,童子出来对王延宗道:“总管让你带人进去,他在书房等你们!”王延宗执礼甚恭,抱拳应了声:“是!”当先领路进去了。
杨彧无奈紧随其后,一踏入厢房,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这股香气起初淡雅如菊,气味幽然绵长,温和而隽永;越往里走,香味明显变强,却浓而不烈,深沉悠长,仿佛雪山之巅的古寺,宁静庄严,圣洁而内敛,令人闻之清心忘俗。
杨彧精神一振,抬眼看到书房门正开着,王延宗躬身站在门口,轻唤了声:“元先生!”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延宗啊,进来吧!”正是元总管的声音。
杨彧暗暗纳罕,这王延宗功力如此精深,为何对一个小小的武家总管如此恭敬有加?难道那个元总管的武功比他还要高?不及他细想,王延宗蓦地回头冷冷看了他一眼,嘴唇翕张间,声如蚊讷传来:“记得小心说话!”说完,已跨步进了书房。
一进入书房,杨彧迅速扫了一遍整个书房,只见雕琢古朴的菱花窗前,素白的窗纱已被整齐地束在一处,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文士正满脸倦容地躺在窗前一张酸枝摇椅上,膝上盖着一张双层云貂绒毯子,椅子旁的火盆烧得正旺。
最令人一见难忘的是这中年文士的眼睛,比一般人稍长半寸,双目张阖间,带着一种摄人心神的妖异魅力。他脸上的肤色晶莹剔透,白如晶玉,颌下三绺长须。中年文士头戴青丝绶诸葛巾,身着银白镶金边的锦袍,甚是儒雅,杨彧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心知他正是元总管。元总管手里捧着一卷新书,正细细研读。王延宗紧走几步,走到他的旁边,轻声说了几句,元总管听完后,秀长的眉毛微微一扬,抬眼看了杨彧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据我所知,绿瘦红肥于半月前接了巴州海龙帮帮主刘铖的花红,目标是个盗取帮中武学秘籍的叛徒,却不知道与杨兄弟有什么关系?”
他的声音却稍嫌尖利,甚至带着一丝阴柔,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刻意放慢说话的速度。杨彧被他一眼扫过,便感觉仿佛被看得通透了一般,整个背脊都凉沁沁的,双腿酸软,差点便跪倒在地。幸而这月余的逃亡磨练让他的意志愈发地坚韧,咬牙坚持挺直腰杆,沉声道:“不错,刘铖要杀的确实是我,不过并不是因为我偷了他的武学秘籍,而是因为他是个无耻小人!”
元总管这一眼叫做“照妖法眼”,是他的绝技之一,是属于“炼神”的武功,意志稍差或者心里有鬼者在一眼之下便能出丑,见杨彧竟然能抵住自己的目光,不由微感意外,正眼看着他道:“哦,说说看!”
杨彧把心一横,索性把自己与刘铖为何结仇,刘铖怎样集全帮之力追杀自己,自己为了掩人耳目应募武家的车夫之事和盘托出,那元总管听完,哑然失笑:“这刘铖我也听说过,手段是有的,但心胸未免不够宽广,又如此好面子,海龙帮在他手中,只怕止于此了!”正说着,忽地沉思了片刻,续道:“不论你是因何进的武家,既然你现在是武家的人,武家也从未有让外人随意欺凌的道理,你就安心做你的车夫,待这趟差事完后再自行决定去留!”言罢,摆了摆手。
王延宗会意地躬身退出了书房,杨彧连忙跟着出来,本已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了下来。晚风吹拂,杨彧忽地感觉背后寒意渗人,这才发现后背衣衫早被冷汗打湿了一片。暗暗后怕的同时又有疑惑升腾起来:“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这元总管为何会为了我和海龙帮交恶?”他可不会天真地相信元总管所说的,仅仅因为武家的规矩!
重新回到大堂上,王延宗才驻足回头,深深地看了杨彧一眼,警告道:“既然元总管让你留下,你就暂且留下,不过若让我发现你动什么歪心思,我自不会客气的,你好自为之!”说完,拂袖走了。
杨彧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暗暗捏了捏拳头,他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既然寄人篱下,所有委屈都只能忍着。
大堂上被撞碎的桌椅早已换好了,重又恢复到觥筹交错的热闹场景,只是不见了路十一的身影,杨彧猜想他多半是吃完回去休息了,也未放在心上,也草草填饱肚子,起身回去休息。
大通铺在后院,杨彧作为苦力,不能随意踏足住着武家亲眷的厢房,只能沿着一侧的马墙慢慢往回走。时值申酉之交,雨势渐止,雾气却愈发弥漫开来,四周都笼罩在苍茫的白雾之中,天地间仿佛就剩下自己一人,前方的路途在雾中忽隐忽现,透着无尽的危险与诡秘气息。
杨彧收摄心神,慢慢绕过一株月桂,却见路十一斜靠在一块大青石上,见他过来,憨笑着起身向他招了招手。杨彧猛地醒悟过来:原来他是在这里等我!心里不自禁地涌起一股暖意,急忙抢步上前,问道:“路十一,你怎么还没休息?”
路十一随意道:“没事,我从小做惯了粗活,就走了这么点路一点都不累,你怎么样?元弼没有为难你吧?”
“元弼?”杨彧怔了一下才明白过来他口中的元弼正是元总管,讪笑道:“为难我倒是没有,他只是让我赶完这趟车而已!”
路十一不动声色地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元弼这人向来自负,绿瘦红肥只不过是对单枪独马的杀手,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倒是你,元弼是出了名的笑里藏刀,现在被他知道了你利用了他,你以后记得要多防着他点!”
杨彧想起元总管那能动人心肺的一眼,不由地感到头皮一麻,苦笑道:“不至于吧?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元总管犯得着与我这样的小人物计较吗?”
路十一忽地哈哈大笑,竟一扫一直以来的憨直模样,眼中闪烁着杨彧从未见过的神采:“那是你不了解他,你可知道他的外号?”见杨彧摇了摇头,笑道:“元弼的外号叫‘神算子’,而他也颇为这个名号沾沾自喜,如今无意之中被你小小的算计了一次,这对他来说无异于人生败笔,他岂会善罢甘休?”
杨彧心里一惊,暗自叫苦:“本以为可以驱虎吞狼,谁知是狼未驱走,反而又引火烧身!”不过木已成舟,他却并不后悔,反而愈发激起更强大的斗志:“武功再强又算得什么?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目光忽地触及路十一神光内蕴的双眼,心中一凛:“他的眼神……原来他也不是个普通的人!”惊疑问道:“你……真是路十一?”
路十一一愣,正色道:“我当然不叫路十一,不过名字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放心,我不会害你就是!”
杨彧凝视着他脸上的神情,想起他先前一副老实巴交的劳苦模样,竟然骗过所有人,心里便横生出一股寒意:“这人装扮起苦力来惟妙惟肖,竟然连元总管这么精明的人,都被他蒙骗过去,而且我与他朝夕相处半月有余,都未能察觉到他的异样,这人的城府,当真可怕!”
路十一见他沉默不语,心知他仍然满怀戒心,无奈道:“元弼之所以没有发现我,一是因为我本身就不名一文,元弼自然不会注意到我,再者对于象他这样的地藏级高手来说,一个身无半分武功的人与蝼蚁无异,他又怎会将目光在我身上多停留一分呢?”
杨彧想起刚才王延宗的警告,以及话语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强横之意,深以为然,旋即又讶然追问道:“你真不会武功?”
路十一眼睛里蓦然流露出滂沱般深沉的悲恸:“我是个孤儿,义父在路边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躺了至少一天的时间了,若不是我父母用身体为我遮风挡雪,我恐怕早就冻死了,后来经过我义父的悉心救治,命虽捡了回来,全身多处经脉却因为寒毒侵蚀,已经坏死了,再也不能修炼武功了!”
杨彧心里猛然一震,或许是感受到了路十一心中的哀痛,直觉里便信了他的话:“既然你不懂武功,又怎么会知道元弼已达地藏级境界呢?”
路十一闻言古怪地看了一眼杨彧,道:“我说我‘不会’武功,没有说我‘不懂’武功!”杨彧一怔:“这有什么分别么?”
路十一狡黠一笑:“自然是有分别的,不懂武功的人定然就不会武功,但不会武功的人未必不懂武功,不是么?”
杨彧被他说的有些晕,路十一也不细说,续道:“元弼的‘惊神诀’据说是出自先秦以前,是一种专门炼神的功法。杨兄弟,你也是个伏藏师,可知何为炼神?”见杨彧缓缓摇头,正色道:“炼神者,修炼元神也!只要元神一成,便能脱去肉身的桎梏,瞬游万里,正所谓‘朝游北海暮苍梧’是也,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天人境界了。然则炼神谈何容易?我们人自一出生起便不断从眼,耳、鼻、舌、身五识中感受外界五境变化,从而产生种种欲望,这也就是所谓的‘欲神’,因之从五识来,故而又被称之为‘识神’!识神不灭,元神不生,是以欲要炼神,便要先去此识神!”
说到这里,见杨彧露出恍然的样子,又道:“《黄帝阴符经》中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意思是说,心因见物而欲望幻生,故说生于物也;逐物而丧失欲望,故言死于物也。是以若要去识神,当从守心开始,而守心之机,在于制目。目者,六识之首,乃心神之窍,故而惊神诀的第一要诀便在双目上,元弼的三大绝技之一,照妖法眼正是由此而来!”
杨彧听得意犹未尽的同时,暗暗心惊:“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对元弼所练的功法如此熟悉?”心中正惊疑不定时,路十一谨慎地四下看了看,忽地自怀中掏出一卷白绢,伸手塞到杨彧手里,压低声音道:“这就是元弼所练的惊神诀,其中炼心凝神之法,别出机杼,自成一格,你不妨拿去看看!”
杨彧差点跳起来,将信将疑地打开白绢,只见素白的绢面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开篇“惊神诀”三字最是触目,字迹轻灵跳脱,有若草原上难驯的野马,桀骜不羁,张扬之气似乎便要跃然而出。
路十一郑重地道:“这只是手抄的副本,虽然算不上什么天藏心法,但当初我们为了得到它也是费了不少心力,可以说得来不易,你定要小心收藏,若是丢失倒还罢了,倘若被被元弼发现了,就会让他有所警觉,这对我们以后计划会非常不利!”
杨彧感到事情处处透着古怪诡秘,茫然看向路十一,喃喃问道:“这是为什么?”
他问得无头无脑,路十一却似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坦然道:“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小人物’!”
“小人物?”
“是的,小人物!”路十一肩膊一挺,一股厚重气势喷薄而出,他语调昂然:“因为你成功逃过了海龙帮倾全帮之力的追杀,我们才注意到了你!海龙帮虽说不是什么名门大派,但在巴州一带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帮了,你一个人藏下品的无名之辈竟能接连三次逃过海龙帮的围追堵截,足见你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一回想起那段如丧家之犬般的日子,杨彧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娇小却倔强的身影,也正是因为这个身影支撑他走到了现在,眼中浮现出一丝柔情,木然道:“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