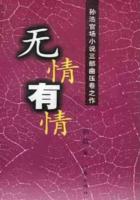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书里写的是真的吗?”
“作为一种描述,它是真实的。但它阐述的纲领都毫无意义。悄悄地积累知识——渐渐扩大启蒙的范围——最后促发群众的革命——将党推翻。看这书之前你就知道它会这么说。这都是胡说的。群众永远不会造反,再过一千年、一百万年都不会。他们不能这么做,我也不用告诉你原因,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曾经对暴力革命抱有什么希望,你必须将它丢掉。没有任何方法能把党推翻,党的统治将永远持续下去。要把这个作为你思想的出发点。”
他向床走近了一些。“永远!”他重复道,“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怎样做’和‘为什么’。你已经足够了解党是怎样维系它的权力的。现在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牢牢地抓住权力?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渴望权力?继续,说说吧。”见温斯顿没说话,他加了一句。
谁想温斯顿又沉默了一两分钟。疲惫的感觉将他淹没。奥布兰的脸上再一次隐约地现出狂热的激情。他已经预知到奥布兰会说些什么。党谋求权力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多数人。它追求权力,因为大部分人都软弱怯懦,无力承受自由也不敢面对现实。所以必须要由更加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计划地欺骗他们。人类要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做出选择,而大部分人都觉得选择幸福要好些。党永远都是弱者的监护者,一伙为了让好事光临而致力于行恶作恶的人,宁可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我。这很可怕,温斯顿想,可怕的地方在于在说这些话时,奥布兰打心眼里相信它们是真的。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这点。奥布兰无所不知,比温斯顿强了一千倍,他知道世界的真实样貌,他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潦倒不堪,他知道党通过谎言和残暴的手段让他们身处那种境况。他了解每件事,权衡每件事,但这不重要,为了终极目的的实现,这些都是合理的。温斯顿想,面对这样一个比你聪明的疯子,这样一个温和地聆听你的观点却坚持着自己疯狂的疯子,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我们好。”他声音微弱。
“你们认为人类不适合自己管理自己,所以——”
他几乎刚一开口就叫了起来,一阵剧痛穿过他的身体。奥布兰将控制盘上的杆子推到35。
“真蠢,温斯顿,真蠢!”他说,“你应该知道,你要说得更好才行。”
他将控制杆拉回来,继续道: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答案是,党追求权力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只关心权力。不是财富,不是奢侈的生活,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幸福,而仅仅是权力,纯粹的权力。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纯粹的权力’。我们和以往所有的寡头统治者都不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所有其他人,即使是那些和我们很像的人,也都是懦夫和虚伪的人。德国纳粹和俄国共产党有着和我们类似的管理方法,但他们从来都不敢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假装,也许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并非自愿夺取权力,而是时间有限,不久就会发生转变,会出现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明白,没有人出于放弃权力的目的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独裁政权不是为了捍卫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现在,你开始明白我的话了吧?”
温斯顿被震撼了,正如之前他看到奥布兰那疲惫的面孔后大感震撼一样。那是一张坚强、丰满、残酷的脸,又是一张充满智慧的、克制感情的脸。这张脸让他感到无助,这张脸又如此倦意弥漫。眼下有眼袋,双颊的皮肤松松垮垮。奥布兰侧了侧身,特意让自己那张憔悴的脸离他近些。
“你在想,”他说,“你在想我的脸怎么这么老,这么疲倦。你在想,我可以畅谈权力,却不可以阻止自己身体的衰败。你还不明白吗?温斯顿,个体仅仅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衰败是保证机体生命力的前提。你会在剪指甲的时候死掉吗?”
他离开床,又来来回回地走了起来,将一只手揣在口袋里。
“我们是权力祭司,”他说,“上帝是权力。但目前对你而言权力只是一个单词。是时候让你领会一些权力的含义了。首先,你必须理解,权力属于集体。个人只有在不是‘个人’的情况下才能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口号是‘自由即奴役’。你曾经想过吗,这句话可以颠倒过来?奴役即自由。单独的、自由的人总会被击败。一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会死,这种失败是所有失败中最大的失败。但如果他能够完全地、绝对地服从,如果他能够从个体的身份中逃脱出来,如果他能够和党融为一体,以至于他就是党,那他就能无所不能,永生不朽。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权力是指对人的权力,凌驾于身体的,特别是凌驾于思想的权力。权力凌驾于物质——正如你所说的,外在的现实——这不重要。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物质。
温斯顿有一会儿没有注意控制盘了,他突然想抬起身子坐起来,但他只能痛苦地扭动身体。
“但是你们怎么能控制物质呢?”他立刻说道,“你们甚至不能控制气候和重力定律,还有疾病、疼痛、死亡——”
奥布兰晃了晃手,打住了他的话。“我们能够控制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你会一点一点地学到的,温斯顿。没有我们做不到的。隐身、腾空——任何事。只要我想,我就能像肥皂泡那样从地板上飘起来,我不想,是因为党不希望我这么做。你要把19世纪那些关于自然规律的想法都抛开,我们才是制定自然规律的人。”
“但你们没有!你们深知不是这个星球的主人!欧亚国和东亚国呢?你们还没有征服它们。”
“这没什么重要的。我们会征服它们的,时机合适的话。就算我们不这么做,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能否认它们的存在。大洋国就是世界。”
“但世界无非是一颗灰尘。人类渺小而无助!人类才存在多久?几百万年前地球上还没有人呢。”
“胡扯!地球的年纪和我们的一样,它并不比我们老。它怎么可能比我们要老呢?除非经过人类的意识,否则没有什么能存在。”
“但岩石里满是已经灭绝的动物的骨头——我曾经听过,猛犸象、乳齿象以及巨大的爬行动物在人类出现前很久就存在了。”
“那你见过这些骨头吗,温斯顿?当然没有。它们是19世纪的生物学家捏造出来的。人类出现前什么都没有。在人类消失后——如果人类灭绝了——也什么都不存在了。人类之外别无他物。”
“可整个宇宙都在我们之外。看看星星!它们中的一些在一百万光年以外的地方。它们在我们永远都到达不了的地方。”
“星星是什么?”奥布兰漠然地说,“它们无非是几公里外的亮光。如果我们想,我们就能到那儿去。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清理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星星都绕着地球转。”温斯顿抽动了一下。这次他没说任何话。奥布兰继续说了下去,好像在回答一个反对意见。
“出于某种目的,当然,那不是真的。当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预测日食和月食时,我们经常发现,假设地球绕着太阳转,星星在亿万公里之外会非常方便。可这又算得了什么?你以为创造两套天文体系超出我们的能力了吗?星星可以近,也可以远,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你以为我们的数学家做不到吗?你把双重思想忘掉了吗?”
床上,温斯顿缩起身子。不管他说什么,迅猛而来的答案都像棍子一样将他击倒。而他仍然知道,知道自己是对的。“在你的思想以外别无他物”的观念——一定有办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吗?不是很久以前就被揭露说这是个谬论吗?它还有个名字,他忘了。奥布兰低头看着温斯顿,嘴角上出现一抹微笑。
“我和你说过,温斯顿,”他说,“玄学不是你的强项。你尝试记起的那个词是唯我论。但你错了。这不是唯我论,这是集体唯我论。这可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这是相反的事。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他用一种不同的语调说。“真正的权力,我们整日整夜为之战斗的权力,不是凌驾于物体的权力,而是凌驾于人的权力。”他停了下来,有一会儿,他又换上了那副神情,好像一个老师在向一个有前途的学生提问:“一个人如何对另一个人施以权力,温斯顿?”
温斯顿思考了一下,“通过让他受苦。”他说。
“一点不错。通过让他受苦。只有服从是不够的,除非让他受苦,否则你要如何确定他是服从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权力就是要让人处在痛苦和屈辱中。权力就是要将人类的意志撕成碎片,再按照你想要的新的样子将它们重新粘起来。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明白我们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和过去那些改革家所畅想的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世界刚好相反。这是一个被恐惧和背叛折磨的世界,一个充斥着践踏与被践踏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残酷的世界。旧时代的文明自称其建立之基是爱与正义。而我们的文明则建立在仇恨之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耀武扬威和自我贬低外,什么情感都不存在,我们会将它们统统毁灭。革命前幸存下来的思想习惯已经被我们消灭。我们割断了联结孩子和父母的纽带,割断了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联系。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孩子、朋友,且未来也不会再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一出生就要离开母亲,就好像从母鸡那里拿走鸡蛋。性本能将被彻底消灭,生殖将成为更新配给证一样一年一度的形式。我们要消除性兴奋。我们的神经学专家正在做这件事。除了对党的忠诚,没有其他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其他的爱,除了为击败敌人而笑,没有其他的笑。艺术、文学、科学都不会有了。当我们无所不能时,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什么科学。美和丑也不再有区别。不再有好奇心,在生命的进程中也不再有喜悦。所有其他类型的欢乐都要被摧毁。但是,温斯顿,别忘了,对权力的迷醉将永远存在,且这种迷醉还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敏感。永远,每时每刻都会有取得胜利的狂喜以及践踏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的激情。如果你把未来想成一幅画,那就想象一只皮靴正踩在一个人的脸上——永远都是如此。”
他停下来,好像在等温斯顿说些什么。温斯顿却又一次地想往床底下钻,他没说话,心脏就像结冰一般。奥布兰继续说:
“记住,永远都会这样。那张脸总会在那里让人踩踏。异端,还有社会的敌人,永远都会待在那里,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他们、侮辱他们。你落到我们手里后经历的每件事——都将持续下去,甚至比这更坏。间谍活动、各种叛变、逮捕、虐待、处决、失踪,所有这些都不会停止。这既是个充斥着恐惧的世界,也是个充斥着狂喜的世界。党越强大,容忍度就越低,反抗的力度越弱,专制的程度就越强。高德斯坦因和他的异端说将永远存在。每一天,每一分钟,它们都会被攻击、被质疑、被嘲弄、被唾弃,然而它们又会一直留存下来。我和你在这七年里上演的这出戏会反反复复的,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地演下去,但总的形式会更加巧妙。我们总是将异端带到仁爱部来,让他们因疼痛而叫喊,让他们精神崩溃,卑鄙可耻——最后翻然悔悟,拯救自己,心甘情愿地匍匐于我们脚下。这就是我们所准备的世界,温斯顿。这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是一个狂喜接着一个狂喜的世界,是无休无止的压迫着权力神经的世界。我能看出来,你开始明白了,意识到这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而最后你不止会理解它,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已经恢复得可以说话了。“你们不能!”他声音微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温斯顿?”
“你们创造不出你刚才描绘的那个世界。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梦。”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把文明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忍上。这样不能持久。”
“为什么不能?”
“它没有生命力,它会解体,它一定会自己毁灭掉自己。”
“胡扯!你依然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仇恨比爱更耗气力。为什么它应该这样呢?即使它真的这样了,又有什么不同吗?假设我们选择让自己更加迅速地耗光力气,假设我们让人生的速度加快,让人一到30岁就衰老,这又能怎样呢?你还不明白吗?个人的死亡算不上死亡,党是永生的。”
温斯顿一如既往地被奥布兰的说法打击得无可奈何,此外,他也害怕,害怕若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奥布兰会再次打开控制盘。但他依然无法保持沉默。除了对奥布兰所说的感到无法形容的恐惧外,他找不到支持他这么说的理由,在没有论据的情况下,他无力地进行了回击。
“我不知道——我不管。不管怎样你们都会失败。会有什么东西击败你们的,生活就会击败你们。”
“我们掌控生活,温斯顿,掌控它的全部。你对那个被称作‘人性’的东西心存幻想,这让你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并让你反对我们。但我们是人性的缔造者,人的可塑性是无限的。也许你又回到了你的老思路上去,觉得群众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把这想法从你的脑子里拿出去吧。他们就像动物一样无助。党就是人性,其他的都是表面之物——不相干。”
“我不管,最后,他们会击败你们。他们早晚会看清你们,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们撕成碎片。”
“你看到什么证据证明它正在发生吗?或者任何它会这样做的理由?”
“没有,但我相信会这样。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里有什么东西——我也说不清,某种精神,某种原则——你们永远不能战胜的东西。”
“你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信。”
“那么,那个会击败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人的精神。”
“你确信你是人吗?”
“是的。”
“假如你是人,温斯顿,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这种人已经灭绝了。我们是后来的人。你没意识到你是孤单的吗?你身处历史之外,你是不存在的。”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说起话来更严厉了,“你觉得你在道德上比我们要优越,因为我们又撒谎又残酷。”
“是的,我觉得我有这个优越感。”
奥布兰没说话,另外两个人说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温斯顿意识到其中一个人是他自己。那是他在兄弟会登记的那个晚上,和奥布兰谈话的录音。他听到自己正在承诺,他会撒谎、会偷盗、会造假、会杀人、会鼓励吸毒和卖淫、会去传播性病、会朝小孩子的脸上泼硫酸。奥布兰不耐烦地做了个小手势,就好像在说还不值得这样做。接着,他转了一下按钮,声音停止了。
“从床上起来。”他说。
绑住温斯顿的带子自己松开了,温斯顿下了床,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
“你是最后一个人,”奥布兰说,“你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你会看到你是怎样一幅尊容。把衣服脱了。”
温斯顿解开系工作服的带子。原本用来扣住衣服的拉链早就被扯下来了。他记不清在被捕之后有没有脱掉过衣服。工作服之下,他的身体上有些脏兮兮的淡黄色的碎布,隐约可以辨出那是内衣的碎片。就在他将衣服扔到地板上时,他看到屋子的尽头有一个三面镜。他向镜子走去,可没走多久就停下脚步,忍不住发出惊叫。
“继续走,”奥布兰说,“站在三扇镜子的中间,这样你还能看到你侧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