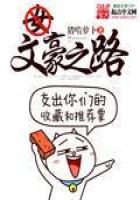在贝塔减地理教室,约翰了解到:蛮族保留地是不值得去耗费精力文明化的地区:那里气候和地理条件恶劣,或者自然资源匮乏。“咔哒”一声,百叶窗关上了,房间暗下来;老师头顶的屏幕上,展出了阿科马的忏悔者拜倒在圣女像前的影像。约翰曾听过他们痛哭,在基督十字架和菩公的鹰形图案前忏悔罪过。年轻的伊顿学生们哄堂大笑。忏悔者们依然在痛哭,然后站起身来,脱掉外套,用带有绳结的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自己。即使忏悔者们痛哭和呻吟声渐长,但还是被更大的笑声淹没了。
“他们为什么要笑?”野蛮人悲痛而困惑地问道。
“为什么?”院长向他转过身,露齿而笑,“为什么?因为这的确太好笑了。”
在屏幕的微光下,贝尔纳冒险采取了一个行动,要是放在以前,即使在完全漆黑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做。仗着他自以为傲的重要身份,他伸出手臂搂住女主任的腰。柳腰轻摇了下,屈服了。他正想趁机偷偷亲吻她一两下,或者掐她一把,百叶窗“咔哒”一声又打开了。
“我们继续参观吧,”济慈小姐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过了一会儿后,院长说:“这儿是睡眠学习控制室。”
成百上千个合成音乐盒,每个宿舍一个,排列在三面墙边的架子上;第四面墙边的鸽笼式文件柜里是录音带,收录了睡眠学习的课程录音。
“把录音带放进这里,”贝尔纳打断了加夫尼博士的话,解释说,“按下这个开关……”
“不对,是那边的开关。”院长愠怒着纠正。
“好吧,那个开关。录音带就打开了,硒电池将光脉冲转换为声波,然后……”
“然后你就能听到了。”加夫尼博士总结。
“他们会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么?”他们在去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半途路过了学校图书馆,野蛮人问道。
“当然不”,女主任红着脸说。
“我们的图书馆,”加夫尼博士说,“只有参考书。年轻人若是需要消遣娱乐,可以去感官剧院。沉溺于单独的娱乐活动可不是好事。”
五辆校车从他们身边的玻璃化公路上驶过,上面载满了孩子,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安静地拥抱。
“这些学生刚从泥沼火葬场回来,”加夫尼博士解释说。此时贝尔纳正偷偷地与女主任定下了特别之夜的约会。“他们从十八个月大时开始接受死亡条件设置。孩子们每周都要花两个早上的时间去医院上课,那里有最好的玩具,接受设置的那些天,他们会得到巧克力奶油点心。他们学着把死亡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和其他生理过程一样。”女主任专业地补充道。
约会定好了,八点钟在萨伏伊。
回伦敦的途中,他们在布伦特弗德的电视公司工厂前停了下来。
“你不介意等我一下吧?我去打个电话。”贝尔纳问。
野蛮人边等边看着。正好到了早晚换班时间,低等种姓的工人们正在单轨火车站门前排队,大约有七八百个伽玛、德尔塔和伊普西龙男女,却只有十来种不同的面孔和身高。售票员递车票的时候,会顺带递过一个小纸盒。长长的队伍正缓慢地向前蠕动。
“那里面是什么?(想起了《威尼斯商人》)那些纸盒里。”野蛮人向刚刚回来的贝尔纳打听。
“一天用量的唆麻,”贝尔纳含糊不清地回答。因为他正在咀嚼贝尼托·胡佛送给他的口香糖。“下班后领取,四粒半克药片,星期六能得到六粒。”
他亲切地拉着约翰的手臂,向直升机走去。
列宁娜欢快地哼唱着走进更衣室。
“你看起来挺高兴的。”法妮说。
“是啊,高兴得不得了。”她回答,“嘶拉”一声拉开拉链。“半小时前,贝尔纳打来电话。”“嘶拉,嘶拉”!她脱掉了短裤。“他突然邀约,”“嘶拉”!“问我今晚能不能带野蛮人去看感官剧,我得快点儿了。”她匆忙地奔向浴室。
“她真幸运!”法妮自言自语着看着列宁娜走远。
善良的法妮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没有丝毫嫉妒的意味。列宁娜确实很幸运,她和贝尔纳共享了野蛮人的盛名。原本不起眼的她立刻反射出时尚的光辉。青年妇女弗德协会的秘书不是已经邀请她做过一次演讲了么?爱美神俱乐部不是已经邀请她去参加年度晚宴了么?她不是已经上感官新闻,有形有声地出现在全球无数人面前了么?
显赫人物对她的恭维和关注也让她得意洋洋。文明世界总统的第二秘书曾邀请她共进晚餐和早餐,弗德大法官和坎特伯雷的首席歌唱家分别和她共度了周末,内外分泌公司董事长不停给她打电话,欧洲银行副董事长带她去了一趟多维尔。
“感觉妙极了,但是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在糊弄人。”她向法妮承认,“因为,大家最想知道的自然是跟野蛮人做爱的感觉。我却只能说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但这是真的。虽然我也不希望是真的,”她悲伤地叹了口气,“他英俊极了,你不觉得么?”
“他不是挺喜欢你的吗?”法妮问。
“我觉得他对我忽冷忽热。他常常躲着我。我一进屋,他就会出去;从来不碰我;甚至都不看我。但有时我突然转身,会发现他正在盯着我;你知道的,当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他会用怎样的眼神看你。”
是的,法妮很清楚。
“我真想不明白。”列宁娜说。
因为想不明白,她更加困惑和失落。
“因为我喜欢他。你懂我吧,法妮?”
她越来越喜欢他。现在,正好有机会了。她洗完澡,一边给自己身上拍香粉一边想。“啪,啪,啪”——真正的机会。她愉悦的心情化成了歌声。
“亲爱的,抱着我直到我心醉;
亲吻我直到我情迷;
抱着我,亲爱的甜心;
爱像唆麻一样美丽。”
芳香风琴正在演奏一曲让人心情愉悦、耳目一新的香草狂想曲——百里香、薰衣草、迷迭香、罗勒、桃金娘和龙嵩有节奏的翩翩起舞发出琶音;馨香的旋律经过一系列强烈的变奏融入了龙涎香,然后在檀香木、樟脑、雪松和新割干草的气息中回转(伴随着极其细微的不和谐的杂音——少许猪腰布丁和猪粪的气味),慢慢地变回最初淳朴的香气。尾音的百里香芬芳逐渐消失时,掌声响起,满堂喝彩,灯光也全都亮了起来。音乐合成音箱里的录音带开始播放。高音小提琴、超级大提琴和交替双簧管的三重奏让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惬意慵懒的氛围。三四十个小节之后,一个远远超过于人声的天籁之音开始婉转歌唱,配合着乐器旋律,时而发喉音,时而发头音,时而如笛声绕梁不绝,时而满载着和谐与渴望,毫不费力地从加斯帕德·福斯特破纪录的低音升到了极高的海豚音,比高音C调还高很多——这种具有穿透力的高音,在历史上众多的歌唱家中,只有卢克瑞嘉·阿胡加里唱出过。那是1770年,在帕尔马公爵歌剧院里的演唱,连莫扎特也为之震惊。
列宁娜和野蛮人陷在他们的充气座椅中,边嗅边听。接下来是运用眼睛和皮肤的时候了。
灯光熄灭,黑暗中漂浮着火焰般闪耀的大字:立体感观剧——《直升机里的三星期》,环绕立体声,合成对话,鲜艳多彩的立体画面,芳香风琴同步伴奏。
“紧握住你椅子扶手上的金属球形把手,”列宁娜低声说,“否则就体会不到感官效果了。”
野蛮人按她说的做了。
火焰般的字母消失了,音乐厅完全暗下来。十秒钟后,炫彩夺目、天下无双的画面突然出现:一个身形巨大的黑人和一个金发短头颅贝塔减女人互相搂抱着,这比现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还要真实得多,漂亮得多。
野蛮人开始发现嘴唇上异样的感觉。他摸了摸嘴,酥麻的感觉缓解了,手一放回金属把手上,又开始酥麻。芳香风琴似乎在演奏纯净的麝香味道。录音带上,那合成的声音,像是一只奄奄一息的超级鸽子,发出“哦——哦——”的声音,每秒钟只颤动三十二次。一个比非洲贝斯还要低的声音唱和着“啊——啊——”,“哦——啊!哦——啊!”屏幕上立体的男人女人再次亲吻起来。豪华宫殿般的剧院中,六千个观众脸部的敏感地带都像通过电流般酥麻,快感和刺激几乎让人无法承受,“哦……”
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第一声“哦啊”过后几分钟后(伴随着一段二重奏,两个男女在价值连城的熊皮上激情地做爱——命运预测师助理说得太对了,每一根头发都如此的清晰可感),黑人遭遇了直升机事故,头朝下栽下去。“砰!”额头上传来剧痛,观众席不禁发出“哎哟”的声音。
头部碰撞完全改变了黑人的条件设置。他对金发碧眼的贝塔女人产生了一种近乎发狂的独特热情。女人抗拒,但黑人还是坚持,挣扎,追求,攻击情敌,最后还惊心动魄地绑架了女人。金发贝塔被迷昏带到了天上,与黑人疯子单独在一起,整整三天都在听他讲******的无耻言论。最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和空中的翻滚打斗,三个年轻英俊的阿尔法成功解救了她。黑人被送到了成人重新设置中心。故事以金发碧眼的女人成为三个拯救者的情妇圆满结束。他们合唱了一首合成四重奏,有最好的管弦乐队伴奏,还有芳香风琴的栀子花香。最后给了熊皮一个特写的镜头,中间穿插着高分贝的萨克斯音乐。一个立体的吻消失在黑暗中,最后那点儿酥麻快感在唇上颤动,像是飞蛾扑火后留下的微光,不停颤动,越来越弱,最后慢慢平静,归于静止。
但列宁娜心中的飞蛾并没有死去。甚至直到灯都亮起来,他们随着人流向电梯走去的时候,飞蛾的幽灵仍然在她唇上振翅,在她的皮肤上探索欲望和快感的痕迹。她的脸颊绯红,用力地搂住野蛮人的手臂,贴在自己的胸前,整个人变得瘫软。他垂眸看着她,脸色变得苍白,心痛而渴望着,又为自己的****感到羞愧。他配不上她,配不上……他们四目交对,她那会说话般的眼睛真像是珍宝一样!那是女王的气质。他匆忙将目光移开,抽出被俘虏的手臂。他吓坏了,害怕她不再是那个自己配不上的圣洁姑娘。
“我觉得你不该看这种东西,”他说,急于把过去和未来有可能毁掉列宁娜完美形象的原因转嫁到客观环境上去了。
“哪种东西,约翰?”
“类似这种可怕戏剧的东西。”
“可怕?”列宁娜非常吃惊。“我觉得很美好啊。”
“太低俗了,”他愤怒地说,“太下流了。”
她摇摇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这么奇怪?怎么会突然一反常态地破坏气氛?
在计程飞机里,他几乎没看她一眼。被从未说出口的承诺束缚着,遵从着那早已不起作用的法则,他扭过身体坐着,一声不吭。他的身体有时会激烈地抽动,就像绷得紧紧的琴弦被拨动一样。
计程飞机降落在列宁娜公寓的屋顶上。“终于到了”,她走出驾驶室时高兴地想。终于到了,即使他刚才那么奇怪。站在灯下,她拿出小镜子照了照。终于到了。她的鼻子有点儿泛油光。在他付计程费时,她抖了抖粉盒儿,在泛油光的地方补上粉。她想:“他简直太帅了,其实不用像贝尔纳那样腼腆的。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早就上床了。好了,现在终于得手了。”镜中的自己露出了笑靥。
“晚安!”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列宁娜转过身。约翰站在计程飞机的登机口处,直直地盯着她看;显然,从她开始补妆时,他就一直在看着等着。他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犹豫,试图下定决心,也许一直想,想——她猜不透他的心思。“晚安,列宁娜!”他重复道,想努力对她微笑,却只做出一个奇怪的表情。
“等等,约翰……我以为你……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想……?”
他关上门,向前探身对司机说了什么,计程飞机飞向云端。
从窗户向下看,野蛮人能看见列宁娜扬起的脸,在灰蓝灯光的映射下显得苍白。她张嘴喊了些什么,她逐渐变小的身影急速离他而去;逐渐缩小的方形屋顶在黑暗中慢慢消散。
五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他藏东西的地方拿出被老鼠啃过的书,虔诚地翻阅着那脆弱褪色的书页。他在读《奥赛罗》,他记得奥赛罗是黑人,就像《直升机里的三星期》的男主角一样。
列宁娜擦干了眼泪,穿过屋顶走到电梯前。下到二十七楼之前,她拿出了唆麻药瓶。她觉得一克是不够的,一克唆麻并不足以治愈她的心痛。但是如果吃两克,可能明早就不能按时醒来。她做了折中的选择,向左手的掌心倒出了三粒半克的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