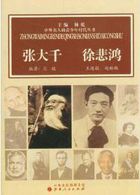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曏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
1919年1月,《北大日刊》以“自动研究”为题,登出梁漱溟的一项建议,说:昨范静生先生过谈,获闻其游美种种所得,其一则自动研究乃行之于小学生。范君述其所见,如讲授衣服一节,其教员但示如何看种种小参考书,及其他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其结果竟能由小学生自作种种研究报告。此诚令人闻之不能自奋者也。吾今自誓,吾自今后再不妨碍他人才思。如何是妨碍他人才思?他人方宜自用其才思处,而我代为之是也。哲学之生命全在思辨上。思辨而启便生,思辨而废置便死。哲学系学生诸君向哲学中讨生活。我既辱与诸君相讲习,自今以后不敢置诸君于死地,唯愿勉助诸君开辟生活。今拟以废止讲演在哲学教授会议提出,先写其感想如此。
在北京大学,梁漱溟建议不一定非要哲学系的教授讲课,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思辨”,这在当时,是件很新鲜的事。
还有一件事情亦很新鲜。
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发表了一个反对考试的宣言:不参加考试,不要学籍。
梁漱溟也不在乎学籍,但他认为考试仍有必要,并在《北大日刊》登出他的意见:“顷见朱谦之君反抗考试的宣言,我不甚谓然。”梁认为,朱君把考试和背诵几乎看成是一回事。其实,死背书不必要,背书有时仍属必要;考试不是全无必要。最好是让学生对功课产生兴趣,用考试“督迫他用功”是错的。考试不应是考学生的死知识,是试一试他有无心得。“因为有的人,他的心得见解,不去考问时,模模糊糊,若有若无,因受考问,才把见解清理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考试有必要,不过不要评定分数罢了”。背诵上,梁说,“我是第一个不会背诵的人”。从小到大没有背过书,至今佛经、孔经都举不出成句的来。每到用时再去翻书,很费事,“顿觉背诵亦不可少”。
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答复也登出来,告诉“谦之先生”,不考试可以,但是因为没有分数,也便不能发文凭。
1921年9月,当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新书出版时,书的扉页上印有一帧照片,四个人站在荷池旁。这是梁漱溟同他的三个好朋友、北大学生叶麟、朱谦之、黄艮庸的合影,四人年龄都在二十几岁,相互间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虽然四个人的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而且议论起来几乎一人一个样子,但他们充满青春的朝气,相处十分愉快。
所附题记还说:他辞去了北大教职,准备去山东滨县住一段时间,朱谦之将去杭州,叶麟提议照相。他们三个是最先听他说放弃佛家生活的人。这照片是改变生活态度的纪念,这书是改变态度的宣言,所以印在书前。
梁漱溟回忆:“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
来听课的人中,既有梁的朋友张难先、伍庸伯、江问渔(恒源),亦有抱着“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彭基相、余光伟。
北京大学的学术讨论风气开中国学术界之先河,这种风气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例如,陈独秀和陶孟和在《新青年》写文章讨论梁济自杀的问题,他该不该自杀?自杀纯属个人行为或不能这样看?梁漱溟写《答陈仲甫先生书》,又引起胡适写出他的感想,一同登在《新青年》上。
梁漱溟认为,他父亲自杀不只是个人的事,可以进行讨论,以免别人“流于错误不自觉”。他也不以公开议论自己的父亲为不孝,说“大约他天才智慧只算平常的”。但在另一面实在有过人的精神,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的维新家。“等到年纪大了,摄取知识的能力减退,形成新思想的能力减退”,以至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思想的遗留,于是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这使梁漱溟连带着想起一个问题:“何以这么大的中国却只有一个《新青年》杂志?”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头脑仍然固闭,“诸君所反复说之不已的,不过是很简单的一点思想,何以一般人就大惊小怪起来?”所以梁漱溟认为:“这国民精神的培养恐怕是第一件大事了。”
胡适则认为:梁漱溟的答书使他知道了“巨川先生精神生活的变迁”,这使胡警觉到防止思想老化,要准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提醒“今日的新青年,请看看二十年前的革命家”。
再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李超,为反对包办婚姻贫病而死。在她的追悼会上,参加者男士多,女士少,且限于本校的女生。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发言,追悼会变成了讨论会。
蒋梦麟批评北京的妇女界只顾穿戴华贵坐着汽车逛街;其他人也有感于妇女反而不热心妇女解放,讨论起怎样想办法使妇女关心自身解放的问题。
梁漱溟对大家的发言不太满意,他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现在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感情这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大家不要忽略过去。”认为“要求自由不是计算着自由有多大好处而要求的,是觉着不自由不可忍耐。北京的妇女界不来追悼李超女士是因为她们麻木,麻木是感情的反面。你指给她解决问题的道路,她不理会,应该唤醒她们的感情,不是教她们计算”。“提倡欲望,虽然也能使人往前动作,但我不赞成。”
梁漱溟认为:社会上贪婪之风太盛,并断言,贪风不改,国家民族没有前途。《新青年》登出一批文章来指导社会,于社会并没有多少益处。陈独秀作的《人生真义》、李大钊作的《今》、胡适作的《不朽》,宣示给别人的人生态度,虽不能说同是贪婪,其实是一条路子,“一言以蔽之,总是向外找”。“眼看一般人死命的东寻西找,真是可怜。”人生的意义和乐趣就在自己身上,好像宝贝本来自己家里有,却走遍天涯去找。“他们再也不得回家!因为他们已经走入了歧路。陈先生胡先生李先生都还在歧路上……”
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梁漱溟后来曾评论说:“五四运动是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开辟这个运动的是陈独秀和胡适……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当时北大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很有功绩,影响也很大。……但据我当时的交往,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胡适之先生后来同他们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
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有被捕者,梁漱溟就此事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摘要如下:
“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这次被捕学生中间,也有我的熟友。在他们未被释放的时候,我听到许多人运动保释,而当局拿出‘此风万不可长’的臭话,一定不允,我也同大家一样的气恼。但我今天拿出我与大家不同的意见来投稿在大家认为学生派的报纸上贡献与我同人。”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不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功,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没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哪一件不是借着国民的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既然恨司法官厅不去检举筹安会,我们就应当恭领官厅对我们的犯罪的检举审判。
……我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面顾全了法律,一方面免几个青年受委屈。
从文中可以看出,梁漱溟还是同情学生的。有论者认为:“从文中可以看出,梁漱溟向往着建立一种法制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西式的,是和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相对立的。他认为这种西式制度是世界的潮流,中国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这个世界潮流,中国人也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去生活。否则,中国就不能自立于世界上。从这一点出发,即便可以说梁漱溟的意见不利于学生,但起码不能说他的立场是封建的、反动的,和五四新思潮相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