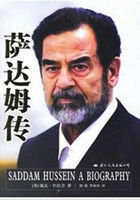梁漱溟虽然在京郊闭门读书,但对国家时局还是很关心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正因为如此,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人于1925年邀请他南下广州共商国事。然而,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未有意见,故未能成行。到了1927年,根据他的观察,对多年来困扰人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便是要“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便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他有了政见,因此,同年5月他应李济深等人前年之约到了广州。
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及第四军军长。他与梁漱溟过去在北京早已认识,而且交往甚密。所以两人见面时,梁便问道:“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李很持重地回答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梁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李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实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梁听了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李听了以后,感到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后来梁回忆说:“当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国民党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岂能容得别人有异样的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去了。”
梁、李二人这次见面,关于时局的谈话,彼此没有达成共识,但李对梁的学识与为人,还是敬重的。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发展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梁则认为既不合时宜,又无轻就之理,于是坚持不去上任。这年年底,李济深再次请梁出山,向他请教政治方略。梁到广州后与李进行彻夜长谈。梁很坦率地对李说:“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不是一些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大权仍然是集中在个人手里。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李听后不甚了然,便问如何开这条路。梁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条路就是我所谓的‘乡治’。”紧接着梁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李济深听了讲解后表示同意,便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他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众千余人。是时梁的意思,仍不出英国式的宪政范围,但有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于是他便竭力主张从地方自治入手,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结合起来,搞成一个自治体,即上述的所谓“乡治”是也。但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时他心中还没有什么底细。
梁漱溟的表弟郑天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校长)于1928年5月至8月,应梁漱溟之邀,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秘书,梁漱溟任代主任(主任为李济深)。两人相处四个多月,梁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给郑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郑天挺的日记里,自5月14日至6月3日,分七次记录了梁漱溟做“乡治十讲”的讲演内容。特摘要如下:
14日晚:
……个人政治主张与诸前人异。数十年来谈政者皆喜法西人,而迄无殊效。盖中国人有中国人之天性,中国之文化未可强效不同文化、不同天性之西人。
……然而数十年终无成就者,则以不合于中国之实况。
22日晚:
略谓:西洋文明系有对的,中国文明系无对的。因有对,故凡事皆向对方求解决,政治亦然。而中国正相反,此根本不合也。西洋政治精神在彼此监督,互相牵制,所谓三权鼎立是也。而其动机,实在彼此不信任。中国不然。彼此尊崇,彼此信托,皆相待以诚。倘一存猜疑,必至于糟。今欲仿效西人政治,势必降低固有精神,绝难有所创获,此其一也。选举制度为西洋政治之中心,西人皆用自炫手段以求当选,而中国以自炫为可鄙,必欲仿效,则必弃自尊之美德,先自轻贱。然此最高之精神一落,则不可复振矣,此其二也。西洋政治以欲望为本,中国则于欲望外更有较高之精神,如舍欲望外不计其他,必不能行于中国。
29日晚:
……在今日欲振兴工商业实不可能。社会不安定,易于破坏,一也;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难与西人竞争,二也。或谓由国家经营之国家资本主义其法较善。不知政局不定,国家亦无力经营。且若由国家经营,则政权、财权皆聚于政府,恐谋之者益多,而政局亦益不能安定矣。故可以挽救中国近日之局面者,唯有振兴农业。
31日晚:
……法律仅能使人做事合理,而不能使人做合理事。做事合理是谓法治;做合理事是谓人治。在法治派之政治理想以为,政权人人有份,政治自下而上,是为原则。而在人治派观之,因人类理智之有高下,则政权必交之理智最高者。人类理智不同,则政治不妨自上而下。中国自来为人治的政治,而非法治的政治。又谓:中国近日政治上经济上皆陷绝境,非从农村入手,无从整顿。一方面使农业发达,一方面使农民知识提高。
6月2日晚:
……法律是假的,风俗习惯是真的,吾辈应创习惯,唯乡治能创习惯。欲人民之问公众事,必须使之现有此意志、兴趣、能力、习惯。今之所以欲先行乡治者,以乡之范围小,利害切身,引其注意易而力强,一也;活动力之所及以范围小为宜,二也;中国固有之精神,城市已丧失殆尽,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三也;城市之心理习惯已近外国,唯乡村不然,四也;工商业为个人主义的,而农业为合作的、互助的,五也;乡里间尊师敬长,尚德尚齿,六也。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吾人建筑新政治之基础。
……吾之改造经济注意点在以私有经济制度为一切罪恶之源泉,私有经济制度为生存竞争之起源,因之人人敌对,人人时在危险情状之下。今若逆社会罪恶产生道理而思改革,终必无成,故改造私有经济制度必自改竞存为共存,始乡治之意即在此。先从消费享受求合作,渐至生产之共营。
在郑天挺6月3日下午梁漱溟演讲后的日记里,梁先介绍日本河西太一郎《农民问题研究》一书的大意,然后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主观、客观因素,如:天然制约、经济上的原因、收获后的原因、不能大经营的原因,又将农业与工业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工业上,阶级观念甚盛,故工人团结以对资本家,而在农业上适相反,又有中农之介于劳资之间。在工业上,工人皆思生产机关公有,而农民仅望分得少许土地,两者目的不同,故求改造经济之心理亦不同。今就经济目标为改造办法,必先使小农之私人经营渐改至合作,使私有为公有,分作为合作……总之,我国之精神文化皆与工商业无缘,除此文化已无前途外,今后局面必为农业复兴,而政治亦除乡治外无他路。必先发展乡村而至城市,先兴农业而至工商,农业之兴,必自合作社始。
从郑天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梁漱溟的“乡治”思想,与其在这一阶段的著作、演讲是一致的,如:制度的建立的关键因素是人民的习惯而不是法规制度;民族精神有高低不同,不能以高就低,无益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应坚持新的开悟;注意吸收进步的意见和方法(设想了一种新的农业合作方式,源于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