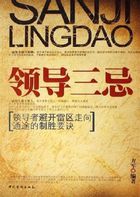梅子对走进门的儿子说:先洗把脸,妈妈今天带你去吃水岸火锅。儿子表情黯然:这个双休又不回去呀?梅子说,今天晚了,明天吧!
学校南面是座湖,傍湖西岸正在开发公园。县城里没有公园,城区的人对在建的公园很神往,没事爱来湖边走走。走的人多了就有了烟火。最先冒出来的是两个烧烤摊,两张茶几,几只马扎,湖岸路边一摆就有了生意。烧烤不能当饭吃,吃多了难免流露出遗憾。客人的遗憾就是商机,烧烤摊主摇身一变成了档主,挂出招牌:水岸火锅。
梅子挑了个靠边的位置,弯腰能从湖里舀水。此刻还没到客流高峰,湖边游人不多,档口也只有两、三个桌子上有人。客不多菜就上得快,刚沏的茶还没泡开锅子就端上来了。梅子吩咐上菜的小姑娘:给我们上瓶酒。姑娘向她要什么酒?梅子说,白酒。儿子不解,叫了声:妈!梅子没应。少时酒上来了,梅子吩咐:斟上。儿子问:妈你咋回事儿?梅子说:我让你斟酒。儿子迟迟疑疑地给母亲把酒斟上了,梅子又说:你也斟上。儿子也给自己斟了一杯放在面前,等着母亲发话。梅子也沒什么话,只对儿子说了一个字:喝!小西试着尝了一下,感觉很辣。向母亲投去一瞥,看到的是鼓励的目光。他一咬牙把杯子的酒全喝下去了。梅子点点头说,像个男子汉。接着亲自给儿子把酒斟上,说:这杯酒妈妈陪你喝,喝了这杯酒妈妈就不拿你当孩子了。来,妈妈祝你成年。
喝过成年酒的少年有点儿兴奋,杯子一落马上又提瓶子,却被母亲拿筷子拔开了。母亲说,今天就是个仪式,不是妈妈纵容你酗酒。林小西把酒瓶放下,问:妈你有话要说?梅子说,先吃饭吧!
梅子不断给儿子夹菜,夹了菜就把筷子横架在碗上,看着儿子吃。林小西几次放下碗筷敦促母亲:妈,你不吃我也吃不下。梅子总是说:妈妈不饿。说了不饿还要拿起筷子吃两口,以慰儿子的不安。孩子毕竟是孩子,林小西虽然心里忐忑,还是狼呑虎咽地吃了两碗饭。完了一抹嘴:妈,有啥话说吧!梅子注视着儿子,好一会儿无话。林小西说,妈你刚才说不拿我当孩子了。梅子叹了一口气:可你毕竟还是孩子,妈妈要说的事情很严重,真担心你承受不起。林小西神情悽然,幽幽地说:还有啥事儿比我爸爸死更严重?对孩子而言,父母离去是最不能承受的痛。世俗杂念只有成年人才看得真。是这样吗?梅子想起儿子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打击中的表现,不敢有些许自信。但她又不能不冒这个险。因为她清楚这件事情不可能瞒儿子太久,他早晚会知道的。以其让他从另外一种渠道得到真相,还不如亲口告诉他。这是一层原因。还有一层,事情已经出来了,她必须尽早去面对。总置身世外,不管是不是有意人家都会认为她在逃避。逃避只能让她更说不清楚,更被动。原以为经历过儿子的劫难之后,儿子就是她的一切。但还是做不到。荣誉可以放弃,羞辱也可以忍受,唯冤屈不能背。
听我说儿子,妈妈需要你的支持。妈妈希望你够坚强。你坚强妈妈才扛得住。林小西说,妈你说吧!梅子调整呼吸,语调尽量平静:你爸在一篇日记里说他找胡水垓要了一百万。林小西的谅讶很克制:一百万?妈你应该知道家里有没有这笔钱。梅子揺揺头:妈沒见到钱,也沒听你爸说过。林小西愿意相信母亲不是在骗他,但他需要说服自己的依据。爸爸自己在日记里说拿了一百万,这应该没什么可怀疑的。剩下的问题是一百万的去向,妈你说沒见过也沒听爸爸讲过,那爸爸会把这么多钱给谁?这正是梅子想不明白的。以林向西对家庭财政的一贯态度,他有一百万不会不交给她。她自己这么认定,别人也一定会这么认定。她说她没见过这笔钱,这话除了她自己恐怕就只有儿子一个人从感情上愿意相信,洗不清嫌疑一辈子的名誉就毀了。还不仅是名誉问题,如果国家要追脏,她从哪里弄一百万去。这个窝脏的罪名够监禁一辈子,无论对她个人还是对一个风雨飘揺的家庭,这个打击都是毁灭性的。林小西问:妈,你要怎么做?梅子说,妈要去找这笔钱。林小西忧心忡忡:能找到吗?梅子说,妈不知道。小西问:找不到咋办?梅子说,那妈也不能躲避。妈回黑洼去,不管今后是站着走路还是爬着走路,妈都要证明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妈沒有昧良心所以不怕回黑洼。妈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刚刚安定下来,妈又要把你一个人扔在城里,妈不放心。可是妈办法呀!梅子想起儿子曾经受过的委屈,想起那个晚上儿子在教学大楼的天台上一边哭一边吃安眠药的无助,她的心就一阵抽搐。林小西站起来,过去搂着母亲的肩膀说:妈你放心,我经历过一次了,不会轻易再被绊倒。我们走吧,我想去看看我爸爸的日记。
梅子母子回到黑洼,一进村口,首先看到林向西的那个空冢被刨了,几个人正下力推着石碑,样子似要把碑推倒。这个碑当初被推倒过一次,第二次用混凝土下了基脚,再想推倒它不容易。王二柱操起一柄铁锤就砸,铁锤砸在碑身上显得轻飘飘的。林小西看不下去,墓是假的碑不是假的,碑上有父亲的名子父亲的遗照,不能让人这般作践!梅子怕儿子年少莽撞,一双手紧紧地撸住他的臂膀:不要生事,快跟我回家去。不由分说,拽着儿子就走。走出几步远,听到身后有人骂:二柱子你吃饱了不干正事,哪儿下作哪有你。多好一块石料,留着垫个路搭个桥不好,非要砸乱!骂人的是邹大昌,他站在路上,手里的棍子指着墓地上的几个人,骂得胡子一翘翘的。王二柱手中的铁锤最后一次砸在石碑上,飞溅的石屑正好嘣到他的眼睛,直听他嗷地叫了一声,铁锤掉在地上。几个人围拢去看,见王二柱的右眼血糊糊一片,以为他被吹灯了。急着掰开手看,发现一枚石屑还嵌在眼皮下端。好险呀,只差一线!王二柱受了伤,没人肯再捡起地上的铁锤,奇怪的是刚才还铮铮作响的石碑突然从上端裂开一条缝,像有某种神力源自碑体自身。几个人怔怔地看着那条开裂的石缝慢慢扩展,炸裂的响声动人心魄,只听“轰隆”一声,半截石碑坠了下来。几个人傻愣片刻方才如梦初醒般地拔腿就跑,这个怪异的现象后来让他们很长时间睡不着觉,大白天没人陪着单独都不敢从那里经过。消息传出去,整个黑洼人都跟着心虚,从此再没人敢去碰那块断碑。
当时梅子把儿子拽开,经过已经停建的新村工地,看见邹浩东独自坐在砖堆上发愣。她们走到近处,邹浩东回头看了一眼,表情像看陌生人一样木然。梅子先叫了一声:浩东!邹浩东喔道:回来啦!口气很冷。梅子问:工程停了?邹浩东说,停了。梅子说,冬天很快就到了。邹浩东说,那谁也挡不住。梅子听邹浩东的口气完全心不在焉,说了声:我回去啦!邹浩东说,啊!梅子刚走,邹浩东又喊:哎!梅子站住,回头问:有事儿?邹浩东说,你不该回来。梅子说,这是我家。邹浩东说,对啊,那就在家呆着吧!梅子没再说什么,回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