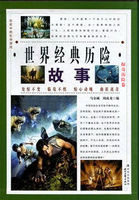天狗知道糊涂是装不得了,就过去扶起了女人。女人软得像一摊泥,天狗扶她不起,自己也跪下了,说:“我,我……”又急又怕又窘,支吾不清。女人抬起了头,一双抖抖的手,托住了天狗的脸。
“师娘!”
“谁是你师娘?法院让你叫我师娘?街坊四邻让你叫我师娘?”
“……姐!”
天狗叫出一个深埋在心底里的“姐”,女人突然软在了天狗的怀里。
外边的夜黑严了,黑透了,不是月蚀的夜,天空却完全成了一个天狗,连月亮,星星,萤火虫都给吞掉了。屋里灯很亮,灶火口的火炭很红。夜色给了这两个人黑色眼睛,两个人都看着亮的灯和红的炭,大声喘气。天狗抱着女人,女人在昏迷状态里颤栗。天狗的脑子里的记忆是非凡的,想起了堡子门洞上那一夜的歌声,想起了当年出门打井时女人的叮嘱。过去的天狗拥抱的幻想,是梦;现在是实实在在的女人。肉乎乎软绵绵的小兽,活的菩萨,在天狗的怀里。天狗怎么处理这女人?曾经是女人面前的孩子的天狗,现在要承担丈夫的责任了吗?天狗昏迷,天狗清白,天狗是一头善心善肠的羊,天狗是一条残酷的狼,他竟在女人头发上亲了一口,把颤栗的菩萨轻轻放在了凳子上。
女人在黑暗里睁大了一双秀眼。
“天狗,你还要到老屋去吗?”
“我还是去的好。”
“我知道你的心,天狗,可我对你说,我和他都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他。我是老了,我比你大三岁……”
“姐,你不要说,你不要说!“
“你让我把话说完,天狗,这一半年里,咱家是好过了,怎么好的,我也用不着说出来。你既然不这样,我也觉得是委屈了你,我将卖蝎的钱全都攒着,已经攒了一千三了,我要好好托人给你再找一个,让你重新结婚,就是花多花少,把这一院子房卖了,我也要给你找一个小的。兄弟,五兴他爹,我和你哥欠你的债,三生三世也还不完啊!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报答你,看着你夜夜往老屋去,我在厦房里流泪,你哥在堂屋里流泪……他爹,你怎么都可以,可你听我一句话,你今夜就不要过去,我是丑人,是比你大,你让我尽一夜我做老婆的身份吧。”
“姐,姐!”
天狗痛哭失声,突然扑倒在了尘土地上,给女人磕了三个响头,即疯了一般从门里跑出去了。
第三天里,打井的把式死在了炕上。
把式是自杀的。天狗和女人夜里的事情。他在堂屋的炕上一一听得明白,他就哭了,产生了这种念头。但把式对死是冷静的,他三天里脸上总是笑着,还说趣话,还唱了丑丑花鼓。但就在天狗和女人出去卖蝎走后,他喊了隔壁的孩子来,说是他要看蝎子,让将一口大蝎瓮移在窗外台上,又说怕瓮掉下,让取了一条麻绳将瓮拴好,绳头他拉在手里。孩子一走,他就把绳从窗棂上掏进来,绳头挽了圈子,套在了自己脖上,然后背过身用手推掉大瓮。绳子就拉紧了。
天狗回来,师傅好像是靠在窗子前要站起来的样子,便叫着“师傅,师傅!”没有回音,再一看,师傅的舌头从口里溜出来,身上也已凉了。
把式死了,把式死得可怜,也死得明白。四口之家,井把式为天狗腾了路,把手艺交给了天狗,把家交给了天狗,把什么都交给了天狗。他死得费劲,临死前说了什么话,谁也不可得知。天狗扑在师傅的身上,哭死了七次,七次被人用凉水泼醒。后悔的是天狗,天狗想做一个对得起师傅的徒弟,可是现在,徒弟对于师傅除了永久的忏悔,别的什么也说不出了。
堡子里的人都大受感动。
埋葬把式的那天,天狗虽不迷信,却高价请了阴阳师来看地穴,天狗就打了一口墓。墓很深。深得如一口井。他钻在里边挥镢挖土,就想起师傅当年的英武,就想起那打井前阴阳师念的“敕水咒”。
堡子里的人都来送葬。这个给堡子打出井水的手艺人,给家家带来了生存不可缺少的恩泽。他应该埋到井一样深的地方,变成地下的清流,浸渗在每一家的井里。
棺木要下墓了,女人突然放声嚎啕,跳进了墓坑,乞求着埋工说:“让我给他暖暖墓坑,让我给他暖暖啊!”
天狗也跳进去,解开了怀,将胸膛贴在冷土上。
日光荏苒,转眼到了把式的“百日”。这天,堡子里来了许多悼念的人,这一家人又哭了一场,招呼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吃罢饭,天狗就支持不住,先在师傅睡过的炕上去睡了。他做一个梦,梦见了师傅,师傅说:“天狗,这个家就全靠你了!家要过好,就好生养蝎,养蝎是咱家的手艺啊!”天狗说:“我记住的,师傅!”就过去扶师傅,师傅却不见了,面前是一只大得出奇的蝎子。天狗醒来,出了一身汗,梦却记得清清楚楚。翻身坐起,女人正点着灯,在当屋察看着蝎子盆罐。地上还有一批小瓦罐,上边都贴了字条,写着字。
天狗说:“五兴呢?”
女人说:“刚才把这些字条写好,看了一会书,到厦屋睡了。”
“蝎种全分好了?”
“好了,每家五只,除过五十家匠人顾不得养外,拢共得七百五十只,你看行吗?”堡子里的人都热羡着这家养蝎,但却碍于这是这家的手艺,便不好意思再来学养。天狗和女人商量了,就各家送些蝎种,希望全堡的人家都成养蝎户,使这美丽而不富裕的地方也两者统一起来。
天狗听女人说后,就轻轻笑笑,说:“明早咱就送去。中午去药房再卖上几斤,五兴再过十天就要高考了,要给他买一身新衣哩。”
女人说:“五兴考得上吗?”
天狗说:“问题不大吧。”
女人揭开那个大瓮,突然说:“天狗,你快来看看,这个蝎子好大!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怎么长得这么大呀!”
天狗走过去,果然看见蝎子很大,一时又想起了师傅,心里怦怦作跳,就坐回炕上大口喘气。
贾平凹作品精选任氏
任氏是个女妖,与郑六在长安城里认识的。
郑六好酒色,但人丑陋,又贫困无家,托身于妻族,便终日跟从了妻表兄,叫韦崟的,喝三吆四,闲游瞎逛。一日,两人又约定去新昌里吃酒,走到宣平,郑六忽记起还有一桩别事,说要迟到一会儿,自个骑驴往南,在升平北门里遇着了任氏。任氏那天穿着白衣,款款在街上走,郑六猛地瞥见,一时惊艳,人驴都愣住不动了。想:天下还有这般美人!以为是在梦中,自己打自己脸,脸生疼,就哀叹自己贫而丑,只能守家中那个黄脸婆。恨恨骂道:美女人都叫狗×了!骂是骂了,却不忍掉过驴头,也忘了要办的事,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欲要搭话,却又不敢。任氏并不作理会,裙长步碎,腰肢软闪,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郑六急说:“哎,掉东西了!”任氏捡了手帕,拿眼看他,眼是会说话的,郑六胆就大了,说:“这么美的人儿,怎么步行呢?”任氏并不羞怯,却笑了说:“有驴的不让嘛!”郑六立即翻下驴背,说:“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你若肯,你坐了,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任氏说:“是吗?”郑六说:“是啊!”任氏也不扭捏,说:“那我真要坐了!”坐上去,郑六驴前驴后颠着跑。
郑六信着任氏走,一直走到城东乐游原,天色便黑下来,见着路旁有了一庭院落,虽土墙车门,里边室宇却华丽清洁。任氏就下了驴,说:“稍等一会儿。”自个先走进去。门屏间有一女仆,过来问郑六名姓,郑六告诉了,也问女人名姓,方知姓任,排行二十,郑六说:噢,任二十娘!过了一会儿,被引入室去,室里早已有人列烛置膳,热情招呼吃喝。酒过三杯,任氏更衣出来陪伴,两人相互敬酒,酣饮极欢。郑六先是心意急迫,额头出汗,手却索索直抖,口里也语无伦次起来。暗自骂自己没彩,待稳住神气,借低头去捡掉下桌的筷子时,趁机将椅子往任氏身边挪近。见任氏并未退让,伸手过去捏了一下她的腿,慌忙缩回。任氏笑笑,倒端了酒杯又敬他,郑六已耳脸彤红,接了酒杯,也接了女人身子,嘬口就要吹灭灯盏。任氏说:“你啥不怕的,倒也怕灯?”郑六越发放肆,也不言语,抱了任氏在椅上解怀松带。任氏推拒,郑六已跪下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人儿……你救救我吧!”任氏看着郑六,擦了他口角涎水,扶起来,说:“这也是我命里所定……”郑六就抱起去了卧房。女人的妍姿美质,郑六从未见过,女人的歌笑态度,郑六从未经过,这一夜,郑六如狼如虎不能歇,如痴如醉又不敢信。
天明,任氏却催郑六早去,说是其兄在南衙任职,每日清晨要回来的。郑六不得已,又强支精神折腾了一番,还不忍走。任氏约了再会的日期,郑六方吻了女人从头到脚,又嗅了女人的衣衫鞋袜离去。
到了城门下,门还未开,城门外有家卖饼小店,店主正生火起炉,郑六一边坐于帘下等候城楼鼓响,一边与店主说话。
郑六说:“从这儿往东,那一大院落的是谁家呀?”
店主说:“哪里?那里一片荒地,没人家呀!”
郑六说:“我刚才还经过那里,怎么能没有?”
店主一脸疑惑,突然说:“噢,我知道了,这里有一个狐狸精,常诱男人过夜的,已经有过几个遭了道儿,今日你也遇了?”
郑六登时羞赧,却说:“没。”但郑六终不肯信,天大亮后,偏返身回去看,果然只见土墙车门,里边却衰草败柳,是一片荒芜的园子。
灰塌塌回来,见了韦崟。韦崟指责郑六失约,郑六也不好实说,支支吾吾只是受着。想自己所遇美人原是妖狐,甚觉悔恨,发誓道:再不寻女人了,美女人都是狐狸精!但一见到老婆,黄脸焦发,又唠叨不已,不去想任氏,又能想谁?夜里与老婆上床,老婆噗地吹灭灯,他就想到那日之夜,闭了眼,幻想身下老婆是了任氏,老婆说:“你现在刚强哩!”郑六也不作答,事毕翻滚一边,眼睁睁着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