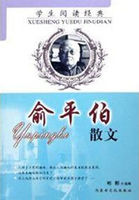浙江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联手,成立光华法学院,旨在远离教育行政化,实现“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这一举措吸引了许多国内知名的法学教授,成为近日教育界的一大新闻。
“教授治校”曾是浙大一段已逝的历史。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时,即提出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视教授为“大学的灵魂”,吸引了四方许多优秀人才。1945年9月,他发表文章更称:“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其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的模式是,凡大计方针均须通过校务会议民主决策,此外经费、训育、建筑、招生等项也都分设专门委员会民主掌管,由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这一治校方针,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全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近年来,大学体制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各个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大学日益变成了机关重叠、人浮于事的衙门。而每次由行政主导的改革,其实质都是在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以维护其巨大的空转。所谓本科教育评估,教授分级的评选,各种科研基金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是操于行政之手,使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行政化就是学术腐败的制度根源,因为它避免不了学术对权力的追逐。
在我看来,大学行政化的结果是造成了两个依附:学校对政府的依附和学者对学校的依附,也就是学术对权力的依附。而行政主导学术的表现,一是在人事方面,如职称晋升、工资待遇、教师流动等,最终决策权全归行政。浙大光华法学院提倡教授治院,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入手,便是看到这一点。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教师的晋升也如此,由本专业的权威人士评定,避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但问题是,职称最终仍得由校方确认。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浙大及其法学院以后要面临的问题。
二是在学术研究的取向方面。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自由教育,是探索知识和真理的场所。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如果要用简短而又通俗的语言来阐明‘大学是什么?’可以用一句古语来表达,就是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自由教育仅仅是理智的训练,因此,它的目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培养卓越的智力。”因此,在大学里,学问和思想是不应设限的,尤其不能以实用来划界。但由于科研资金掌握在行政权手上,行政的意图往往会左右学者的研究方向。比如,某些历史时期研究的缺失,就是因为拿不到科研经费,甚至不能发表成果,研究者要么只好转移学术兴趣,要么就甘于做学术边缘人。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当年,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已经成为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但若以今日行政化教育的眼光视之,陈先生的研究便是有点太自由和独立,完全是出于个人志趣,著述引文也不合乎大学科研处所定的规范,晚年所撰《柳如是别传》,其旨在“著书唯剩颂红妆”,更是与宏大的国家目标无干,世界观也与时代格格不入。可以想见,这位“教授的教授”倘若放在今天,大概也只能做边缘学者,拿不到任何“国家级课题”基金了。
我想说的是,在动辄以国家科研项目体现国家目标的今天,学术研究上应当允许个人目标,否则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独立。学术的真正目标归根到底是某些恒久或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所发明,而不是像当年凡有运动,就一定要拿学术来捧场,让学者们写一些诸如“鲁迅与爱国卫生运动”之类的文章。如果学术只能围绕着行政权力的导向来进行,其结果便恰如贺卫方先生所说,它只能使更多学者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因此,对于浙大法学院此次开风气之先,我还是乐观其成的。虽说是旧梦追寻,其实也属新的开辟。但愿浙大能起一个好头,为大学体制改革积累些好的经验,以利更多的后来者,而不是最后成为一个孤岛。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19日
断手背后是基础性秩序的沦陷
秋 风
1月15日,中建五局承建的南京溧水某工程工地上,在农民工与公司因为工资问题发生纠纷后,中建五局一名雇佣人员将一名农民工王超的左手砍断。万幸的是,这名农民工马上接受了手术,似乎可以保住自己的手。
但在中国,每天有成百上千像王超这样的工人,彻底失去手指、手或者胳膊。一种情形是机器吃人。有统计说,在珠三角地区,一年有4万根打工者的手指被轧掉。浙江省阳康被媒体称为“切指城”,该地有7000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1000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臂、手或手指。更不要说,还有很多工人,比如煤炭工人,整个身体都被黑暗吞噬了。
这些工人的遭遇还属于工伤范畴,另一些民众则是被人吃掉的。媒体隔三差五会报道,某地农民工讨要薪水,结果被暴徒砍断手指。为这些农民工维权的律师也会有此遭遇。就在两个多月前,广州花都区一位替农民工打官司讨工资的律师,在自家门口被三名歹徒持刀追砍,身中十刀,失去四根手指。若干积极从事业主维权的社区自治领袖人物,也曾经被暴徒追砍。
据说,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以用手劳动,而劳动创造了文明。过去20来年的经济奇迹,正是无数普通民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当然还有聪明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创造财富的整套机制似乎十分嗜血。本来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改善境遇的人们的身体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却被一只巨大的怪兽吞噬了。吞吃人体的,不仅是冷冰冰的机器、黑黝黝的矿坑,更有那明晃晃的刀刃。
当然,某些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世界全部奥秘之钥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经济增长必要的代价。如果农民不下煤窑,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所以,丧命煤矿是实现收入增长的必要成本。假如工人不进“切指城”,那他们的手指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至于讨薪者被砍掉手指,最起码说明他们已经挣到收入了,他们的手指终于进入市场了。
确实,经济增长当然会有成本,冷酷一些说,世间总有意外,总有某些人不够走运,成为他人享受文明的献祭,比如因为车祸而死。但是,孟子说过,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一切善行的起点,甚至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亚当?斯密也说,人皆有“同感”之心,道德就是因此而形成的。而最大的道德、善行就是让每个人的生命都得以维持,肢体不被伤害。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会透过集体智慧,形成并执行一套道德规则,控制人的兽性,引导每个人把他人当成人,尊重他人的生命。
但是,在浙江的“切指城”,在珠三角的那些工伤事故高发的工厂,工厂主们似乎在这方面无动于衷。谁都知道,办厂不易,提高生产的安全系数是需要投入的,而这方面的投入可能让企业无利可图。但是,成千上万被切断、绞碎的手指、手臂,似乎没有触动工厂主们一丁点的恻隐之心和同感。为了金钱而指挥暴徒对工人挥舞砍刀的工厂主、物业公司、建筑公司经理,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和同感完全被遮蔽了。
凡此种种或可表明,在当代中国,维系文明的合作、交易关系所需要的基础性秩序已经极度虚弱,甚至已经崩溃了。
上述种种骇人听闻的经济过程吞噬人的肢体现象,与政府管制不力有极大干系,而政府管制不力又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占据首要位置,为此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包括民众的身体。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不应偷盗,不应欺骗,不应伤害他人的身体,这些毋须法律规定,毋须政府禁止,一个正常社会中的人会普遍遵守。假如一个社会上有太多人对于这些戒律也得靠政府监视才会遵守,那这个社会就缺乏基础性秩序,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秩序。
如此社会基础使经济增长带上血腥味。开工厂的人眼看自己的机器一天一天地切断工人手指而无动于衷。从事商业的人一旦与弱势者发生纠纷,立刻就会考虑使用暴力手段,而他总会十分方便、廉价地找到替他动手的暴徒。在这样的社会秩序荒漠上,政府即便强化管制,恐怕也无济于事。南京市政府已经宣告,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建五局将被永远清除出南京建筑市场,但其他公司嗜血的动物本能会仅仅因此而不再发作吗?事实上,在如此这般的社会基础性秩序之上,政府本身的行为也可能趋向野蛮化。城管队员们为了所谓的城市秩序而打砸小贩摊点甚至打死旁观者,恐非偶然。
那么,如何拯救这个处于沦陷中的社会基础性道德秩序?这是需要每个人来解答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