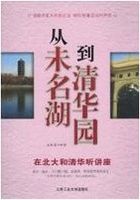有人可能会说城市眼下还有困难,但若是拿农民工遇到的困难与所谓城市的困难相比,可以说,城市的那点困难简直就不叫困难,只能说是城市还想要更高级的享受。退一步,就算城市还有困难,也不应该只要农民工带来的享受,而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却漠不关心,甚至总想将这一人群利用之后再驱赶出城市。很多城市人内心都清楚,说到底,没有几个人的祖宗就是“城里人”,甚至往上数,有的人自己的爷爷辈就是乡下人或说至今也还是乡下人,有的是打自己的父辈才进的城,更有一些人直到自己才成为所谓的城里人。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看不起农民兄弟的呢?不错,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大多数农民兄弟除了贫穷“第一”,各方面都不如城里人。但这绝不是他们的过错。甚至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还恰恰证明着这是以牺牲农民兄弟的很多利益才使得我们的城市像今天这样建设、发展起来,城里人也才活得更像个城里人。上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一句“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说的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不公或说农民为城市发展牺牲太大了。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还能至今不思忏悔呢?后来又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据统计,1953~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将近9500亿元,占农民净收入的57。5%。进入90年代后,这个数字每年增加到1000个亿以上,而农民的税费、摊派等负担每年都在400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约6000多亿的债务被县、乡两级政府用于超前消费。”(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2002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第23页)又另“据统计,城市的人均存款额是农村的10倍,加上其他资产,城市的人均财富是农村的20到30倍”(同上)。我想,这作者说的还是“人均”,如果“不人均”,百分之十或更多的城里人的存款数额恐怕要是一些农民的成千上万倍吧。同是中国的国民,相差是多么悬殊啊。
我们不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实现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社会要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就只是一句空话。而城市像现在这样对待农民工又有何公平正义可言?我们不是要以人为本吗?以人为本,我的理解就不是说只以城市的人为本,而是包括所有的国民,甚至包括凡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人;以人为本,就不仅是要让人有饭吃有衣穿,政府还要为他们“遮风挡雨”,还有负责他们生老病死的义务。
原载《郑州晚报》2008年4月15日
我们的桂冠路线图
刘洪波
到了发桂冠的时节。诺贝尔奖开了,各个奖项分别亮相。这自然又引起了一年一度的心病。固定的谈资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不能花落中国;临时的谈资也有一个: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得了化学奖。
我的印象,在中国,诺贝尔奖情结之重,主要体现于文学奖,每年都会讨论文学奖就是证明。这不是说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等奖项就不想得,那也是很想得的,为什么没有人讨论来讨论去呢?大概是先已自认“技不如人”,服气了,也就不需要太讨论了。哪年有个把海外华人得奖,那可以用来反省一下科研人才的问题。是的,科研人才甚至科研体制有问题,这我们总是勇于承认的。
于是,好讨论的就只有文学奖啦。这个讨论之所以存在,就表明这样一个隐藏的看法:物理化学我们是搞不过别人的,经济学呢,我们也是搞不过的,说点什么也总归是别人的理论,只有文学,我们是不差的,我们甚至是很好的,很好而又不得奖,那就是文化偏见的问题。“诗无达诂”,真是一个好话。旁观者可以说“文无第一”,局中人也可以说“文学还是自己的好”。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写得最好,故而“文无第一”就可以转化为人人可以称第一,而不必称第二了,“桂冠人人可得而戴之”。
这样的一个心态,即使我们可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以为然,又可以使我们对获得这个奖项怀抱期待,对没有得奖产生从酸叽叽到愤愤然的各种委屈反应:且羞且怨、且羡且妒。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的,要说有也只有一个推广不够的问题,或者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言还不够有力的问题,推广好了,就有奖了,或者中国文化主导世界了,奖就在我们这里不挪窝了。
哈哈!这样的思维线路图和得奖线路图。我们的文学作品很好,我们的文学人才很多,我们的文学体制优秀,我们的文学思维先进,总之,我们认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特异,而且健康,这与科研上是不一样的。
思维路线图和得奖路线图,还有一种。这奖那奖,这指数那指标,何必看别人闹腾呢,可以换思路的。于是中国科学院给中国发了一个奖: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名第一。这个冠军不简单,综合衡量了几十个国家为其国民及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所承担和履行的责任,才得出了一个排名表,居首为中国,末位为美国。
老听说世界上最高一档的就是定标准。标准一换,就有桂冠。如果这个指数能够影响扩大,把那些认为用其他标准老是排名吃亏的人都吸引过来,世界上扬眉吐气的人就多了。这也是对世界的一项特殊贡献。
我的朋友长平先生说中科院的《国家健康报告》雷倒许多人,我觉得很片面。这个报告雷倒许多人,但也迷倒很多人啊!何况被雷倒也好,被迷倒也好,总之是有影响力的,而我怀疑世界上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把这个报告不当回事,那才是真的可怜,会使我们获得“国家责任指数全球排名第一”的桂冠变得像开心辞典。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理解别开生面的思维路线图和得奖路线图之苦心。仿此路线图,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可以另辟一个奖来解决。王蒙和余光中有建议,设“世界华语文学奖”,思路好,但太小气了,自家子玩玩,有什么意思?还是要像“全球国家责任指数”这样,包容各国,雷倒或迷倒许多人。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6日
贾府失盗之后
王跃文
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并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行窃。贾政接报,头一句便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方才放了心:“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耽罪名。”
读着《红楼梦》里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原来像贾府这等府第,连奴才们都知道要恪守主子的财产机密。
贾府有贪墨之罪,似乎是肯定的,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但贪墨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抑或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课子极是严厉,宝玉只需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等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便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是贪墨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有株连之法,自是过于苛严了些。但如要向贪墨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帑,索人贿赂,反而是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我不明白,贪墨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得多了。
坏人们可以好好的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有载: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真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想起了令人敬重的克拉克夫人。上个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哈伯因为研究出合成氨和硝酸技术而享誉世界。德国因为拥有这两项技术,一方面粮食大量增产,一方面可以制造出更多的炸药。恰恰因了这两项技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穷凶极恶,为欧洲人民增添了苦难。哈伯得到德皇的赞赏,便又研究出了毒气弹氯气罐,直接替战争效力。哈伯的妻子克拉克夫人因为丈夫的罪过而深深地痛苦,极力劝阻他放弃不人道的研究。哈伯不听,又去研究新的毒气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终于在1915年自杀了,想用自己的死来唤起哈伯的良知。哈伯依然我行我素,还是研究出了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的那高贵的灵魂永远不会原谅哈伯的,尽管他后来在191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如果贾政是哈伯,王夫人是克拉克夫人,王夫人不会自杀的。她会一边吃斋念佛,一边替丈夫骄傲:毕竟获过诺贝尔化学奖啊!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8年第9期
假如江姐活到今天
刘兴雨
每当听到《红梅赞》那充满激情的歌声,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假如江姐活到今天该会怎样。
根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料,她的儿子、孙子都学有所成,在遥远的美国成了专家、获得了学位,给咱中国人长了脸。这一点,已经没有了悬念。
江姐的儿子尽管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但他的血管里流的还是中国人的血液,就像张明敏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尤其是孝道一定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一定会把江姐接到美国去开开眼界,这一点,想来江姐不会拒绝。可在美国看完了高楼大厦之后,她一定会拒绝儿子在美国度过余年的请求。为什么?因为她满耳听的都是异乡之语,到外面遛弯迷路了都不知向谁打听道,而且,在她心里会认定“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她知道,她的根还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尽管那里生活很舒适。
江姐生活在中国,内心一定会久久不能平静,她的情绪应该在自豪、迷惑甚至愤懑的状态下交织。当她看到各级政府大楼上飘扬的国旗,她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当年她们在狱中绣红旗的情景,如今,这样的旗帜已经飘满了天下,而这旗帜上有她的一滴血,她怎能不激动,怎能不自豪?可当她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了黑社会的报道,尤其广东的揭阳帮,简直成了黑社会的天下,当地的生产、流通都被他们操纵,当地的公安都对他们束手无策,她会不停地叨念,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当她看到宽广的马路,看到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她会觉得眼花缭乱,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看到各家各户都有了电视、冰箱,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个手机,想起当年为之奋斗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她内心会十分欣慰。当年仿佛十分遥远的梦想,如今不但都变为现实,而且许多都超过了那时的想象,就像现在几乎普及的电视、冰箱、手机、电脑,她那时不但没有听说过,而且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每想到这些,她都禁不住欢喜,我们当年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人们能过上好日子吗?可当她知道,许多工人都下了岗,挂着小牌在寒风凛冽的街头等着人找活儿,而他们的工厂竟被人用难以相信的低廉价格出卖,中间的大量回扣竟无形中流入个人的腰包,尤其是看到有些贪官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成亿地捞取人们的血汗钱的时候,她会暗问自己,我们当年提着脑袋革命,难道是为了养活这些大大小小的蛀虫吗?钱几辈子都用不了,怎么还贪呢?这一点,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们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牺牲,是为这帮混蛋这样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取吗?
她看到许许多多不公平的事情,就像火上的猎物,忍受着煎熬。有些明明该办的事情没人去办,有些明明不该办的事情照样有人明目张胆地办;有些明明应该用的人才弃之不用,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却可以呼风唤雨;办假证的广告满街都是,还公开留着联系的手机号码,影响市容败坏人心,人们居然都视而不见,她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南方遭遇50年一遇的雪灾,断水断电,人们过年不能按时回家,她心急如焚;听说有些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甚至用钱买官卖官,她禁不住忧心忡忡;看到孩子们课业那么重,小小年纪就卷入了竞争的洪流,她不禁叹息又惋惜。
毕竟要过年了,满大街摆着春联福字,还各处悬挂着红灯笼,人流熙熙攘攘。尽管人们抱怨食品涨价太快,可比起三十多年前买肉买菜、买豆腐都要凭票都要限量的时候,那真是天差地别了。于是,江姐也清除了心中的不快,买了一副对联,欢欢喜喜回家过年去也。
原载《本溪日报》2008年2月3日
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