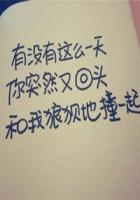我生来很少撒娇,小时候也不如其他小孩哭闹,一个人躺在摇篮里能玩一天的橡皮鸭,上学后顺理成章地一直当班长,指挥这指挥那,性格顽强得不像女孩。长辈们说我不像你,你却傻乎乎地乐,嘴上嚷着:“像的像的,小乖怎么不像我了?”
你总叫我小乖。像养小兔子一样养着我。最自豪的不是我考试拿了第一,而是把我生得很白。你从来不要求我一定要怎样,“生活就是要自由自在才好”,你总是这样说,太过简单的你,像个哲理家。或许正是你的不严苛,让我的青春叛逆期缩得很短。也因为你的随意,让我从来不觉得和别人不同。我们常常夜聊,关了灯,月光渗过玻璃进到屋里,视界里暧昧不清地凸显出事物的轮廓。有时候太困顿精神的防线也退去了,你喃喃地说:“一白遮三丑,幸亏你不像我……”话到这里声音淡去了尾巴,我的心跳得很快,忍不住靠近过去,只听到你轻微的呼吸。
初中时,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很老很老的题目:我最难忘的人。启发思维时,老师让们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人,别的同学用了“伟大”、“无私”、“勇敢”、“可爱”等等词语,轮到我时,大脑里却锁定不了任何东西,像是大雨冲刷后的天空。你略显稚嫩的娃娃脸和总是无辜的眼神盘旋在我脑海间,没有母亲的威严,像是姐姐,实则又更像妹妹。回来后我将困惑告诉你,你笑得厉害,我莫名其妙生了气,你才强忍住严肃下来。你问我:“这样不好吗?”我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高中后学会发呆,不知是不是看了太多小说的缘故,突然少年老成地感叹起生活的无趣来。成绩自然跌落谷底,班长和学生会代表之类的统统离我远去。想到我的一生很可能就这样废掉了,你安慰我这是成长的叛逆期,度过这一段就好了。你的纵容并不能让我得到安慰,我像是渗透了毒汁的花朵,充斥着黑色,无理取闹也来得更频繁。高二我谈了恋爱,跟班上成绩最好的男生,逃课逛街时正好遇到买菜回家的你。我大大方方地向你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你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茫然地看着我,陌生得像是第一次遇见我。
回家前我准备了很多话,没想到你只问我谈了多久,我说今天第一次约会。你木讷地回答了一个字:“哦。”那天我们的话很少,直到晚上躺入被窝,我以为你睡着了时,你又突然出声:“喜欢他?”我闷声说是。“很喜欢?”你追问。“也不是那么喜欢吧。”我说了实话。
也是从那时起,你似乎才意识到我也是会长大的,有一天,也会离开你。于是开始变得患得患失。每天都在校车停站的地方等我。班上不怀好意的学生嘲笑我被你监视,然后议论:“哦呀,她妈妈很小就生下她的传言是真的耶。”第一次直面谣言的压力,那些复杂的目光让我焦灼不堪,像是在强光下被人扒掉了衣服。我闷得慌,想让所有人住嘴,却堵不住那些阴暗的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好更加厌恶我生存的空间,而你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冲你嚷嚷:“你再这么约束我,我就不回来了!”你也很委屈:“我只是害怕……”自此后你由着我,只在不经意时常提醒我要保护好自己。那年我十七岁,深知你的意思,你是怕我重蹈你的覆辙么。心里嘀咕我才不会那么笨,原本想借机询问你的过去,也只是想想。
你私下去图书馆借了好多书回来,我问你干吗,你一本正经地说:“我在为你调制解药。”我反问你:“你十七岁时也是这样中毒么?”你摇了摇头:“我跟你不一样,那时候我是爱的。”这时候窗外有客机经过,嗡嗡嗡的声音像是棉花糖塞满了喉腔。晴朗的天空被画出长长的白线,在遥远的天边扩散成温柔的长团团。心就在那个瞬间柔软下来的,如你所说,成长是一个过程,很快就会好起来。“你还没坐过飞机吧?”我问。你收回视线看着我。“将来,我们一起坐飞机去海边。”这是我对你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约定。
我们是被风吹到宇宙边境的两棵蒲公英,在风沙里艰难扎根。年幼时我不懂,长大后才渐渐体会到你傻笑的表情后,更多的是无奈。你不会责怪别人,也不把恶意当真,那时候我暗暗决定,那么以后就让我来做那个坏人,将风风雨雨阻挡在外。
高三后,面临着志愿的压力,追上文化课的分数实在太艰难,于是选择了做艺考生,当然,这并不单单是逃避,我爱画画,这是真的。我重回卫星的轨道,你欣喜不已。早早地为将来盘算。你又托人介绍了一份兼职,下班后在家装筷子。那天回家推开门,被客厅里堆成小山的筷子吓了一跳,你得意洋洋:“我是所有人里面装得最快的喔!”装一双筷子五分钱,一天最快也只能装三百双。看到你的手不停,我心酸得劝你放弃这份工作,你可怜巴巴地说:“下班回家你也不在,我一个人太寂寞,找点事做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想你了。”
我一直寻觅着你的不同别人之处。你从不用母亲的身份威慑于我,也不用我是你的寄托来严苛于我,更不勉强我完成你未了的梦。“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有你的思想和追求,除了支持你,我什么都不会做。”你沉默一会儿,又接着说,“但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一点都不寂寞。”我惊觉,原来那些说你幼稚鲁钝的人都看错了你。我终究还是像你的,只是他们不知道你骨子里的智慧和坚强。很少有人知道你的好,你是我一个人的宝。
我们是亲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这种关系在很小的时候定性。你不管做什么都会同我商量,并不是潦草询问,很多时候,最后的决定都取决于我的意向。你平等待我,所以我从不吝啬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因如此,你常常感叹我对你太好,从来不和别人一样逼仄你,歧视你。有一次回姥姥家,多日不见,思念冲淡了怨念,姥姥对我们亲得不得了。去厨房取饮料,听到姥姥让你不要太宠我。你笑嘻嘻地答:“是她很宠我才对。”我哪有很宠你,一直都在索取,从来没有给予过。只因我陪在你身边,你便无止尽地信任我。你怎么这么傻。
你爱我出于天职,但已远远超过了母爱的分量。你把爱都给了我。有时我很无措,不知道该怎样做才配得上你的爱。
有时你问我:“小乖,将来我也变成你姥姥那样的人,你会不会离开我?”我闭上眼睛勾勒出你苍老的容颜,独独描绘不出那种凶悍的眼神。我睁开眼睛说你使劲瞪我一眼试试。你便瞪了。光却是散的,软绵绵的汇聚不成一把利刃。于是我说不会。那时候我想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凶的表情。
时间晃晃悠悠地前进,一转眼,春变成了秋,秋迎来了冬。我长高了长大了,而你却好像一点没变。大学我在附近的城市念的,每个周末你都会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家。电话里你的声音总是沙哑的。我担心你是不是又没感冒了,买的药是不是又赌气不吃了,还是又太想念我哭过了……想到这些我立马收拾行囊,天大地大你最大,我哪敢有别的原因冷落你。
姥姥说你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又倔又傻。是的是的。现在连我也时刻为你担心了。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我回家。兴师动众地像是迎接他国来的贵宾。刚吃过午饭你又献上我最爱的水果。“小乖,这是你最喜欢的荔枝喔,你尝尝甜不甜?”你剥开壳递到我嘴边,殷勤得实在过分。下午我躺在窗边画你养的几盆花,你请了假呆在家,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会儿又跟我插上两三句话。过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把沙发也挪到了窗边,对着我的画指手画脚起来。“要不要我给你画一张?”我问。“不用不用。”你连忙摆手。然后好一会儿不再听见你的声音,我抬起头奇怪地看着你,你竟满脸通红,眼神怪异,嘴唇颤巍巍的,似是有什么想说。“你是不是什么都能画?”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心里咯噔一下。
“眉毛很粗,眼睛不大,眼神特别深邃……鼻子啊,比较高那种吧,对了对了,嘴巴超性感的!”你眉飞色舞地比划。“你好色诶!”我笑着碰了碰你的手肘,你顺势拉着我的胳膊靠了过来,“哪个少女不怀春嘛……”
我们花了一下午努力去重塑那个人的容貌,最后的成果却被否定了。“不像不像。”你拿着画看了好久,终于喃喃开口。但走失的表情却让我怀疑,是否真的如你所说。你已经恢复了平静,眼神很无措,似乎突然对我讲述他的容貌有些后悔。但好奇却让我无法到此为止。“好吧,我告诉你。”你叹气,口吻没有戒备,而是非常不舍,像是马上要将非常珍贵的宝物同人分享,但同时也有兴奋。我知道,一直以来,只要我问,你一定会说。
“我们是同学,我一直很喜欢很喜欢他,每天去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他来了没有,如果哪天他请假了不在,我也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高三时他要出国,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出去吃饭,没想到他会邀请我,当他问我能不能参加的时候,我简直……简直……你无法想象,那简直太奇妙了!”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那是十七岁少女的眼睛。
“就是那时候的事么?关于我?”我也来了兴趣,放下画板认真聊起来。
“……嗯。”你腼腆地低下头,“吃晚饭散了之后,他送我回家,因为喝了酒,第二天又要分别,所以想着当时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他也喜欢你吗?”
“嗯!”
“然后……就有了我?他后来有找过你么?”
“对不起……”你抱住我,“他不知道有你存在的。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生下来。自他以后,我觉得我不会爱上任何人了。那种感觉太奇妙了,我甚至怕他回来后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他找没找过我,这对后来的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因为我有了你,什么都不怕了……我这样很自私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的内心又近了一步。看到你这样可爱的样子,完全生不起气来。你怯怯地问我:“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我可以告诉你,只告诉你一个人。”我摇了摇头。你说得对,因为有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也是。关于他,将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梦境。而梦境,不该落入现实里。风风雨雨终将过去,我们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
是吧?妈妈。(选自《萌芽》2012年7月)
青梦
潘云贵
春天刚刚抵达东南小镇时,蔷薇花已经爬满各家院落,墙角有点点红梅挂于疏朗黝黑枝头。风过处,尽是淡淡的香。
青石小道上常有穿蓝印花小褂的女子素面走来,戴青竹编的斗笠,三三两两并肩而行。她们言语清细,落得像丝丝细雨。
这般景致自然是美的。我每次在回家途中遇上这些女子,都会停下来驻足片刻,犹如是在观赏一具具精致花纹的青花瓷器。而这当然不是出于一个被繁冗学业困扰的女大学生对简单女子这般闲云野鹤生活的痴迷,亦不是出于女孩子们对于女人这种成熟群体的偏执向往,而是一种塌陷在回忆里的停留。我是个恋旧的女生。
美,是人类共同的风景。回忆,则是人类共有的习性。二者都会散发出让人上瘾的清香,梦入莲藕深处一般,误了时辰,也应是值得。人事是这一生忘不去的风景,亦如青花般曼妙。
“叶青,你有一件东西要记得还我了。而我也要送你另外一件东西。”
司徒发短信过来的时候,搁在床尾的手机“咯咯”响了两声,仿若短促的鸟鸣,打搅了我本该持续到中午十二点的好梦。
我睡眼惺忪,按下读取键,并特意注意了一下日期:2010年5月2日。
闲来无事的周末里,我总是迷恋于睡眠,一天直立不到九个小时。
我陶醉于梦中那些泡在潮湿中的旧时光。一个人在虚境里形同幼兽,伸出猩红的舌尖舔舐回忆的痂。那些伤口精致得像小瓷器的瓶口,盛放一生悲喜,又若浸染在夕照中的海水,不断的波涛汹涌中发出咸涩的味道,猛烈地撞入胸口。
我是如此爱着海。
“叶青,五月二日,记得和我一道去南澳。”
三天前,他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向我预约。而我正在清洗自己又留了一季的长发,水是从深巷古井取来的,清幽凛冽,慢慢地搓揉,柠檬发液的香气飘满了风里。而这香毕竟是短暂的,经不起深究,顷刻间又被浓郁的芳香所挫败。我知道,这是水仙的香。
当时是黄昏,夕阳卸去他高大细长的影子而延伸向未知的角落。他微笑着,拿过放于窗台的喷水器往水仙花浓密的枝叶上摆弄。叶尖伸展在余晖下,金色的光斑愈发明亮,晶莹的水露在花叶上细致打磨了一阵,又轻挑地溅入水里。风中有小粒尘土扬起,碰到他高挺的鼻尖又缓缓落了下来,打在叶上,又被水滴粘住,混在一起,像低像素的镜头窥见得不太分明。
我一边拿着吹风机,一边看着司徒,像在欣赏一幅色彩均匀舒缓的油画。司徒亦转头看着我,眼睛很干净。他轻轻放下有些许时日没有动用的喷水器,问我。
“叶青,我真怀疑这些水仙到底是不是你栽的?”
话语中带着小小的责备,抑或疼惜,像指间漏下的光粒,细碎得让人想挽留。
有多久没有人这样责备我了呢?自己不禁浅笑起来,双眼也渐变得温润。
这般亲切的、轻柔的责备,如同一只白色的巨鸟透过云层时掉落下的羽毛,一片接着一片,沾染着纯澈又清新的气息,紧紧贴在身体里某个溃烂成军的伤口上,细心抚慰。
我心想应是眼里掉进些沙粒了,便用手轻轻揉了揉。
司徒正站在窗边看我,我也便向他走去,并拿起他刚刚放下的喷水器,继续浇灌瓷盆中的花草,不时轻微地弯下腰身去拔掉那些长得不算好看或是被青虫蛀坏的叶片。
我对水仙花的钟情与疼惜并不亚于司徒,有时甚至超越了他只是简单喷水的动作。
这个男人现在正痴迷地观察着用来放水仙的青花瓷盆,神情专注而天真,像孩子瞧见久未见到的神兽一般。男人瘦削的脸庞亦藏着可爱。
“叶青,这种瓷器怎么会出现在你家?”
他一向都是如此好奇惊然地对待一些人事。而我对他,自然是习以为常。
拥有这个青花瓷盆的人,其实不是我,是祖母。
我一直都很怀念在漳州平和的小日子。
年少的影像里总会浮现出祖母的身影。她亦如世上所有老人一般慈祥,拥有深邃凹陷的瞳孔,脸上漂亮游弋的鱼尾,渐渐脱落的牙齿,一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嗫嚅的婴儿。我喜欢祖母,并热切地许愿,年老后的某天,当自己站在擦得发亮的镜子前时能看见镜子中的自己也同她一样散发出老女人的气质。
祖母时常会一个人头戴镶着印花头巾的斗笠慢慢走到月港那头的海边去,望着远处的海洋用尽一辈子也无法丈量的深情与等待。记得走之前,我都会从漏风的门缝里瞥见她站在镜子前往自己惨白塌陷的脸上补妆,用一些红润的劣质胭脂掩盖那一张失去血色的面孔。她的身子在颤抖,宛若昨夜被雨水打落的红色花瓣,衰败成一地寂然。
我知道,她的年华不再了。
每逢祖母出门,我总跟在她身后,学她缓慢挪步的样子,但每次还是不小心就走到祖母的前头。她慈笑抚摸我留着蘑菇样式的头发,却总也不告诉我深藏在她嘴间仿佛轻轻一抖便会落下的故事。
“阿青,你长成大姑娘后,阿嬷就告诉你。”
她每次总是这么说,然后一个人又安静地向前走去。打耳的海风里,她像去赴一场在夕阳下盛大举行的约会,或是走向总也无法预知的生命尽头。
苍老,一声不吭地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