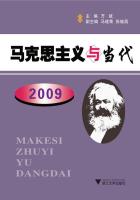在柏拉图那里,真实世界就是理念世界,它的存在是不可见的。在柏拉图看来,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的实体(理式),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即真理,是现实世界中感性事物的本质与原型。理念尤其是善的理念之于现实世界,其作用与影响是规定性的。当然,理念与现实在世界之中发生关联,只是这个世界是二元分立的。在整个世界的结构中,理念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理念寓于世界的结构中,世界赋予理念以全部意义。”([法]让·布兰:《柏拉图及其学园》,商务印书馆,1999,第53—54页。)那么,就柏拉图的美学思想而言,艺术与美的本质在于摹仿。也就是说,艺术与世界之美是摹仿现实世界的,而现实世界则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因此,艺术和美的事物与理念相隔两层,是摹仿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
“然而,在柏拉图看来,现实结构在这种‘审美’背景上无法展示出来。诗人和画家需要的是假象,他们无法把握住存在。”([瑞士]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三联书店,2002,第6页。)原因在于,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虚假的,而艺术与诗却是双重的摹仿。在柏拉图那里,理念对文艺和美的事物具有规定性。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还把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根据柏拉图,美本身就是理念,它是永恒的、绝对的与神圣的。
在美本身与美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柏拉图认为,“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文学出版社,1963,第188页。)在这里,美本身即理念是美的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事物的根本规定。
同时,柏拉图通过对许多具体的美的事物的考察,得出了“美是难的”的结论。世界之美、事物之美总是相对的,它们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们的美也不可能是永远的,只有对美自身即美的理念的把握,才是永恒的、绝对的与无限的。柏拉图把对美的辩论归结为不同的、个别的美的事物所共有的性质,于是美的本质问题就成为了美学的根本问题。
在理念论及两重世界的区分的基础上,柏拉图还提出了迷狂说、回忆说来论证人何以具有这种观照和彻悟美本身的能力。在柏拉图那里,艺术只是双重的摹仿,因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适合作理想国的国王,而他对文艺则采取了贬抑与轻视的态度。
柏拉图认为,文艺创造不是健康合理的思维活动,而是一种丧失了理智的迷狂。文艺只属于情欲,它摧残人的理性、亵渎神明与伤风败俗。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必须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柏拉图所设立的两重世界,即可知的理念世界与可感的物质世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识论及其二元分离的问题,成为了后世美学与形而上学力图克服的目标。
2.人的灵魂的存在、问题与超度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个目的论的体系,他把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理念,灵魂、精神按等级有序地达到最高的善。其实,古希腊的奥尔菲斯教派与毕达哥拉斯已涉及到灵魂的问题,并提出了灵魂不死与转世的思想,而柏拉图继承与发挥了这一学说。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能加以分解的、有生命的和自发性的,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纯粹的,因它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堕落到地上并被圈入肉体中,因此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过程,同时灵魂是会轮回转世的。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也继承了他对灵魂的这种看法并加以描述。在柏拉图那里,灵魂与肉体是相分离的,灵魂是不朽的,肉体则是可朽的。
在这里,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桎梏。为此,“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第72页。)灵魂摆脱束缚,回到其理念这个本源之处。柏拉图关于两重世界的区分表明,只有灵魂才能担当起超度现实世界的重任。但灵魂又是如何超度的呢?这就要靠灵魂的回忆。
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的理念在内的一切理念都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且具有真的知识。理念为灵魂所固有,而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则是与肉体的感官相关联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在一个时候终结后,但在另一个时候又另行投身肉体而再生出来。
由于灵魂投生多次,能获得所有事物的知识,因此灵魂能回忆起前世所具有的美德与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根本看不见洞外的真实世界即理念世界。作为理念,美存在于这真实的理念世界之中。“对这种卓越或完美的最高的、最强有力的反映:善是美的。”(James Alfred Martin,Beauty and Holiness——The Dialogue between Aesthetics and Relig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14.)美本身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排除了感觉的干扰的纯粹思想,才能把握到美德与智慧。
同时,对美的认识与把握,不能凭感觉,也不能靠理智,而只能凭藉灵魂的回忆。人出生后,灵魂被肉体所蒙蔽,就把原来的知识丢掉了。要想重新在灵魂中获得它,人就必须学习,必须作灵魂的回忆。
在这里,学习、认识无非是灵魂回忆起它前世所固有而在投生时遗忘了的知识。在希腊语中,灵魂为psyche,原意为生命的气息,它使躯体具有生命和自我运动的力量,使人体具有认知的能力即思想。在柏拉图看来,“简单地说来,死,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灵魂从肉体中‘释放’;换句话说,这是灵魂独立的成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终身关注的,正是使灵魂力求完满地独立于肉体的命运之外。”([英]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5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家是不害怕死亡的。柏拉图把灵魂不死与转世作为知识来源于回忆的依据,并认为灵魂具有高低不同的理性、激情与欲望三重性。
柏拉图认为,灵魂与神同族,血缘相通,先于肉体而存在。灵魂是一种被视为寓于人体,又可以游离于人体。在人的灵魂中,理性是灵魂的最高原则,是不朽的、与理念相通,是灵魂的本性;激情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是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则指肉体欲望,既可服从理性也可背离理性。灵魂偏离了理性,追求可感世界的欲望,所以像囚禁牢狱一样陷身肉体,灵魂始终面临着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与交织。
亚里士多德将《论灵魂》列为“第二哲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形式,肉体只是质料,灵魂才是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灵魂中有一部分是理性灵魂,它是不朽的,而其余的植物灵魂和感觉灵魂,则是可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灵魂是神所派生出来的。
柏拉图认为,只有皈依天道并以正义和美德为标准,灵魂才能摆脱轮回转世,在天上与诗神一起永享福祉。柏拉图的善与美的关切,“这个意象传承给了新柏拉图主义,尤其是普若克洛斯,然后经过奥古斯丁、托名狄奥尼索斯,进入了基督教的传统,他们一直把上帝赞美为亮、火或光源。”(Umberto Eco,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47.)当灵魂与肉体在一起时,是不纯粹的,必须通过净化,才能把握美德。美本身的理念,是净化了的灵魂所固有的。
在柏拉图那里,艺术不仅是对现实的摹仿,而且还是艺术家的创造。柏拉图的灵感说认为,诗或一般的艺术作品本质上不是人的产品,而是神的诏谕,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柏拉图灵魂观念的提出,为西方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经院美学的建立及其问题
作为西方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理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对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的上帝观念,乃至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柏拉图给予理论以极大的兴趣与关注,并由此去探讨与评价实践。
“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去理解他关于美的观念,他的这个观念被广泛地引入到后来的基督教之中,并用来反映作为神圣美的要素的美的神圣性。”(James Alfred Martin,Beauty and Holiness——The Dialogue between Aesthetics and Relig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14.)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发展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思想。奥古斯丁认为,肉体是唯一实体,而灵魂是加上去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实体形式,是一切生命的与心灵的行为的来源。中世纪神学还认为,灵魂是永恒的,它在人生活时进入,人死亡即离开。
在中世纪,西方美学思想的孕育与产生,除了宗教神学外,显然还受到经院哲学的规定与影响。作为欧洲中世纪特有的哲学形态,经院哲学是天主教教会用来训练神职人员,并在其所设经院中教授的理论。
经院哲学并不主要研究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天主教教义、教条进行论证,以神灵、天使和天国中的事物为对象。在神学的语境里,经院哲学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宗教神学、经院哲学的影响下,中世纪的美学具有了独特的、经院的特征。在中世纪,艺术对美的表现也与宗教的存在密切相关。在教堂里,“不管是镶嵌画板还是壁画,这些艺术品都用来荣耀上帝,或者启发那些来教堂聚会的信徒聆听用演讲和歌声宣扬的基督耶稣的福音同时观赏画。”([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77页。)而且,中世纪美学明显地受到过柏拉图理念论的深刻影响。
柏拉图认为,审美观照是不朽的灵魂的理性所固有的,他以此排斥审美快感。无疑,这也影响了基于实践理性的经院美学。经院哲学发生于欧洲的基督教教会学院,它标志着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第二次全面兴起。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初期,最初流行于巴勒斯坦的下层犹太人中间,后来传播至整个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基督教会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世纪早期,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主要致力于《圣经》与教义的阐释,当时的美学与哲学一样受制于神学及其论证。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对经院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的成果,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使中世纪经院哲学达到了鼎盛。
根据亚里士多德,具体事物既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与上帝相关联,并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形式与质料等范畴,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作为中世纪哲学的一部分,中世纪美学被置于神学的规定之下,并没有出现专门意义上的美学家,但尚可从哲学、神学的一般框架之中,梳理出中世纪美学的一般情况。在柏拉图哲学中,与理念相关联的种、属与类的涵义,到了中世纪被归结为上帝的属性,而不再具有实在性了。
基督教把圣父、圣子、圣灵称为三位一体,相信只有一个唯一的上帝。公元二世纪的护教士阿里斯蒂德,解释了基督徒为什么拒绝接受希腊和罗马的神灵,“他说,这些神是人造的,因此根本就不是神;而且,他们被赋予了和人共有的缺点和罪行。”([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8页。)这从一个方面,阐明了中世纪的一元神上帝的根本规定性。
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的美学思想以流溢说为中心,认为物质世界的美是由于分享了太一的结果。他第一次把美学问题置于哲学体系之中,并且最先把美学转向神学,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美学思想。普洛丁受到过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但他又比柏拉图的理论更精致,也更神秘。
在对待文艺的问题上,教会的态度也有着一些变化,起初教会一味地反对文艺,后来它则转而利用文艺为宗教的宣传服务。为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同美的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欧洲后世神学的终极根源,就在于《理想国》中那一伟大的譬喻:把太阳和它的光比做是绝对的善及其表现的产物和象征。”([英]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第64页。)经院哲学家都承认上帝的存在,一些人还利用《圣经》,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上帝的存在作出系统的论证与阐明。
4.上帝、美的规定与神圣之美
在早期,柏拉图主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试图运用归纳的方法,从具体的伦理道德行为中,探求美的定义。到了中期,他才提出了理念论。“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31页。)在奥古斯丁看来,对于人类而言,有事物的美、形体美与灵魂美,还有感性美与理智美,可感世界有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美。
然而,所有这些美都来自上帝的创造。到了中世纪,神成了一元神即上帝,此时的美学已被纳入到了神学之中。中世纪美学不是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简单的延续与重复,而是把美学作为神学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并加以阐释。
在神学中,美是上帝的一个根本属性,这是早期基督教思想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帝对中世纪艺术与美的规定性,当然离不开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作为形而上学的开端,柏拉图把存在把握为理念。在柏拉图看来,以理念世界为对象获得理性认识,直到转向终极的善理念,它是万物最高的终极目的,是一切存在的原理与认识的极致。
因此,中世纪存在的问题就是上帝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经过古罗马的普洛丁,对上帝是至美的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普洛丁把基督教神学和东方神秘主义,融于柏拉图的美的理念说之中,认为最高理念即太一或神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显然,普洛丁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导向了神秘主义。普洛丁不仅肯定了理念世界的存在,而且把最高的理念说成是太一、神。在他看来,太一是至美的、完满的,而事物本身无所谓美,只有当它分享到神所放射的理念的光辉时,它才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