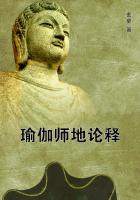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概述
中国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之初。它继承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的传统,吸收了世界进步与革命文学的优秀元素,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建国后一段时期,由于漫长的封建文化的禁锢,人民旧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规范的形成、文化意识的转变显得非常缓慢,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要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人们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国后几十年对人们的行为都有一定影响。
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赞美社会新风气,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
受到这种战争心理的影响,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领域,一方面,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战争心态的词汇,战争文学观念成为主流。
但与此同时,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重视文学自身价值这一传统有力地支持了作家们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达对社会的理性看法,以及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正是因为坚守这一传统,许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利以后,仍然抱着对文学的炽爱,在秘密状态下创作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熟悉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对农民的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也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反映出来自于生活最真实的呼声,极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们认识到,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化规范及其文化心理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为了调整这种不相适应性,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试图纠正这种文学发展的倾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收效甚微。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学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除了“样板戏”和部分诗歌外,文字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有关“文革”期间的文学状况,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当代文学史的第三阶段是以1978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在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中央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显露端倪。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旧有的文化规范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人们旧有的传统思维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譬如,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绝的态度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决定了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痛苦的文化蜕变和激烈、充满矛盾的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每一次争论都为推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作家们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整个80年代的文学显得生机勃勃。
“文革”结束后,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终于爆发出了现实战斗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在“文革”后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中,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活。
这一阶段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却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于社会及人性的感性认识,而在“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与打击。“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历“上山下乡”,真实体验了民间生活,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文学新创作趋向。
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使得许多作家在实践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的文学创作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拨乱反正的过渡时代,那么,90年代才渐渐显现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点。这种新的特点,对未来的文学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方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旧有的一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文学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90年代,新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种新的因素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等。“共名”是时代主题的体现,是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自身的理解,对时代关键词进行阐述,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真实的感受很可能会被掩盖。
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学创作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不同专题,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思潮之间互相冲突,充满了激烈斗争。
90年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无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鸣的现象,不同风格、不同类型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以及民间文化结构,文学走向呈现多样性。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鼓励来肯定其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认可、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过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文化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
90年代有许多作家对于社会以及社会历史的认识非常相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面貌,作家的叙事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以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风格更加多样化、自由化,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0年代的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转向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则着眼于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有的则专注于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这种“无名”状态使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
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10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为本世纪的文学舞台拉上了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建国初期的中国文学概述
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页。这次大会确定了我国文艺运动的方针和任务,促进了文艺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文艺界就在酝酿和讨论着革命文艺的新使命这个问题了。1949年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文艺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成立新的全国性文学艺术界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7月2日,第一次文代大会正式召开,会议代表824人,郭沫若为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这次大会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在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祝贺大会的召开,并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宝贵的意见。朱德说,“我们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难以后,将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在经历困难时期并且克服自己的缺点以后,一定也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这就是党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对文艺大军的期望。
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主席也亲临会场,向代表们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无论是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还是毛泽东主席的讲话,都包含着一个中心思想,即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艺事业得以繁荣的首要前提。
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来讨论文学艺术工作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作出决议:“一致认为他们所指出的在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还在“大会宣言”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
最后,大会产生了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等。
第一次文代大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开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次大会根据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确定了文学艺术的总方针,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力歌颂在革命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农民、解放军。郭沫若在开幕词中明确主张,“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他从分析“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入手,说明了文艺必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是文艺得以兴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