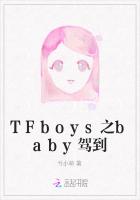育辉
刘半农在北京的最后几年,与其二弟刘天华以及三弟刘北茂均在北大执教。
1932年5月的一个周末,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刘氏三兄弟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均在天华先生家欢聚,大人叙家常谈事业以及各自的见闻,小孩子们则嬉戏玩耍,一派欢乐、活跃、和睦的景象。但那次周末聚会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半农先生的一席谈话,他由当时反动当局的文字狱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而谈到他在北大和编辑《新青年》时期共过事的李大钊同志。半农先生感叹地说:“大钊先生忧国忧民,却死于军阀张作霖之手,至今已四、五年了,他的灵柩还停放在宣武门外的淅寺,不得安葬。我一直在考虑,想联络一些人,活动活动,看有什么办法解决他的安葬问题,人死了还得‘入土为安’嘛!但看起来这事很麻烦,首先当局一关就不好通过,那些掌权的军阀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我手头还保存着大钊烈士的一篇亲笔诗稿,另外我还有鲁迅和陈独秀等几位作者的诗歌原稿,这点稿子已不可多得,尤其是大钊那篇《山中即景》现在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我想如能把这诗稿影印出版了,也算是做了一点对死者的纪念吧,活着的人心里也宽慰些。为了这些稿子,我曾想方设法,但也没能够出版;还有人来劝我说:‘就不要再拿出来了,免得找麻烦,弄得不好还要坐牢。’其实我也不怕坐牢,我还没有尝过坐牢的滋味呢!我盼望将来总有一天把这些诗稿拿出来影印出版。”
半农先生继续说:“记得大钊先生就义的前一年,我曾去看望他,当谈到当年的‘三·一八’惨案时,大钊先生义愤填膺,痛斥了军阀段祺瑞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他用拳头击着书桌喊道:“渗无人道!简直是惨无人道!’后来他留我吃饭,对女儿说叫妈多添两个菜。吃饭时端出来的是:炒黄豆芽、肉片炒豆腐、炒木须肉和鸡蛋汤。”天华先生听到这里很感兴趣地说:“炒木须肉和鸡蛋汤可能就是添的菜吧,大钊先生生活很俭朴啊!”半农答道:“是啊!他身为北大的名教授,生活却很俭朴,他对穷学生穷朋友却常解囊相助,毫不吝啬。”这时天华的夫人殷尚真好奇地问道:“大哥可见到这位教授夫人没有?”半农先生说:“吃饭时没出来,饭后我对大钊先生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来了几次,嫂夫人也没有出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时大钊就出去了,我透过玻璃窗,看见大钊先生在对面屋里弯着腰在给他夫人整整衣角,拍拍灰尘;大钊夫人进来时,身穿一件普通旗袍,略带乡土气,但谈吐不俗,看上去比大钊要大几岁的样子。”半农先生娓娓而谈,大家凝神静听,不禁都肃然起敬。
半农先生所收藏的那些白话诗稿,有的作品还残存着旧诗的痕迹,但他仍十分珍视这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成果,并形象地比喻道:“即使是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也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经过他不懈的努力。那部新诗原稿终于在1933年春以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名义影印出版了,书名为《初期白话诗稿》,包括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沈尹默等九位诗人的二十六篇新诗原稿。白话作为“五四”时代白话诗园中的一名拓荒者,成绩卓著的诗人刘半农先生却没有将自己的诗稿收入。他在序言中强调说,为了使“同好的人购买起来方便些”,已与出版商说好“我也不要拿稿费,你也不要定高价”。《诗稿》出版后,受到文艺界的关注与好评。
《诗稿》出版月余,在北京地下党和北大进步师生长期的筹划下,大钊烈士的灵柩终于决定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半农先生在欣慰之余,即于当年四月十日邀请其好友钱玄同等十二人联名发起了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公葬时,党组织曾指定专人事先准备好一块刻有镰刀斧头图案党旗,并撰有文字的石碑。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共产党的石碑公开竖立在墓地上的,于是送葬的同志临时决定,将这块石碑随大钊烈士的灵柩一起埋入地下。
事隔月余,比大钊同志长六岁的夫人赵纫兰也不幸病故,大钊同志的友人遂公推刘半农先生来撰写碑文。半农先生毅然命笔,其中一段写道:“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减,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主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措词含蓄的碑文,在风凄雨横的1933年也不能公开采用。作者不得已,遂又改用工整道劲的唐人书法分别给李大钊烈士夫妇写了仅有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和五个遗孤姓名的墓碑。书写时半农先生十二岁的次子育伦在一旁帮着铺纸磨墨。先生心情沉重,只是低头写字,连写了几张才觉得满意。写完后,他语重心长地向孩子解释说:“写某年某月某日死,用‘死’而不用别的字,是表示‘死’于非命或暴力。是对军阀的控诉!”
一年以后,1934年夏,半农先生带领北大师生去内蒙一带考古和调查方言,不慎染回归热症,抱病回京仅一周即溘然长逝。
(载《江南论坛》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