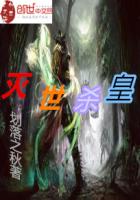朱成国从昏迷中醒来,吩咐师爷给了郎中十个大洋,送回洋河镇。
朱成国养伤期间最痛苦不是趴着,而是每次大解,尽管特制了一张床,从中间挖开一个洞,躺上去从洞中漏下屁股,但每次都会撕裂伤口。帮他擦屁股的人更要小心,弄疼了,朱秃子张口便骂,动之挥拳。师爷为此专们从偏远村落骗来一名中年妇人,说是侍候月子。
这天,朱秃子觉得屁股疼痛稍有缓解,将众兄弟招集到身边团团围坐。
“师爷,伤差不多好了,把临河镇粮店撤到洋河镇,换地方扎营。”
“朱爷,真要走呀,这仇咱可不能不报呀。”丁二毛委屈地说。
“报仇容易。养伤这几****想过了,要做大事别在自家门前折腾。况且我们也要提防刘少堂,如果此时他联手其他民团围攻我们,我们必输。好在这场迟迟不退的大水,帮了我们。”
朱成国一席话让众匪沉默不语,细思极为有理。
“给镇上派出所长房向东的大洋要快点送去,别让那条狼等急了,他可是不见钱就呲牙的主,在我们撤离之间,不要节外生枝。”朱师爷说。
“我不想离开临河镇。”丁二毛说。
丁二毛自从跟了朱秃子,早被父母赶出门,离开朱秃子他是一条落荒野狗,无处藏身。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朱成国安慰众人。
“派人找曹老六了解对岸的情况。你们都回吧,没事别到这里来走动,这段时间不许扰朱庄以及周围村民,喝酒吃肉只能在院里,更不许出去找女人,有违抗者按帮规处罚。”朱成国说。
四
朱成国的分析不无道理,倒不是刘少堂急于过河报复,而是另有其人,此人是冯信之,冯锦汉的父亲。
冯信之进入刘圩子土楼,是后半夜,刘少堂在梦中被叫醒了。
更夫首先叫醒了倪瑞轩,如今他睡在刘家大院门房里,任何人进入土楼都要经门房,会见刘少堂也需倪瑞轩先审定同意方可引见。
冯信之进入门房从怀里掏出两块大洋双手捧着恭敬的递给倪瑞轩,被坚定地回绝了。这一举动令冯老先生深感刘少堂治家之严,似乎由此找到朱秃子失败原因。
“请问你是刘家少爷吗?”冯信之问倪瑞轩。
“不,我倪,是刘家护院。”倪瑞轩经历朱秃子抢人的事件后,成熟了许多。他听从了刘少堂的训诫。
对陌生人千万不可轻易说出真实身份,不要轻信任何人;逢人留一手,才能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刘老爷治家如此严谨,老生敬佩。”冯信之由衷的说。
“老先生过奖,请问您深夜到此有何指教。”
“本人是土梁村的冯信之,登贵府拜会刘老爷,有要事相商,烦请通报。”冯信之说着递上一封信。
“刘老爷睡了,再说是后半夜,多有不便,麻烦你明天来吧。”倪瑞轩说。
“小兄弟,听说过土粱村冯家小儿被朱秃子剥皮的事吗?”
“听过,多年前的事了。”倪瑞轩答。
“正是。这是我小儿冯锦汉。”冯信之拉过身后一后生。
冯锦汉个头刚及倪瑞轩眉宇,眉毛粗重,双眼清澈,透着虎虎生气。因为走了夜路,圆口黑布鞋满是尘土,父子俩神情透着远途跋涉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