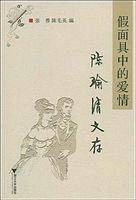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日本“新感觉派”骁将之一。1968年以《雪国》、《千鹤》、《古都》三部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语言魔术师”的美誉。おお
[日] 川端康成
春花秋月夏杜鹃
冬雪寂寂溢清寒
这首和歌,题为《本来面目》,为道元禅师镰仓(1192—1333)初期的禅僧,1223年入宋,受曹洞宗禅法和法衣回国,而后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1200—1253)所作。
冬月出云暂相伴
北风劲厉雪亦寒
而这一首,则是明惠上人镰仓时代华严宗僧人(1173—1232)的手笔。逢到别人索我题字,我曾书赠这两首和歌。
明惠的和歌前,冠有一段既长且详的序,像篇叙事诗。用以说明这首诗的意境。
元仁元年(1224)十二月十二日夜,天阴月晦,入花殿坐禅。中宵禅毕,自峰顶禅堂返山下方丈。月出云间,清辉映雪。虽狼嗥谷中,有月为伴,亦何足惧哉。入方丈顷,起身出房,见月复阴,隐入云端。比及闻夜半钟声,方重登峰顶禅堂,月亦再度破云而出,一路相送。至峰顶,步入禅堂之际,月追云及,几欲隐于对山峰后,一似暗中相伴余矣。
这篇序后,便是上面所引的和歌。和歌之后,作者接下去写到:
抵峰顶禅堂,已见月斜山头。
登山入禅房,
明月亦相随。
愿此多情月,
伴我夜不寐。
明惠上人是在禅堂守夜,抑或在黎明时分重返禅堂,他未加说明,只是写到:
坐禅之时,得闲启目,见晓月残光,照入窗前。余身处暗隅,心境澄明,似与月光融为一体,浑然不辨。
心光澄明照无际月疑飞镜临霜地
西行西行(1118—1190),平安朝末年诗僧。有“樱花诗人”之称,故也有人相应称明惠为“咏月歌者”。
月儿明明月儿明
明明月儿明明月
明惠此诗,全由一组感叹的音节连缀而成。至于那三首描写夜半至清晓的《冬月》,其意境,照西行的说法,“虽是咏歌,实非以为歌也”。诗风朴直、纯真,是对月倾谈的三十一音节。与其说他“以月为友”,勿宁说“与月相亲”;我看月而化为月,月看我而化为我,月我交融,同参造化,契合为一。所以,僧人坐在黎明前幽暗的禅堂里凝思静观,“心光澄明”,晓月见了,简直要误认是自身泻溢的清辉了。
“冬月出云暂相伴”这首和歌,正如长序所说,是明惠在山上禅堂坐禅,参悟宗教与哲理,其心境与明月契合相通的诗。我之所以书录此诗,是因为据我体会,这首和歌写出了心灵的谐美和通达。冬月啊!你在云端里时隐时现,照耀我往返禅堂的脚步,所以狼嗥也不足畏;难道你不觉得风寒刺骨,雪光沁人吗?我认为这首诗,是对大自然,以及对人间的温暖、深情和慰藉的赞颂,也是表现日本人慈怜温爱的心灵之歌,所以,我才题字赠人的。
矢代幸雄博士以研究波提切里波提切里(SandroBotticelli,1445—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而闻名于世,对古今东西方美术,学识渊博。他把“日本美术的特质”之一,概括成“雪月花时最怀友”这样一句诗。无论是雪之洁,月之明,也即四季各时之美,由于触景生情,中心感悟,或因审美会意而欣然自得,这时便会思友怀人,愿与朋侣分享此乐。也就是说,美者,动人至深,更能推己及人,诱发为对人的依恋。此外的“友”,广而言之是指“人”。而“雪”“月”“花”这三个字,则表现了四季推移,各时之美,在日文里是包含了山川草木,森罗万象,大自然的一切,兼及人的感情在内。这三个表现美的字眼,是有其传统的。即以日本的茶道而言,也是以“雪月花时最怀友”为其基本精神的。所谓“茶会”,也即“感会”,是良辰美景、好友相聚的集会。——附带说一下,我的小说《千鹤》,倘若读后认为是写日本茶道的精神与形式之美,那便错了;这是一篇持否定态度的作品,针砭时下庸俗堕落的茶道,表示我的疑虑,并寓戏戒之意。
春花秋月夏杜鹃
冬雪寂寂溢清寒
道元的诗句,也是对四季之中美的讴歌。诗人只是将自古以来日本人民对春夏秋冬四时最钟爱的景物随意排列起来,你可以认为,没有比这更普通,更平常,更一般的了,简直可说是不成其为诗的诗。但是,我再举出另一位古人的诗,与这首诗颇相似,是僧人良宽(1758—1831)的辞世诗。
试问何物堪留尘世间
唯此春花秋叶山杜鹃
这首诗与道元那首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事,平平常常的字,与其说良宽是不假思索,毋宁说是有意为之的,在重叠之中表达出日本文明的真髓。更何况这是良宽的辞世诗呢。
漠漠烟霞春日永
嬉戏玩球陪稚童
暂伴清风和明月
为惜残年竟夕舞
非关超然避尘寰
平生只爱逍遥游
良宽的心清和生活,如同这些诗作所描述的,住草庵,穿粗衣,闲步野外,与孩童嬉游,和农夫谈天,不故作艰深语,奢谈深奥的宗教和文学,完全是一派“和颜温语”,高洁脱俗的言行。他的诗风和书法,均已超越江户后期,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以及日本前近代的习尚,臻于古典高雅的境界。直到现代,日本仍极其珍重其墨迹和诗歌。良宽的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辞世之情,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也不想留下什么。死的死去,大自然只会更美,这才是自己留存世间唯一可资纪念的。这首诗凝聚了自古以来日本人的情愫,也可从中听到良宽那虔敬的心声。
久盼玉人翩然来
今朝相会复何求
良宽的诗作里,居然还有这样的情诗,而且也是我喜欢的一首。良宽到了六十八岁垂暮之年,得遇一位二十九岁的年轻女尼,深获芳心,成就一段良缘。这首诗既表达他结识一位永恒女性的喜悦,也写出他望穿秋水,久候不至的情人姗姗而来时的欢欣。“今朝相会复何求”,诗句质朴真切,感情纯正。
良宽七十四岁圆寂。生在多雪之乡的越后,同我的小说《雪国》写的是一个地方,现在叫新NFDAFO兀地处内日本的北部,正好承受从西伯利亚横越日本海吹来的寒风。良宽的一生,便是在这样一个雪乡度过的。人生渐渐老去,自知死之将近,内心已趋彻悟之境。这位诗僧“临终的眼”里,想必也像他绝命辞中所写的那样,雪乡的大自然会是更加瑰丽。我有一篇随笔,题为《临终的眼》。但此处“临终的眼”一语,是取自芥川龙之介(1892—1927)自杀时的遗书。芥川遗书中这句话于我铭感尤深:“大概逐渐失去了”“所谓生活的力量”和“动物的本能”云云。
如今,我生活的世界,是像冰也似透明的,神经质的,病态世界。……我究竟要等到何时才敢自杀呢?这是个疑问。唯有大自然,在我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美。你或许要笑我,既然深深喜爱这大自然之美,却又想入非非要去自杀,岂不自相矛盾!殊不知,大自然之所以美,正是因为映在我这双临终的眼里之故。
一九二七年,芥川龙之介以三十五岁的英年自杀身死。我在《临终的眼》一文中曾说:“不论怎样厌世,自杀总归不是悟道的表现。不论德行如何高洁,自杀者距大圣之境,终究是遥远的。”我对芥川以及战后太宰治(1909—1948)辈的自杀,既不赞美,也不同情。但是,有位友人,日本先锋派画家之一,也是年纪轻轻便死去了,他也是很久以来就想要自杀的。“他常说,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死即是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见《临终的眼》)。依我看来,他生于佛教寺院,又毕业于佛教学校,对死的看法,与西方人的观点,自是有所不同、“有牵挂的人,大概是不会想到自杀的”我因此联想起那位一休禅师(1394—1481),他曾经两次企图自杀。
这里,我之所以要在一休之前加上“那位”两字,是因为在童话中,他作为一位聪明机智的和尚,已为孩童所熟悉。他那奔放无羁的古怪行径,已成轶闻广为流传。传说“稚童爬到他膝上摸弄胡子,野鸟停在他手上觅食啄粒”,是为无心禅宗主张“但能无心,便是究竟”,而“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真理)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62页。的终极境界。看上去他似乎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其实,也是位极其严肃、禅法精深的僧人。据说一休是天皇之子,六岁入寺,一方面表现出一位少年诗人的天才,同时也为宗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苦恼不已。他曾说:“如有神明,即请救我;倘若无神,沉我入湖底,葬身鱼腹!”就在他纵身投湖之顷,给人拦住了。后来还有一次,一休住持的大德寺里,有个僧徒自杀,致使僧众几人牵连入狱,这时,一休自感有责,“肩负重荷”,便入山绝食,决心一死。
一休把自己那本诗集,取名为《狂云集》,甚至以狂云为号。《狂云集》及其续集,以日本中世的汉诗而论,尤其作为一位禅僧的诗作而论,是无与伦比的,其中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诗,描写闺房秘事的艳诗。他饮酒茹荤,接近女色,完全逸出禅宗的清规戒律;大概是想从中自求解脱,以此来反抗当时僵化的宗教形式,要在因战乱而崩溃的世道人心中,恢复和树立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