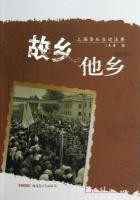有时候,我没有泛舟湖心,而是沿着葱绿的岛岸游弋,那清澈的湖水常常诱我跳进湖水。不过,我走得最多的水线是从大岛到小岛。在小岛上岸,在那儿度过午后的时光。时而在柳树、泻鼠李、春蓼与灌木丛中作举步维艰的散步;时而伫立于某个小沙丘上。那上面覆着细草和欧百里香,甚至还有岩黄芪和三叶草,好像从前曾有人把种籽撒在那儿似的,这里特别适宜兔子栖息,它们可以在那儿平平安安地繁衍,既不必担惊受怕,又不会伤害什么。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税务员。他便从沙纳泰尔弄来了一群公兔和母兔。他的太太、他的姐姐、戴莱丝还有我,我们一起煞有介事地把兔子安置到了那个岛上。在我离岛之前,它们开始生育后代了。倘若能够耐得住数九隆冬的严寒,那它们一定子孙成群了。建立这个小小“殖民点”,就成了一个大好日子。当我神气十足地率领着同伴们把兔子从大岛迁往小岛时,就连阿耳戈英雄们希腊神话中的五十来个希腊英雄,他们登上阿耳戈船,在伊阿宋的指挥下前去科尔喀斯夺取金羊毛。的舵手也不会有我那么自豪。我十分得意地注意到,那位对水过分恐惧、往往见水就昏的税务员太太,那天在我的带领下满有信心地上了船,在整个航程中没有半点惊慌神色。
当湖水激荡,不能泛舟时,我就在岛上度过我的下午,到处溜达,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坐在最招人喜爱而又最僻静的角落纵情幻想,有时坐在土台或山丘上,骋目全湖和沿岸旖旎迷人的风光;湖的一侧有近山环绕;另一侧则伸展着一片富饶而肥沃的平原。极目远眺,一直可以望见远处遮挡住视线的淡淡的青山。
黄昏将近时,我从岛的高处下来,信步来到湖边,坐在某个隐蔽处的沙滩上;涛声阵阵,湖水翻腾,吸引住我的情思,驱除了我心头因别的事引起的激动,使我整个心思沉浸在柔美的遐想之中。这时间,夜晚常常悄然而至,而我还没有察觉。湖水在我眼前时涨时落,喧哗不止,时强时弱的波涛声,不停地在我耳边喧腾。它们取代了我那因幻想而停止了的内心活动,不费心神就足以使我愉快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我时不时泛泛而短暂地思考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不稳定性,水面恰好给我提供了这种不稳定的图景。但是这些浅淡的印象很快就消失在这种单调的持续运动中了。那持续运动安抚着我,用不着我的心主动配合,就不停地把我吸引住了。到了钟点和事先约好的信号把我召唤时,我得很费些劲儿才能从这状态中脱身出来。
晚饭后,每当夜空晴朗,我们还要一块儿到土台上散散步,呼吸湖上的气息和清新的空气。我们到凉亭歇脚、嬉笑、聊天,哼一支古老的歌曲,它比那扭扭捏捏的现代歌曲可就强多了。末了,各自带着对这一天的满足心情回去就寝,一心巴望明天还要这么度过。
撇开那些令人厌烦的不速之客不谈,我在圣皮埃尔岛上勾留,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简直可以这样说,那里的东西太有吸引力,足以唤起我心中如此强烈、如此柔美、如此持久的怀念。十五年后,每当我想起这个可爱的地方,仍因热烈的向往而恍如身在其中。
我在漫长岁月中历尽沧桑,我发现,具有最甜蜜的享受和最强烈的快感的时期,并非那些常引起回忆或最使我感动的时期。那些一时的狂热和心血来潮的时刻,无论多么热烈,却恰恰因为本身的热烈程度而仅仅成了生命线上一些稀稀落落的点。这些点为数太少、稍纵即逝,不能形成一种状态。可我心所怀念的幸福,断乎不是由一些瞬息即逝的时刻,而是由一些平凡而持久的状态构成的。这些状态本身并不强烈,但它们的魅力却随着岁国的流逝而骤增,最终能够从中找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连续的波动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保持它的一种固定而永久的形式。因此,与外界事物相因而生的情感,必然与它们的变迁而一起变异。我们的情感常常在我们之前或在我们之后,去追忆那不可再得的过去,或去预想那也许远不会有的未来,总之,没有一件坚实的东西可以作为心灵的依托。由此可见,世间有的只是逝去的欢乐,而所谓持续的欢乐,我很怀疑它是否存在过。我们难得有享受十分强烈的那么一刹那,而足以使我们的心真正能够说出:“愿这一刹那长此下去。”既然如此,我们怎能把这样一种瞬息状态——它只给心中留下不安和空虚,只留下对过往某些事物的悔恨和对今后某些事物的希求——称为快乐呢?
但是假设有这么一种状态,在那里,心灵能够找到一个坚实的位置,整个儿地静息在那里,并在那里聚集它整个的存在,既不必追怀过去,亦不必思考未来;在那里,时间对于它是虚无的,“现时”一直延伸着,但又不显出它的连续性,不显出它那相继接续的印迹;在那里,除了惟一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以外,再无贫乏或享受,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更无希冀或恐惧的感觉。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惟一的感觉就能够把我们的心灵完全充实。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一天,凡是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就都可以称自己是幸福的人。这种幸福并非来自那种不完全的、贫乏的、相对的幸福,就像我们在人生乐趣中所感到的那样。而是源于一种丰盈的、完备的、充实的幸福,它不给心灵留下半点空虚之感,使它需要填补。我在圣皮埃尔岛上,有时躺在船中随水漂移,有时坐在汹涌的湖水边,要么坐在景色秀丽的江边,或是水流穿经铄石潺潺作响的溪边独自遐想时,常常处于这种状态中。
在这种境界中享受到的是什么呢?这绝不是自己身外的东西,除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存在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只要这种状态持之以恒,人就和上帝一样心得意满。排除异念而感到自身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和宁静的珍贵情感。它足以使每个善于排除世俗的和肉欲的杂念的人感到自身存在的珍贵和甜美。因为世俗的和肉欲的杂念总是不断地分散和扰乱我们对生活在人间的甜美感觉。但是,人类的绝大部分,由于不断受到各种情欲的纠缠,他们很少能够感受到这一境界,或者只有片刻的尝试,因而对此只有一种含糊不清和混乱的观念,不足以感到那其中的韵味。按照现在的事物结构,他们若是渴望这些甜蜜的沉醉而讨厌积极的生活,那甚至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对生活不断产生的需要给他们规定了义务。然而,一个不幸者,断绝了和人类的交往,再不能做点于他人、于自己有用或有益的事情了,在这种状态中,他却能找到人生的至乐极福,作为补偿。这才是命运和人所无法从他那儿夺去的。
诚然,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境况中能体会到这些补偿。那就需要心地平和,不能有任何情欲来打扰这种平静。需要有感而发的内心情境,需要把内心情境与四周的客观事物相融合。绝对的安息和过分的激动都是不需要的。但必须有一种均匀而适度的内心活动,没有波动和间隙。没有内心活动,生命就不过是麻木的东西;它若是不平衡或过于激烈,它就会惊醒。当它使我们意识到了四周的事物,它就会败坏我们遐想的魅力,把我们从自身中分裂出来,使我们重新回到财物和人类的束缚中,再度感到我们的诸般不幸。过于沉静会令人生悲,出现死亡的阴影,因此就需要借助于一种令人快乐的想象力。上天曾赋予他们以想象力的人们自然会得到这种援助。这时,不是来自外部的内在情感便在我们内心产生了。静下来的时候比较少,但是当一些泛泛的、愉快的思考只是轻轻掠过心灵的表面不激动它的深处时,沉静也同样是令人惬意的。只需要足够的思考就能回忆起自己,而把痛若忘却。无论在哪里,只要能够静下心来,就可以去幻想。我常常想,若是把我囚在巴士底狱或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我也仍然可以悠然幻想。
但是,还得承认,在这个富饶而僻静,受着大自然的限制、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悠然遐想,可就更加自由、更加惬意了。在这儿,一切都给我提供了令人愉快的景象,没有任何东西勾起我对痛苦的往事的回忆。与少数居民的交往,亲切而温柔,并不十分有趣,不会没完没了地占用我的时间;在那儿,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成天恣情于令我感兴趣的事物和最懒散的悠闲生活中。一个幻想家,他若能从令人生厌的事物中提炼出令人快慰的幻想,借助于所有感动他五官的一切,若能陶醉其中,其乐融融,那么,这个机会对他无疑就是绝妙的了。当我从长久和甜蜜的遐想中觉醒过来时,发现周围是绿茵和花岛,当我骋目于远方那环绕一汪清澈晶莹的宽宽水域、富于浪漫色彩的堤岸时,我把每一件可爱的东西都融化在我的想象中了;最后,当我逐渐清醒,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时,我简直分辨不出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在那逗留的愉快时光中,所有一切都使我这种沉思与幽静的生活变得亲切可爱了。我为什么不在这岛上度过余年,永远不出岛,见不着一个陆上居民?他们总是令我回想起这些年来那伙人对我的加害。我很快会把他们忘掉,但他们不会忘掉我的。但只要他们再不能打搅我的平安,我也就不计其他了。当我把社交界的纷扰所引起的尘世的欲念摆脱掉了之后,我的灵魂就常常超越了这个氛围,去与天使们提前交往了——它还希望尽快有更多的天使。我明白,人们不会还给我这么一个温柔的避难处了,他们原先也是不愿意让我到那儿去的。但他们阻挡不了我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那儿,领略几个钟头的快乐,好像我还住在那里一样。我在那儿能够做的最甜蜜的事也许就是纵情幻想,当我把自己想象成在那儿时,岂不与真的在那儿没有两样吗?有时想象比真的还真哩,因为我把那迷人的图景融进深奥而单调的幻想之中了。当我心驰神往,这些景物往往超脱了我的感官意识。现在,我幻想得越深入,幻想中的景物就越清晰,与当初我真的待在那儿时相比,如今我似乎更加身临其境,更加其乐融融。不幸的是,随着想象力的衰竭,我的幻想越来越困难,而且不能持续多久了。唉,人行将脱离自己的躯壳时,却被它裹得最紧。
张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