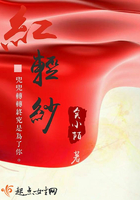纪德(1869—1951),法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几十年常为许多读者所嗜读,在青年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代表作品有《地上的粮食》、《背德者》、《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等,一九四七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おお
[法] 纪德
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现在已开始返航。同乍得湖边境地区告别,心中的确有点怅惘。以后我恐怕没有勇气再来了。
但愿能找到,休问在何方。
轮船停靠在一个小岛上过夜,周围全是纸莎草丛,虽然有一个避风之所,但船身整夜颠簸跳动,链条吱吱呀呀,小艇互相碰撞,加上开门关门的声音,使人完全无法安眠。
很早起锚,连连搁浅。水花溅到后甲板上,我们真不知道把床和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才算安全,真有无地容身之感。看来勇敢的船长也被弄得晕头转向,他先试了一下沙里河的一条汊道,但很快发现是不能通航的……多方尝试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再度向北航行。
船终于进入流水里了。岸边只有高大的芦苇,河岸也慢慢升高,还有巨大的白蚁巢。
我们沿着沙里河的左岸(属喀麦隆)航行,岸上森林覆盖,虽不很高,却非常茂密。参天的巨树,形成了宽大的拱顶,缠满了藤本植物。在这一带,像这样的景色还从没有见过。我真想下船去看看这一片神秘的树林,其实只要叫船长停船就行了,因为他已经同意,船的行动完全由我们随意支配。刚好轮船经过了几处没有芦苇的地带,在这儿停船登岸是最方便的。为什么我没有下令停船?是害怕打乱了航行的计划?是担心其它我料不到的原因?原来我非常讨厌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摆架子,发号施令。好时机错过了,森林已开朗,河岸只有一片芦苇,这时我终于和船长商量停船。船长也需要停船砍伐木柴,他说到附近的林边停靠。船停了,我们登岸。河岸陡峭,但借助葛藤可以攀登。马尔克带了一支借来的荷兰造猎枪,我也带了我的猎枪和充足的子弹。阿杜姆跟在我们后面。这片森林真糟,不如起先见到的茂密、阴森。藤本植物很多,树木不那么老,丛林不那么深。一想到刚才没有去看那片森林,我心里更加后悔。树又都不认识,有些长得粗大,但没有欧洲的树高,只是分枝粗壮有力,铺展得十分宽广。有些树木盘根错节,在半空中缠在一起,人们只能在树根中溜过去。藤本荆棘很多,带芒刺和尖钩;丛林也很奇特,树干枯萎,树叶脱落,因为时令已是隆冬了。丛林虽密,尚可通行,意想不到的小路纵横其间,都是野兽奔跑留下的足迹。到底是什么野兽呢?大家查看足迹,还弯下腰来查看粪便。粪便是白的,像高岭土的颜色,那是豺狗留下的。这边是鬣狗的,那儿是羚羊的,另外还有一些是疣猪的……我们像猎人一样匍匐前进,神经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我走前面开路,好像小的时候在家乡罗克树林探险的样子:同伴们紧紧跟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只拿着一支上了膛的猎枪冒险是很不妥当的。有些时候,像动物园里的臭味非常强烈。阿杜姆是内行,叫我们看沙地上狮子留下的足迹,还是新近留下的哩。我们看到猛兽睡过的地方,看见它们的尾巴在地上扫成的半圆圈。在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些足印,那肯定是一头豹子留下的。到了一根枯树下,我们发现一个大坑,通到一个很大的野兽洞口。如果阿杜姆滑下去可以掩没到胸口。他一直小心翼翼,当然没有滑下去,因为他早就告诉我们,这儿是豹子出没之地。我们的确满鼻子都充满了猛兽的气味。到处都看得到被豹子吞食了的各种鸟类的羽毛。我心里吃惊,豹子也竟挖洞栖息,可是,阿杜姆突然惊叫起来:不是,不是豹子,那头野兽他也不知道名字。他非常兴奋,在地上寻找,最后找到了,得意洋洋地指给我们看一头浑身带刺的大豪猪。不过,这不是一头吃掉家禽的豪猪……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我惊起了一头大母鹿,毛皮是黄褐色,有白点花。珠鸡很多,我开枪,不料一个也未打中,真丢人!我很想弄清是些什么鸟,追了好久,在树下穿来穿去。鸟的体形,像山鹑那么肥胖,但丛林枝叶太密,使我没法开枪。一只大灰猴冒冒失失地跑来在树枝上荡来荡去,停在我们头上几米高的地方,吓昏了。我们听见它在很高的树枝上晃动,也看得见它。只见它猛然一跳,逃跑了,一瞬间便到了很远的地方,还回过头来望着我们。一张小小的灰脸上,露出了两只发亮的眼睛。有时候,树林开朗了,出现了林中空地,春天就要使这充满生机。啊!我真想在这儿停下来,坐下来,坐在高大的蚁巢边,隐在巨大的槐树下,偷看猴儿嬉戏,长久地欣赏美景。但是,等候猎物来到,想打一点野味,使我观赏的兴致减低不少,要我静坐不动,过一会儿,自然的景色就看不见了。一切都像我不在的时候一样,我忘掉了我的存在,只留下一点幻觉。我心情舒畅,真难形容,真想将来旧地重游。当我在不知其名的树枝中擦身而过的时候,天色已晚,催我回船,别人尚有机会再来,我无疑是最后一次了。
刘煜 徐小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