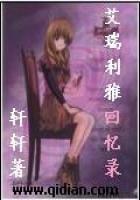写什么呢?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人,一人非常关心我的人,一个在我们那里有非常好的口碑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文兴鲜叔叔。就写他。写他的一生,写我认为是一个革命者的一生一世吧。他就是我小说的主人公。当然,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给他改了名,换了姓!
于是,我就行动起来,就闭门造起车来。就构思出一部人生三部曲:第一部《花红》,写他的少年时代;第二部《柳绿》,写他的青年时代;第三部《松长青》,写他的老年时代。当时,我竟然对自己的这个构思很满意,很自信。暗自下决心三五年写出来。我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不是书呆子!我要用我的成功来证明我个人的价值!那时,我真是心比天高啊!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构思、写作。不几天,我就写出了提纲,拟定了人物表。开始了第一部《花红》的写作。两个月下来,竟写出了近五万字。
我躲在屋里写,不想让人知道我写小说。可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人知道了。有人凭空臆想,夸大事实,说我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说我写起了三四十万字,说我已投给了出版社,说我已收到了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通知。社会上的传言和议论风起云涌,褒贬不一,说好说坏的都有。但真正支持我写作的也的确有人,父亲自不必说,他最支持。他也知道我在写书,他希望他的儿子写出书来。父亲以外,最坚决支持我写作的就是文兴鲜叔叔。他只知道我喜欢写作,热爱写作,知道我在上初中,读高中就公开发表过作品。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支持我写作。所以,他才给我寄了那么多书。但他却不知道我想写他,我在写他。
这时的文兴鲜叔叔还在东北某部队任职。是一名模范军人。当时,《解放军报》公开发表过写他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他非常关心家乡的生产,非常关心他家乡的乡亲们。他曾在1959年给他家乡所在的生产大队一次捐赠了两千元人民币,五十年前的两千元比现在两万元还管用啊!或许可以抵现在的二十万元哪!他每次回来,都要给贫穷的乡亲们送钱。我读高中时,他陆陆续续给我寄了一百多本书。他还要在经济上资助我,我委婉谢绝了。他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个人。因此,我才想到要写他。他是一个值得歌颂的人。他成为我长篇小说主人公的主要原型。
但是,我的身份是农民,农民必须种田,种田是我的主业,写作只能是副业,只能业余进行。
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才真正学干农活。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头学起。一个农民,就是要会干农活,成为种田的内行、把式。我成农民了,必须学会农活。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老老实实的去学、去干。我没有退路。
学农活,我不怕受累,也不怕吃亏,更不怕使劲用力。力气是奴才,用哒它又来。但我就怕那种冷嘲热讽,阴阳怪气的人。就恨那种同工不同酬,评工分不公正的人。我一个男子汉,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一天劳累下来,干了同样的活,使了同样的力,工分却只能评人家的一半,而且是女社员的一半。我心里就是不服气。有一次锄苞谷草,我们一共五个人,就我一个男人。那是一块平田,她们每个人锄四行,也就是一垄。一人锄一垄,各锄各的,谁也帮不上谁的忙,放工时评工分,四个妇女评十分,我只挂靠五分。我当时就质问她们:“为什么只给我评五分?”他们却振振有词:“因为你是学手子,才参加锄草,评你一半工分就不错了哟!”我不服气,拒理力争:“我又不比你们锄得少些,怎么同工就不同酬呢?”她们却嘻嘻大笑。说:“你没看人家当学徒,学两三年,一分一文都不给呢!你还争什么争?”我这才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哪!还有一次学耕田,那是一条黄牯牛,它认生,我老套不上它。有个中年社员就冷笑一声,带着鄙夷的声调说:“真没用,牛都套不上,学耕什么田哟?”我听了心里好气呀,真恨不得回敬他一句:我读的书你读得懂吗?我写的字你写得好吗?我会写文章,你写得出来吗?但我忍住没说,说了有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会学会的!”这时候,我父亲走了过来,对我说:“奎生,不要着急,我来教你!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无师自通的!那么多大本大本的书你都读懂了,那么长长的文章你也写出来了,还怕套不上一头牛呀,还怕学不会耕田哪!”
我说:“没人教过我,我怎么会呢?只要有人教,我就一定学得会!我不相信我的脑子就这么笨!”
父亲说:“就是啰!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我感谢我父亲,他总是那么懂得儿子的心,他一五一十地讲了套牛的办法,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套牛耕田的技术。我也很快就学会了。以后,不管是旱田,还是水田,无论是陡坡田,还是岩旮旯田,我都会耕了。而且成了队里公认的耕田行家里手。而且,父亲还教会了我各种农活的技能。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无论什么农活,力气活也好,技术活也好,我都拿得起、放得下、干得好。
农村很苦,干农活很累,我的写作就渐渐地放慢了,有时候好多天不动笔。这时候,有人约我出去打花牌。我经不住劝说,经不住诱惑,我也不好拂了人家的面子,几次相邀之后,就去了。
打花牌我一学就会。
一学会就放不下了。
一遇到下雨天,我就出门同别人打花牌。
学会打花牌之后,我的写作就基本上停止了。
每次出去打牌,或者打牌回来,父亲只盯我一眼,不说长,也不说短。但我看得出,父亲对我很不满,很失望,也很着急。有时候,我也想洗手不干,改邪归正。但我经不住人家邀约,就又出去打牌了。
有一天,也是下雨天,我在外面打了一整天的花牌,很晚才回来。
我悄悄地推开门,不声不响地走进自己的房屋中。我推开门一看,就愣住了。我的条桌上点着煤油灯。父亲在条桌前椅子上坐着。我站在门外不敢进房屋里去。
父亲低声问我:“回来啦?”
我毕恭毕敬,说:“嗯,回,回来了。”
父亲还是那么轻言细语:“奎生,你也来坐吧,我们两爷子在一起坐坐,说说话吧。”
我挨到父亲身边坐下了。
父亲说:“奎生呀,这一向时,爹很忙,没有顾上你,没关心你,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啊!县里、区里、公社里给你安排了几次工作,都被大队卡住了,不仅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呀!可有什么办法呢?大队不放你走,我们也没办法呀!我知道,你去打花牌,就是为排遣心中的痛苦!但你总不能老是陷入这种痛苦之中呀!你应该面对现实呀!你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自己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去努力奋斗,去努力争取,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我知道你喜欢写作,你心里一直放不下写作,想当作家。这都没有错,我支持你!你看,我今天专门到街上给你买了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一摞白纸。你还是拿起笔来吧!写你的文章吧!我知道你写作要熬更守夜,我还给你打回来了一壶煤油呢!你知道,这煤油是紧俏货,我在街上找了好几家铺子,好说歹说,才打到这一壶煤油啊!”
看到这一支钢笔,这一瓶墨水,这一摞白纸,这一壶煤油,一下子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顿时,我的眼泪倾泻而下,我一下跪在父亲的面前,失声痛哭,万分悔恨地对父亲说:“爹,我错了!”
父亲扶起我,说:“知道错就行了,何况这不全是你的错!奎生,我相信你!”
我从衣袋里掏出花牌,走到火坑屋里,把花牌扔进火坑里。不多一会,花牌就燃烧起来,腾起一串火苗,飘起一缕青烟,留下一堆灰烬。从此,我就告别花牌,同它一刀两断,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劳动和业余写作之中。
1965年,是我人生道路上角色的又一次转换。对我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的。
正月初五,又是正月初五,又是刘队长来到我们家。刘队长本是一个不喜欢串门的人。他也很少来我们家。今天来到我们家,必定有事,而且是大事。果然不错,他指名道姓找到我,说有一个重要的事跟我讲,想同我谈谈。谈谈就谈谈呗。刘队长同我的谈话就在我家火坑旁展开了——
“小曾呀,你回乡已经三年了。三年来,表现很好呀。”
“这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也是您帮助和教育的结果。”
“你的表现,区、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都很满意呀。都夸奖你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模范啊。”
“我做得还不够好,今后争取做好一些。”
“我们都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请您相信,也请您转告区、公社、大队的领导,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希望。”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呀!”
“什么工作呀?”
“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让我通知你,要你当教师创办一所耕读小学。这也是区和公社党委的意见。”
“当教师?让我当教师?”
“是呀。”
“真的呀?”
“你不相信呀?”
“不是我不相信,是我不想教书。”
“你不想教书?”
“不想!”
“教书也是革命工作呀。”
“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呀。”
“你一个知识青年,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现在的需要就是你去教书。大队党支部慎重研究决定的呀。”
“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应该先征得我的同意呀。”
“是你服从党支部,还是党支部服从你呀?”
“反正我不会去教书。”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就种一辈子田,当一辈子农民!”
“一个高中生,就种一辈子田,当一辈子农民?”
“不可以吗?”
“你还是认真想一想吧,想好了,再回我的话。”
“不用再想,我坚决不当教师。”
我们的对话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第二天,大队党支部派了一个支部委员继续来做我的工作。我拒不开门,谢绝见面。那个委员无功而返,愤极而归。
第三天晚上,大队党支部邓书记亲自出马了。
邓书记来到我们家,父亲开门把邓书记迎进了屋里。
我依然睡在床上,无动于衷。为拒绝当教师,我已经关门睡了三天,不吃也不喝,不言也不语。邓书记叫我,我不答应,也不理睬他。他径直走进我房里,我面壁而卧,用后背、用屁股对着他,闭着眼晴,沉默不语。
邓书记也一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父亲见了,生气地对我说:“奎生哪,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邓书记呀?邓书记亲自来做你的工作,你怎么就不理睬邓书记呀?”
邓书记跟着说:“我是代表党支部来做你的工作的,党的话你也不听呀?”
父亲说:“是党培养了你呀,你怎么就不听党的话呢?”
邓书记严肃地说:“是党把你从小学培养到高中,你总不能让党白培养你十二年吧!”
父亲也严厉地说:“我们是贫农,是党救我们出苦海,我们才翻身得解放。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可不能忘记了党的恩情啊!我们不应该忘本哪!”
邓书记接着说:“你是党培养出来的一个知识青年,应该听党的话呀。当自己的喜好与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时,我们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呀。当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呀。”
父亲双眼紧紧地盯住我不放,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父亲对我的殷切期盼。那期盼的眼神中蕴藏着千言万语!
邓书记临走时,语重心长地说:“小曾呀,你可不要辜负党组织的希望啊!也不要辜负了你父亲对你的期盼啊!我们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最终,我走上了教育战线,当上了人民教师。
十天后,曾家畈耕读小学诞生了。
十个月后,曾家畈耕读小学成了全县的模范耕读学校。
又过了十天,我从地区教育局捧回了优秀耕读小学教师的奖状。
我当上教师后,继续兼任着生产队出纳、保管员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业余时间我还继续坚持创作,地区的报刊上经常可见到我的作品。但长篇小说的创作速度渐渐缓慢下来,两年的时间只写了上十万字,按构思,《花红》还不到一半。这时,已是1966年初。
不久,地覆天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文化艺术被围剿,在劫难逃;文化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写小说的没有哪个逃脱厄运。我万幸没有把小说写出来,更庆幸我没有张扬自己写小说的事。风声一紧,风暴来到之前,我就把我写的小说稿,包括提纲、人物表及记录素材的笔记本,全部放在火坑里烧毁了。望着那串串火苗,缕缕青烟,我不禁潸然泪下,那是我的心血结晶呀!陪同小说稿火葬的还有我的六大本日记、一百多本书籍、一百多封书信。那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呀!我写作长篇小说的梦完完全全惊醒了,彻彻底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