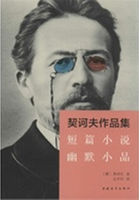不约而同,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了春燕、召弟。
我见了怎么也吃不下碗里的那块肉。
春燕看见父亲、母亲和我都没吃肉,天真地问道:“爹,妈,哥哥,你们怎么不吃呀?你们也吃吧!”
父亲、母亲对妹妹说:“春燕、召弟,你们吃吧。吃了肉,长身体,你们快些长大吧!”
春燕、召弟点头说:“好。我们吃,吃了肉快些长大。长大了,好帮爹妈做事。”
父亲母亲笑了笑,说“你们真是乖孩子呀!”又对我说:“奎生哪,你也赶紧吃了吧!吃了这顿肉好回学校去。在学校里一学期也吃不上几顿肉!”边说,母亲又往碗里夹了一块肉。
我把肉夹起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喉咙里就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吞不下去。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父亲母亲一块肉都没吃呀,全让给孩子们吃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想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父亲、母亲都没察觉。又给春燕、召弟一人夹了一块肉放进她们的饭碗里。
正当父亲又往我碗里夹肉时,忽听到门外“砰”地响了一声,那声音像是重物落地时的那种沉闷声。
母亲说:“好像是来了人哪!”
我说:“这种天道,又是黑灯瞎火的,怎么还会有人来呢?”
父亲说:“你们就待在屋里,不要动,我先出去看看。”
父亲点燃一根松树蔸油亮子。举着油亮子出了火坑屋,进堂屋开大门。不想父亲刚拉开门闩,大门就一下子开了。随着大门的吱吱声,一个人随着大门打开倒进了堂屋里。父亲大叫一声:“谁?”
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冲到堂屋里,只见堂屋地下躺着一个陌生人。那个人满身冰雪,赤着脚穿一双棕草鞋,脸煞白,眼睛紧闭着,喘着粗气。父亲连忙把那人抱了起来,抱进火坑屋,放在椅子上,吩咐道:“奎生,快倒一杯热水来。”
我急忙端来了一杯热水,递给父亲。父亲一只手抱着那个人的身子,一只手往那人嘴里喂热水。热水慢慢地喂进那人口里,那人咕咚咕咚地吞咽着。那人喝下水后,呼吸慢慢地平稳了,脸上也渐渐地转红了,身上的冰雪也已融化蒸发。过了一会儿,那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往屋里四周看了一看。然后望着我父亲,问道:“我这是在哪里呀?”
父亲说:“这是我家,你看,我们一大家人都在这里烤火。”
那人又问:“我怎么到你家里来了呢?”
父亲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我们在火坑屋里烤着火,吃着饭,忽然听到门外有响动,我就出来开门看,门一打开,你一下子就倒进我屋里啦!”
那人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到你家里来了呢?我为什么会到你家里来呀?”
父亲说:“你先不管是怎么来的,也不要去想了。你是冻着了,你就坐着烤火,烤暖和了,再去想是怎么来的。好吗?”
那人点了点头说:“好,好吧。”
那人身子还打着哆嗦。母亲往火坑里又加了两大块栗树柴,拿来吹火筒使劲吹了几下,火苗蹿起,火焰熊熊,屋里的温度逐渐升高起来。
那人烤了一会儿火,逐渐清醒过来,对我们说:“我想起来了,我是到湖北清江坪走了亲戚。今天转身回湖南,走了一整天,冻了一整天,也饿了一整天。又赶了一个时辰的夜路才走到你们这里。我指望喊你们开门,找你们讨个歇。我喊了几次都没喊出声,眼一花,腿一软,我就靠在你们的大门上了。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们一开门,我就顺着门倒进了你们屋里。是你们救了我呀!”说完,那人就想站起来,但几次都没站稳,只好又坐回椅子上。
父亲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那人说:“你们救了我,我要给你们磕头呀!”
父亲说:“嗨,磕什么头呀!你坐着烤你的火,身子烤热乎些了吃饭,吃了饭再说。”
那人就伸手烤火,看见了火坑里煨的汤罐,闻到了那罐里的香气,嘴巴就不自觉地“巴哒”了几下,鼻子歙动了几下,嘴角也抽动了几下,就低着头,眼睛望着火坑里的汤罐,不言也不语。
那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父亲和母亲看在了眼里,知道那人想吃东西,又不愿意麻烦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从而断定那个人是心地善良,老实本分的人。父亲朝母亲投去了征询的眼神,母亲心领神会,知道了父亲的意思,点了点头。父亲就去拿了一个大碗,盛了一大碗饭,用筷子夹了两大片肉,说:“我们才吃完饭,饭菜还是热的,你就趁热吃了吧。”
那人很客气,一再推辞。他说:“我不饿,我不吃。你们这地方我晓得,每人每月只十几斤粮食,每天每顿都是定量下伙的,你们自己都吃不饱,我一个外地人,怎么忍心在你们嘴巴里抢食呀!”
父亲说:“不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匀一口,你就可以吃一餐了。”
母亲也说:“我们今天打牙祭,下伙时,我就多加了一点苞谷面。饭有多的。你就不要客气了。吃吧!再不吃,看到你饿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难受呀!”
春燕、召弟也很懂事地说:“叔叔,你吃吧!你吃,今天的饭里苞谷面掺得多,饭特别的香呀,还有肉呢,才叫好吃呀!叔叔你快吃吧!”
那人看看父亲,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们,笑了笑,点了点头,才拿起筷子吃起来。
那人真是饿极了,端起碗就狼吞虎咽起来。满满一大碗,他连汤带水都吞下了肚子。碗里的一点残汤剩饭,他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父亲见他还没吃饱的样子,就去把锅里剩下的半碗饭盛到那人的饭碗里,又把汤罐里的肉和汤都倒进那人的饭碗里,端来给那人。那人迟疑了一下就又接过碗。不一会儿,他又吃了个精光。
“吃饱了吗?”父亲问那人。
那人不住地点头,说:“吃饱了!吃饱了!多谢你们,吃饱了呐。谢谢你们救了我一命呀!”
“嗨!你这就见外了,切莫说这种感恩戴德的话了。我们也是得到过别人帮助的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呀!”
那人说:“不是讲回报,人得讲良心。你们帮助了我,我这一辈子都是忘记不了的呀!”
父亲说:“好了,好了,不讲这些了。你只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呀?”
“唉!一言难尽呀!”那人叹息一声,对我们讲述了他这次从湖南到湖北走亲戚的经历——
“我是湖南天顶山人。不多年前,我有一个亲叔叔到湖北清江坪一户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前几天,我们突然接到了他病危的信。我的爷爷、婆婆早已过世,我的父母也年事已高。父母就打发我去看一下叔叔。三天前,我赶到了清江坪,哪晓得叔叔已过世几天了,早就安葬下土了。正值壮年的叔叔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我问了婶娘。婶娘告诉我,他们那个地方,连续两年大旱,几乎颗粒无收,人都外逃了一半。没外逃的靠吃政府救济,可那一点救济粮,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只好挖野菜、剥树皮艰难度日。还有的人吃观音土,喝了水,观音土在肚子里发胀,就被活活的胀死了。叔叔就是吃了观音土,屙不出来,胀死了的。叔叔死时,家里已断炊三天了。我到了那里,婶娘到山上挖了野菜,煮了让我吃,叫我吃了马上回湖南。我已没别的办法,叔叔不在了,我留下来也没意义了。我就打算住一晚上再走。没想到婶娘趁我不注意时,她悄悄地跳进了清江。婶娘的尸体都没找到。这个地方我已举目无亲,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只好打回转,没想到我就倒在你们门前了。”
“唉!”母亲叹息一声,说:“那地方比我们这里还苦呀!”
父亲说:“天灾无情呀!都是天灾惹的祸呀!”
那人也说:“我听我爷爷说,他活了七十岁,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灾害呀!连续三年哪!”
父亲说:“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呀!”
母亲慌忙制止父亲:“你瞎说些什么?你不知道祸从口出呀!”
父亲说:“我说的是事实嘛!”
那人接过父亲的话头,说:“你不必说了,你的话,我心知肚明,上面也迟早会知道的。总有改变的那一天哪!”
父亲说:“我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才说真话的。”
母亲说:“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要再说了。请问这位大哥,贵姓哪?贵庚多少呀?”
那人说:“咳!我这个人哪,人家的饭吃了,我还没告知姓名!我叫曾明生,今年过第三个本命年,家住湖南天顶山。”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叫曾明生?我叫曾明俊,真是兄弟对面坐,不知姓和名哪!我还比你多吃两个年豆腐呀!”
那人听了,一把抓住我父亲的手,说:“哎唷,我们真是兄弟呀,一笔难写两个曾,连排行都一样,你年长我两岁,是我哥哥呀!”
父亲一笑,说:“做哥哥实在不敢当哟!”
曾明生说:“哥哥就是哥哥!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啦!”
母亲说:“多个兄弟多份亲情,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那人说:“我从哥哥门前路过好几回,听到人们说起过,你们这里近两年年景也不好,缺粮食吃,你要不嫌弃,你就把我当亲兄弟,什么时候到我那里去,背几百斤苞谷来。”
父亲问:“你还有余粮呀?”
曾明生说:“实话对你说,我们那是山高皇帝远,田多人户少,我们就满山五岭的种。广种薄收,多种多收,一年收好几千斤苞谷。又没哪个去我们那儿搞统购统销,没有人去收购我们的粮食,收了粮食也运不出去。我们天顶山的人下山只有一条独路,要先到湖北,然后才能到湖南。我们没缺过粮食。你家需要多少粮食,我可以给多少。你们家缺的口粮我全包了。我们有吃的绝不让你们饿肚子!”
父亲说:“粮食我们确实需要,但我们必须按数给钱。”
曾明生说:“那行。你要付钱你说了算,但我收多少钱该我说了算。”
“反正不能让你吃亏。”
“我们可是亲兄弟呀!兄弟之间还讲什么吃亏不吃亏呀!”
父亲诚恳地说:“明生弟,老天有眼哪!让我认识了一个好弟弟呀!”
曾明生高兴地说:“是我找到了一位好哥哥呀!”
母亲笑嘻嘻地说:“奎生、春燕、召弟,你们都来喊叔叔!”
“叔叔!叔叔!叔叔!”我们接二连三地都喊了叔叔。
“哎!哎!哎!”叔叔喜笑颜开,不住口地夸我们:“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
从此以后,我们两家来往密切,不是亲戚,胜过亲戚,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
第二天,天还没亮,曾叔叔就大声喊道:“大哥大嫂,我走了,多谢啦!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去玩哪!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谢谢你们啦!吵闹你们哪!”
父亲问:“你怎么这么早就走呀?”
曾叔叔说:“路上不好走,不早点动身,一天走不到家呀。屋里人还在挂念着我呀!”
父亲说:“那你就慢些走噢!”
“好哩!”曾叔叔答应一声就出门上路走了。
曾叔叔一走,父亲就起来了,也赶早到水运队去了。
我在床上睡不着,想尽快回学校去,也就早早起床了。我到屋外看天道,天上还在飘着雪花,路上厚厚的牛皮凌原封未动。我上学要经过千丈岩、云峰山,我一个人也不敢去。我就在屋外山墙边拿了几块柴,把火坑里的火架燃了。
母亲和妹妹们也先后起床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天寒地冻,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们只有围在火坑边烤火。我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看书,复习功课,写着作业。只等天道一晴,我就动身回学校。我知道父亲很忙。我不想让他送我回学校去。我不想分散他的精力。
那时,在我们这个地方,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都没有,广播没听到过,电影一年也不一定能看上一场。大多数人没进过学堂门,也就没有人读书看报。像我这样的高中生在我们这种地方可算得上是稀有动物。我们家除了我的读书声,就只有妹妹们的笑声和哭声,再也没有其他什么响动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么过过去,时光就这么流逝去。
今天的日子也就这么从早走到晚。
很晚,父亲才回来。
父亲一进屋,母亲就问:“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快一更天了呀!我们等你回来吃晚饭的,左等你不回来,右等也不见你的影儿。等不到你回来,我们才吃了饭。春燕、召弟她们瞌睡来了,吃了饭就去睡了。只剩奎生和我还在等你呀!”
父亲说:“我们今天开了一整天的会,白天没开完,晚上又接着开,一散会,我就回来了。”
母亲问:“你们今天没扎排呀?你们不是说任务很急的吗?怎么还停起工了开会呀?”
父亲说:“这比放排的任务更急呀!”
母亲问:“还有什么更急的事呀?”
父亲回答:“上面来了文件,传达了精神,全国都在精兵简政,我们林业部门也要精简人哪!”
“你们水运队都是工人,都是做工的,做工的也要精简呀?”
“除了农民以外,都是精兵简政的对象,都有可能被精简!”
“水运队五六十号人,精简多少?精简些什么人?精简哪些人?这事我看蛮难的呀!”
“是很难哪!”
“就是嘛!在水运队当工人,拿工资,精简掉了,就要回家种田打土垡,哪个愿意被精简呀?”
父亲说:“我就愿意呀!”
母亲一愣,问:“你愿意?”
父亲说:“我是愿意呀!”
母亲不悦,说:“你疯啦?不当工人当农民!”
“你不知道,现在国家遭遇了很大困难,国家有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忧呀!有国才有家呀!”
母亲说:“国家大事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但你的行动要多想想、多考虑再决定,主意你自己拿吧!”
父亲说:“我已经作了认真考虑。”
母亲关切地问:“水运队精简的人已定了吗?”
“还没有。”父亲回答道:“现在是动员、申请,然后组织批。”
“你写了申请吗?”母亲急切地问。
“写了!”父亲说:“我是第一个交的申请。”
母亲有点不高兴,说:“你就这么积极呀?”
父亲说:“我不带头没人写呀!”
“哎哟,你要带这个头呀?你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
“可我是一名工人呀!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上岸的呀!我不能忘这个本哪!再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三四个伢子,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我回来了,两人一条心,我们就能战胜困难,过上好日子呀!”
母亲听父亲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说:“你主意拿定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好了。你说回家就回家吧!”
“那你欢迎不欢迎我回家呢?”父亲松了一口气。
母亲笑了笑,说:“你是一家之主呀,我们不欢迎也不行哪!”
父亲终于开怀笑了。
可林业局和林业站领导不放父亲走。汪局长、杨站长一起找父亲谈话,要求父亲留下来。还说:“水运队需要你!”
父亲很诚恳地对汪局长、杨站长说:“国家有困难,需要精简人。我家有困难,需要我回去。让我走,对国对家都有利。我已下了决心,回到农村去。请领导批准我的申请,让我回去吧!”就这样,父亲离别了他工作十多年的水运队,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家,由工人变成了农民。
从此,他把全部身心都用在了他的子女们身上。
从此,他把汗水都洒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他支撑了一个家庭,也为国家承担了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