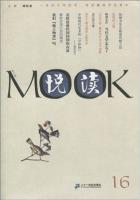人家告诉我,他的全名叫徐君虎,是蒋经国先生的主任秘书。
从此以后,徐君虎先生几乎每天都少不了要和我见上一面,问长问短的,十分关心。估计对万水生也一样。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谁能料到,事隔半个世纪,当我的朋友、着名诗评家李元洛先生,从《华夏诗报》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得悉我与徐君虎先生还有过这么一段缘份时,惠然赐书,告以老先生身体硬朗的喜讯,并且写道:“徐老先生现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之一,与我父辈素有通家之好,交往极为密切,是我尊敬的长辈。”承蒙他的好意,已将我的情况和通讯地址转告了徐老先生,希望我能主动去信直接联系。
由此,中断了多年的感情纽带又得以恢复和加固。
说来也是天意,1990年和1991年,我曾两度获有赴湘拜望他老人家的良机。回首话旧,往事前尘,恍若一梦!我对徐老,一贯以“虎叔”相称,他亦泰然受之。徐老先生乡音不改,听来铿锵仿佛当年。也不知是这一声“虎叔”,逗起了耄耋旧情,还是彼此间虽有二十岁的齿序差距,却同样经历过一段“右派”生涯,因而牵动了怜惜之感,不待我提起话头,他倒主动问起:“可还记得我上你家小坐的事么?”我闻之怦然泫然,“忘不了。”他只顾独自说下去,两眼直直地望着粉墙,犹如那粉墙便是逝去了的日月。“就在同一天,我还去了万水生家。我当时判断,你的家境要比他家略强一点,我便决定认万水生做义子。其实所谓的认,无非是多公开承担一点责任,拉扯他一把;让我同时认两个,我自忖力量不足,结果会是谁也帮不上的。”
既然他老人家无所顾忌,主动捅破了这一层于我多少还有点难以启齿的“纸”,我也就趁机探问:“1955年‘肃反’,我在总政文化部,有人硬说我与你,与蒋经国先生,有‘不可告人的黑关系’,整得很苦;我又不知道你是否去了台湾,只能尽我所了解的,一直交代到你出任湖南邵阳县县长为止,请他们去调查。没有过多久,他们再也不提你的名字了,集中火力追逼‘蒋经国是怎样亲自培养你当特务的’这么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徐老先生说:“他们能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呢?”他说,他对外调人员当面谈了,还写了材料,说得明明白白,“我徐君虎从未认刘仁勇--我少年时代的学名--为义子;义子倒有一个,那是万水生,不是刘仁勇。”
原来如此!可我的肃反审查结论上,还是记了一笔:“公刘……曾是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的干儿子。”
这是为什么?不是一直信誓旦旦,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么?
我始终为自己的天真所误。我根本不理解人家的真正用心所在:蒋经国!有了这么个结论,我就永远得和蒋经国先生纠结在一起,我就永远陷落在无法解脱的羁绊当中;他们感兴趣了,提起来千钧,他们需要体现“政策”了,放下去四两!
1956年春,原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让我看了关于我的这个肃反审查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创作室党支部的名义作出的。我除了指出,有几处措辞含混不清,似乎对我的出身和经历,都有某种“保留”和不信任外,主要强调了所谓干儿子一节,绝非事实。我向陈沂部长提出予以删除的正式要求。不数日,陈沂部长再次找我(这次是在他的绒线胡同家中),传达了党支部书记虞棘先生的断然拒绝:不能考虑。据说,这样写,是有根据的,而且根据就是公刘本人提供的,云云。我再追问,我在哪里提供的?告以是你在昆明部队写的入党自传。我一听之下,不由得一方面怒火中烧,一方面如坠冰窖。我在1954年交的入党自传是怎么写的,幸亏我还记得清楚。尽管这份自传,早已入档,我无法翻出来字字照抄。但,当我叙述少年时的社会一政治经历时,是本着对党交心的绝对坦白态度,充满了自我批判精神,连自己的“潜意识”都彻底解剖了的。记得,我用文字表述过如下的思想内容:
抗敌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们,觉察到徐君虎对我们(指万水生和我两人)异常亲热、关心,便起哄逗他:“徐秘书,你干脆认他们做干儿子罢。”徐笑而不答。我回家后,却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的反应是高兴的,认为:“真要认了干儿子,倒是你的造化。”父母亲的倾向是明显的,加上旧社会的攀富结贵的恶劣习气,于无形中熏染了我,使得幼小的我,心里也就萌生了希望它能成为事实的私愿……
这就是他们所依仗的、所谓公刘本人提供的全部根据!
今天细想,其实,我的上述表白,本来就是过火的:第一,我没有任何争当徐君虎先生干儿子的明确表示;第二,我对别人的起哄,并无喜形于色的反应。这个无反应,或许该归功于世俗的另一面,它形成一种强大的阻力。因为,在南昌人日常的人际关系准则中,说谁是谁的“干崽”(即“干儿子”)是骂人话,是有损人格的。这就造成了我的心理障碍,虽说完全是善意的玩笑,也觉得不好随便接受。何况,日后我进大学学的是法,自然更明白,凡是虚拟的东西,推论的东西,分析的东西,是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作客观事实看待的。因之,那时的我,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觉悟”,早已逸出了实事求是的范围了。
还有一个令人后怕的问题。万一,徐君虎先生去了台湾呢?怎么办?我这样“深刻地”挖掘自己的“肮脏灵魂”,岂不是自掘坟墓?那些掌握着我的生死簿的有权势者,他们是否也会稍稍设身处地的替我想一想:公刘是不是在言过其实地瞎写?难道就不考虑考虑后果?我事后设想,倘或他们动过这样的善念,那么势必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裁决:一种是公刘太幼稚,不识厉害,放他一马;另一种是公刘太愚蠢,吃点苦头,活该。
看来,他们的裁决是后者;甚且不完全是后者,因为主事人还怀有强烈的“立功”动机。
我必须为我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的愚蠢也不仅仅是愚蠢,应该承认,其中的确包含了某种不健康的投机心理。究其实质,还是“左”比右好,自以为批判得愈严酷,就认识得愈痛切。殊不知政治性的愚蠢,其结果肯定会招致政治性的惩罚。
而这一切,不过仅仅是开始。
1957年,我在不曾“鸣放”,也从未写过大字报的情况下,被从甘肃敦煌莫高窟电召回京,并且不由分说地扣上“右派”帽子,斗得死去活来;毫无疑问,这和创作室领导人1955年肃反“肃”了我一年整,却没能把我“肃”成反革命,实在心气难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据我所知,不少“右派”,就是既无“言论”,又无“行动”,单单凭所谓“历史复杂”或者所谓“海外关系”之类捕风捉影,可大可小的罪名入网的。
在那帮“左王”的心目中,我大概就属于“历史复杂”者;也许,“海外关系”四个字同样能派上用场,试问,还有比蒋经国更大更可怕的海外关系么?尽管,再过它三十年,真有这层“关系”的话,又完全有资格进入大会堂吃国宴了。
何况,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究还是找到了一项“铁证”--1956年,我在一次“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赔情道歉”的支部扩大会上的发言纪录;于是,公刘“猖狂进攻”的罪案得以确立。
我的那次发言,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文字狱。我说,我从前读史,总闹不清什么叫文字狱,什么叫“瓜蔓抄”,因为缺乏感性知识。经过“反胡风斗争”,明白了。二,人道主义。我希望,从今而后,从上到下,都应该多一点人道主义。万万不能定了罪,再找罪证,先开枪,然后才了解是不是敌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流弹乱飞”,“伤了自家人”。
印证晚近陆续披露的“反右”内幕,我想,其实就凭这两条,把我划为“右派”,已是绰绰有余了。我当时并不想发言,无奈那位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地动员,一直把工作做到了我的宿舍;临到会议结束的下午,又点我的名,并且使用了“激将”法。也是我“反动本性难移”吧,我到底憋不住还是讲了(日后的斗争会上,虞棘先生正是这么批判的:你以为党真的向你赔情道歉啊?不过是试一试你还翘不翘尾巴罢了!怎么样?到底是反动本性难移!自取灭亡!别人是爱莫能助的!)。那么,不进他们设的圈套,能否太平无事呢?也不可能!徐君虎先生的榜样就明摆在那里。他身为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政协重要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与不少当朝大人物同过学,回国后还坐过国民党的牢,解放前夕又武装起义有功,……如此等等,还不是照旧额头上打金印!什么道理?说穿了,岂不就是因为同蒋经国有那么一段关系么?当然,就他而论,还有一个为官清正,深得民心,教某些人感到很不舒服的特殊问题。
总之,一切都不言自明。
前面说过,我不是徐君虎先生的干儿子,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有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更可怕的是不胫而走的流言,传遍了文艺界,传遍了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传遍了昆明部队,传遍了全国各地!人们瞄着我的脊梁骨指指戳戳,叽叽喳喳;我纵然长出一千张嘴来,也无从辩白。这一回,我的确是体会到“三人成市虎”的滋味了。事情还在于,偏有那么些个好事之徒,偏爱添佐料,调酱醋,凡是涉及我的什么,必定要扯上蒋太子……否则就不过瘾。
等我已然成为“右派”,发配山西劳动之际,这个谣言,又大大地发挥了一次威力。
1958年冬,大地封冻的日子,我们这些修建太谷郭堡水库的军内“右派”们,在水库完工,交付验收的同时,集中到了太谷县城,奉命进行“思想总结”。据说,这将有利于“加速改造,重新做人”云云。
又祭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法宝。
和去年不同的是,现今是利用“右派”整“右派”,而不再是组织“左派”整“右派”。这一着棋,他们算下对了,因为的确有不少“右派”想当左派--说来十分可怜,不过只是图个“摘帽子”罢了。
我所属的那个班,有一个“右派分子”,名叫洋泉,北京大学毕业生;细高挑身材,喜欢读书,也爱下个小馆喝上几盅,就是脾气倔,好跟人干架,平日里极少露笑容,一副硬派小生模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居然私下将自己写的两首旧体诗,拿出来给他认为可靠的朋友读了。不料,他这位朋友很不仗义,关键时刻,翻脸不认人了。这两首诗便出现在大字报上,成了供批判的靶子。于是,一时乌云滚滚,风雨大作;还真有一些人下得了手,立刻展开又一次的“伟大的反右派斗争”,依“左派”同志们之法炮制,一致判决这两首诗是所谓的“毒草”,而且是“直接和台湾蒋匪帮遥相呼应”,“盼望变天”的罪证。个别人走得更远,竟然从中嗅出了洋泉“企图叛逃”的“阴谋”,真是可耻也夫,可悲也夫!我正在暗暗感叹,忽然又该着我倒霉了。就在这样一种低气压中,一个用白话“翻译”和“解析”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班长陈振华传达了大队部的指示,这自然是无法拒绝的。虽然,大队部也者,不过是“右派”们的一种编制称谓,三位正副大队长陈挺、周宏达、华涤,本人也都是“右派”,其政治身份,与连长、排长、班长以及普通“战士”并无区别。我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气力,啃着这两颗“铁核桃”。临了,我还不得不同样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录并张贴出去,但我没有正面批判,这就是说,我没有用公刘的嘴巴说话;只是在“译文”的前面,写了一段引言式的文字,大意说,根据多日来的群众性的揭发、批判和分析,该诗可以作如下解读。底下便是白话体的旧诗新译。诗的原句,我已经毫无印象了,但那对甘霖的渴盼,对西天一朵云彩寄予的期望,却历历在目。凭良心说,这两首《无题》,采情工丽,大有步李商隐《无题》诗的气度,倘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不正常,不是风行“微言大义”和“诛心之论”,是完全能够理解为在炎热的苦夏天气,期待一场豪雨,至多至多,也只宜延伸到作者作为“右派”的一员,心情苦闷,巴不得早一点“摘帽子”,如此而已,哪能上纲上线,拔得那么高,那么骇人!
做梦也不曾料到,我的这张“就事论事”的大字报,倒招来了新一轮的排炮轰击,而轰击的对象,则由洋泉转移到公刘了。
由三位难友发难的第一张题为“质问公刘”的大字报,开宗明义,便点了“蒋经国的干儿子”的名,这大概是“破题”罢,接下去,就撇开洋泉的原作,光说公刘的“创作”了。大字报严厉声讨我“借机放毒”,“借酒浇愁”,“借洋泉的黑诗兜售自己的黑诗”,其理由,据称,是我的译文“情感浓烈而意味深长”,云云。我不想公布这些发难者的名字,他们也是受害者,并非元凶,只不过为了早日摘掉这顶沉重的“帽子”,不得不出此下策,打击别人以突出自己的“向组织靠拢”罢了。我原谅他们,并打心眼里同情他们。他们不过是些被教唆坏的可怜虫,他们无罪。但,这三位谁也没有如愿,其中的一位很快就又同我一道打背包上另外一个名叫子洪水库的工地继续劳改去了,半点便宜也不曾捞着。我和他朝夕相处,我从未讥刺过他;此人目前还在祁县中学教书,想必能说真话了吧。
然后,便是接踵而上的大批人马了,几十张大字报揭批我的“罪恶用心”,铺天盖地而来。我辨认着这无数陌生的名字,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是原先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比方《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战士》等等,包括我所在的三班全体,都不曾参与这一大合唱。我内心有点埋怨大队部,为何出这么个难题,让我下不来台。我只能以沉默对待,一言不发。我至今也并不猜疑,是否大队部在背后作怪,不,策划者当是另外一批听信了谣言的人们。他们以为,从中可以捞到“油水”,却不知道,这是在狠心地往我的伤口上大把大把地撒盐!蒋经国啊蒋经国!你怎么老像影子一样,紧紧地伴随着我?难道就这样一直到我死去才算了结么!
我提出抗诉,要求重新审查。大队部以他们也是“右派”,无权受理为由,搁置了。这场风波,至此不了了之。
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难想见,“蒋经国”三个大字,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大标语、大字报,曾一度贴满山西太原的五一广场和街头巷尾,一直贴到我女儿读书的小学。谣言也愈发离奇了,“造反夺权”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早已不满足于蒋经国先生的低档次了(更不必提他的主任秘书徐君虎先生),他(她)们认为,应该实行“大跃进”,干脆把我直接挂在了蒋介石将军名下,张口闭口,骂我是“蒋匪干孙”了。据《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先生透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本人,亲口对他介绍“文化大革命”的特性,说,“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我看,似乎还少了一个定语,是“无齿(耻)的‘和尚打伞’”,对这等不顾事实、毫无道德的表演,我,一个“摘帽右派”,除了乖乖地看着听着外,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