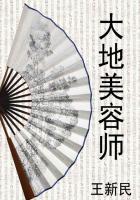老K很喜欢跟我讲他在外面的风光。他说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县长和公安局长家里他也是经常去的,他还陪他们的老婆打过牌。他说,跟她们一打交道,很快就会知道她们的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古话说,一床被子不盖两样的人嘛。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和哥儿们要到公安系统或一些政府机关去帮忙,挂照啊,检查超载啊,收税啊,计划生育啊。他跟派出所的一个所长是哥们,有时候,派出所解决不了的事,也会请他去解决。他说他也知道那些家伙不过是利用他,他一去,没有不赶快交钱或去引产结扎的,如果出现了伤亡事故,他们也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这样,他们处理起来就游刃有余,说,政策是不错的,只不过处理方式有点不当。然后,装模作样地把我处理一下,等大家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把我的处罚解除了,请我喝酒,给我压惊。压他娘的鬼惊,我才不惊呢,哈哈哈。他说得神乎其神,但我总觉得他有自夸的成分。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夸张,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事情,只讲了一点点,还有很多没讲呢。一个人说,真的哩,你不知道,就是现在,外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也要到这里来找我们老大写条子呢。老K唾沫四溅的时候,其他人仰脸望着他,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还补充一句或把他没讲完或忘记了的细节补上。看来他没跟他们少讲,以至他们都能背诵下来了。只有一个进来才两天的家伙,坐在角落里,怯生生地打量着他,既想靠近又有些畏惧。老K指着那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说起来笑死人,这家伙原来也是一个犟头,仗着他老子大小也是个干部,平时大概没少干坏事。那天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跟人家对撞了一下,本来是他自己吊儿郎当地撞到了别人,反倒揪住别人不放,两个人拉拉扯扯的。一个过路人看不过眼,讲了句什么,他伸手揪住那人的衣领把人家一推,骂了句×娘,然后叫人家滚蛋,谁知那人也不是好欺负的,马上一招手,过来两个身强力壮的家伙,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原来,那家伙是公安局的一个便衣,几个人正想找点事做做,这小子撞到枪口上了。呵呵,活该他倒霉,在局子里挨了一顿鞭子,进来后又被我修理了一顿,现在乖多了。是不是?他朝那个家伙一瞪眼,对方赶忙点头。不过他马上会出去的,他老子有门路嘛。老K补充道。
第二天,那个家伙果然被放出去了。老K撇了撇嘴,说,这帮家伙,天生就是做败家子的料,仗着老子娘的势欺男霸女,屁本事也没有,我瞧不起他们,落在我手里,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反正有事没事,老K喜欢找我说话。他说他佩服有骨气有头脑的读书人。他看过很多历史演义,也认识许多英雄好汉,但真正的厉害人,不是像他这样五大三粗头脑简单的,而是文质彬彬甚至穿长衫戴眼镜的,就说×××,不了解的人谁知道他是本县城的黑道老大?他跟你一样,也是戴眼镜,穿中山装,天再热也不露膀子,手臂瘦得跟猴子似的。说实话,有时候我在想,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黑道老大的。但他就是,谁也无法取代他。只有有事要处理时,他才露出他的英雄本色。他一二三四,有条不紊,红道黑道,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无论多大的事,他都能做到不动声色,冷静得让人吃惊。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罗汉,简直是一个政治家。我在演义里看的那些政治家,也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如他呢。那些家伙多少露出过马脚,而他,我从来没见他有露马脚的时候。无论场面多大,事情多么辣(棘)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他名声很大,可以说,从县城到乡下,乃至外地,无论大人孩子,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但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少。其实他每天都出门,像普通人一样喝茶抽烟,逛街买东西。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碰到两个中学生,一个向另一个吹嘘,说认识他,跟他家如何有交情。他听了也只是微微一笑。那两个小家伙,哪知道被他们拿来吹牛的英雄正微笑着坐在他们身后呢。他从不张扬,有时候即使是吃亏和被人欺负也不做声。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买东西,对方占他的便宜,甚至出言不敬,我要出拳还以颜色,他用力一掰我的手腕,制止了我。别看他胳膊那么瘦,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我眼里立时涌上幸福的泪花。我知道,他这是爱护我,瞧得起我。这种幸福感,就是喝茅台五粮液也没法比。我希望那疼痛的感觉永远留在我手腕上。你说,我不佩服他,还佩服谁呢?
我入狱的第五天,老K出去了一次,说是有人来看他。回来时,他手里拎着许多吃的东西,他很大方地把它们分掉了,除了那条大前门香烟。当时,大前门还是高档货。他说他什么都可以戒,就是不会戒烟,烟是有营养的东西,他不抽烟马上就会变蔫,而一抽烟,他又威风了。除了每个人递了一根香烟,其他的他都收藏起来,说是留给我和他抽。我也就不客气,点上火抽起来。跟他客气,他会说你见外。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其实你抽烟没什么瘾,大概你就是要抽烟这个姿势,你喜欢把自己放进那个姿势里去。听了他的话,我吃了一惊,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其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接着,他开始给我表演抽烟的绝技。他说,像你那样抽烟,真是浪费,你的烟草利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看我的。说着,他长长地吸了一口,蓝色的烟雾顺理成章地从两个鼻孔里流畅地出来了,香烟给他的鼻孔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流泻出来的烟雾没有立即飘散,而是再次滴水不漏地被他的嘴巴重新吸收了进去,好像它们忽然有了某种魔法。这次,他让烟雾在肺部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至声息全无,我以为它们不会出来了,或者他会什么魔术,把它们从别的地方排放出去了,说不定我马上会看到他衣服或头发在冒烟。我正在好奇地观望着,却见烟雾重新从他鼻孔里跑了出来。好像它们在他体内捉了一会儿迷藏,然后又开始了你追我赶。他得意地望着我,说,怎么样?我的香烟利用率比你高多了吧?我佩服,说,起码是百分之两百。
不过,牢房里的浪漫主义马上被打破了。一天下午,又一个家伙被推了进来。一个偷了电缆的无业青年。看守一走,几个人立时围住了他,他可怜兮兮地求饶。老K说,你这个家伙,也太不像话了,你可以去抢银行,可以去抢金店,可以去炸什么地方的办公大楼,但怎么能偷电缆呢?难怪前几天我老婆说家里停了电,说电缆被人破坏了,弄得我女儿看不了电视,你知道吗,她最喜欢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八仙过海》,原来是你干的好事!说着一脚踹在对方的肚子上,对方惨叫起来。老K说,再叫,就把你的舌头割掉。那个人马上不叫了。老K说,你别指望谁来救你,要是他们来救你,就不会把你送到这里来,在这里,我们揍你不犯法,是在为民除害。其他几个人也上去戏弄起那个家伙来,有的搔他胳肢窝,有的撒尿到他身上。那个强奸妇女的家伙,有着一双修长的手,指甲也留得长长的,他把指甲嵌进这家伙的肉里,弄得对方眼泪鼻涕一老堆却不敢叫喊。几个人当中,他是最积极的一个。大概他急于把他刚进来时受到的待遇转赠到这个家伙身上去。他们折磨了他至少有一个小时,接着叫他去马桶边“照镜子”。他哇哇吐了起来,他们又叫他像狗一样把呕吐物舔起来,不肯又拳脚相向。那个家伙终究忍不住,拼命地叫了起来,估计外面的行人都能听到。看守再不管就说不过去了。他拿着警棍,打开牢门,冲着大家吼叫了一阵,还在几个人身上来了一下。奇怪的是,他没敢对老K怎么样。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晚上,那个刚进来的家伙再次像杀猪一样没命地嚎叫了起来。看守闻声赶来,每个人都在呼呼大睡,而等他一转身,那个家伙又嚎叫起来。我在黑暗中听到一阵咚咚咚的声音。那声音他们谁都有份,但看守永远也别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带的头。这样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新来的家伙大概终于悟到了什么,不管咚咚的声音多么响,他不再叫了,把身体抱成一个球,任几个人踢来踢去。早晨,他们叫他用牙刷去刷尿桶,再用这根牙刷去漱口。他不再反抗,甚至还显得津津有味。渐渐地,他们取得了和解。
几天后,他便完全融入了这个集体,跟他们一起抽烟,说笑。只是身上还很痛,一不小心就会啊唷一声。可以想象,如果进来了新的犯人,他也会跟他们一起来折磨对方的,而且肯定比别人下手更狠,就像那个强奸妇女的家伙。
本来我想看看书,但想了想,还是没看。我忽然想到,那些狱警真的不懂圣经吗?真的对鲁迅的书那么放心吗?说不定他们是在引蛇出洞呢。
老K对那几个人也爱理不理的,对他们的讨好无动于衷。他似乎越来越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海南那边热闹吧?听说你在那里也是个人物哩,有一次,派出所所长请你吃饭并亲自开车把你送回家,是吧?我眼光没错,一看你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跟许多读书人不一样。你要是跟我们一起混,绝对是个了不起的角色,以后有机会,我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大。你跟我讲讲你在海南那边好玩的事。我敷衍他,这哪是一下说得清楚的?得慢慢讲。我已经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跟他讲。难道我能对他启蒙?我想起自己曾设想过的那个场景,不禁好笑。火种在湿柴上是永远也烧不起来的,在灰烬里更是如此。这些人,已经成了人性的灰烬。但我也不能得罪他,不然,我大概休想活着出去。谁知我越这样,他倒对我越发尊重起来,以为我越有内容。我想起自己曾构思过的一个小说,一个组织的头目为了获得手下人的信任,从路边抓了一个算命的,让自己的旨意通过算命的人说出去,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K还在跟我滔滔不绝。他主动告诉了我许多监狱里的秘密。他说,你别小看了这些狱警,其实他们一个个都是绝妙的演员。有的人,花了钱减刑,狱警便千方百计给他们制造立功的机会,他事先跟对方说好,比如他叫那个人在放风时走在最后,等别人都出去了(自然是迫不及待的),狱警就在早已准备好的地方放起了火,然后大叫失火啦失火啦,这时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几乎是“用胸膛把火扑灭了”(事后,狱警正是这么向上级描述的),“保护了国家财产和狱友们的生命安全”,不用说,那个人立功了,每立一次功减三年刑。多立几次就出去了。当然,不可能老是灭火,得换个花样。那好,再花钱买通某个人叫他假装逃跑,那个人家里经济陷入困境急需钱财,便冒着加刑的危险答应了下来。于是一个跑一个抓,演了一出绝妙的双簧,便再次立功了。至于那个假装逃跑的家伙,家里已经得到了经济援助,也就继续安心服刑了,狱警同时证实他平时一贯表现很好,这次实在是一时糊涂,“请上级部门酌情考虑给罪犯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什么,你不相信?跟你说,只要你有钱,就会减刑。刑期就像量杯上的刻度,花多少钱可以减一格,当然,最好是不要讨价还价。我再跟你讲一件,我有个哥们,杀了人,被判了二十年。他入狱几年后,仇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旅游,居然看到了我那个哥们。他在一家游乐场做事,仇家见了他,以为是看到了鬼,这时我哥们也看到了对方,吃了一惊,但他马上镇静下来,不慌不忙,问客人要什么服务,仇家终于断定,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几年前杀死了他儿子的那个人,便用力揪住他的衣领,要拉他去公安局。游乐场的人很快把我哥们解救下来。那个人气愤地回来报案,相关部门很重视,调查我哥们的案卷,却发现它们已在几年前毁于一场火灾。此事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了,我那哥们至今还在游乐场过得优哉游哉。现在,你相信了吧?他有些炫耀地望着我。
我总觉得,老K跟我讲这些内幕,似乎是想我拿什么跟他交换。他想知道什么呢?
不过后来,我还是和老K建立了一些感情。毕竟是一个很爽直的人,跟我以前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完全不同。跟老K在一起,很轻松,不累。他其实不会掩饰自己。我还发现,别看他高大凶狠,其实有时,他会表现得特别软弱。那次他不知怎么的和狱警吵了起来,狱警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K立即软了下来,脸上露出可怜兮兮的神色,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他人见状,忙装作没听到,靠在那里闭目养神。我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狱警跟他说了什么,但老K的反应也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唯一一次。我不禁想起我一个亲戚,个子高高的,也是当地的一个罗汉,他借了人家许多钱,从没还过,人家也没办法。但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几个公安忽然找到他家里来,他居然腿一软,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一个熟人犯了事,警方来找他了解情况。
没想到我还是比老K先出狱了。看我在收拾东西,老K悄悄跟我说,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了,在我还没进来之前,他就已经接到指示,奉命监视我,并尽量从我嘴里套出什么。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我还够义气吧,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讲。
这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三个月。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因为法庭一直没有宣判。我离开了乡下中学,在县城租房子学外语。学英语的人太多了,我学的是俄语。我想读俄国文学的研究生。期间,跟我有些关系的几个少妇,曾到县城找过我,为了解决身体的饥渴,我再度接受了她们。她们一点也不计较我搞过女学生,坐过牢。这种朴素的民众意识,或许对我日后的思想会产生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县里的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见到我时倒不太自然,眼神躲躲闪闪的,好像坐过牢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小小的县城里分帮结派,互相水火不容。但在对我的态度上却表现出少见的一致。这帮井底之蛙,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粗浅到令人绝望的地步,我跟他们根本谈不到一块去。他们最大的愿望,无非是轮流做一做县文联的主席。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他们,我都是昂然而过的。当然,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叽叽喳喳,大意是说我搞过多少女人或坐过牢之类。倒是外地的一两个朋友,常来拜访我。这时我们又可以高谈阔论一番。我表情严肃。时间长了,我不知道,这严肃是摆出来的还是我真有这么严肃。反正,每当我准备谈自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时,严肃的表情就先挂到了我脸上。它像一个面具在那里等着我,又像一个偌大的会场,在等着我进去,威严地扫视一眼然后开始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