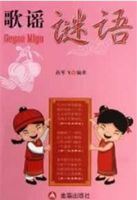群众的意见并没有危及我的政治生命。1977年底,也就是初中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被提升为学校红卫兵团的副团长(团长职位空缺),成为全校性的政治明星。事实上,这意味着我成为了全校“担子”最重的义工:我有出不完的黑板报、做不完的大扫除、掏不完的阴沟、表不完的决心……与我现在寂寞的生活相比,七十年代明星的日子宛如人间的天堂。
但是,我不再有“前途是光明的”自信,因为死亡照常光临,它带着崭新的面具,三次敲响了那“人间天堂”的大门。
第一次,死亡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与他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的爷爷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做客。这个与我同龄的孩子性情孤僻,很少与我讲话。有一天,两位老人到我们家来找他们的孙子:他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带我再去他们家慰问时,两位老人已经非常平静。他们抱怨当时很受欢迎的一部影片里的上吊场面。他们责备他们的孙子不应该太在乎一次小小的考试。他们还说他们对不起自己的儿子。我们离开的时候,两位老人指给我们看他们的孙子上吊的地点:他们住的那一层楼走廊尽头用来装杂物的房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记忆中出现了“自杀”的人。
第二次,死亡是一个隐喻。它通过我身体中第一个器官的衰退来炫耀自己的分量。1977年底,我眼前事物的边界渐渐变得模糊了。班主任老师不断将我的座位往前调。最后,坐在第二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我不得不去医院做检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父亲带我去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检查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口音很重的医生问了我怕不怕光。我不是太明白他说的“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阳光非常刺眼,比如父亲出发去干校的那一天。但是通常我对光线并没有什么恐惧。不过,我却点了点头。这好像正好是医生期待的结果。医生告诉父亲,我应该尽快去配一副眼镜。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母亲带我去长沙市中心黄兴路上的一家眼镜店,为我配人生中的第一副眼镜。当验光师让我戴着他为我选定的镜片去看看街景的时候,我发现世界又变得像从前那样清晰了。但是,我心灵的窗户已经不再是原装的,我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是一种永远的“丢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内疚,对我母亲、我自己以及对整个的世界。我悄悄地发誓,发誓要用一番伟大的成就来弥补这永远的“丢失”。
第三次,死亡是一个句子。其实,它是前一次的一个插曲。只是为了叙述的清晰,我才将它独立出来放在最后。那天在附二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候诊的时候,父亲突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你会短命的。”他接着说这是一个会看相的工人告诉他的。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如此随意地将如此的“天机”泄露给自己年仅十三岁、心理又异常敏感的儿子。我跪在长椅上,面对着明媚的天空,对接下来的视力检查充满了恐惧,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恐惧。父亲1977年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这句话是他一辈子说过的唯一一句能够打动我的话。这句话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的伤口要用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愈合。三十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活过了卡夫卡的年纪。对于一个以文学为天命的人,那个年纪应该是一个心理的分水岭。越过了那个年纪,战栗在灵魂深处的就应该只是对自己过去的羞愧,而不再是对自己未来的恐惧。
我的政治生命于1978年2月17日结束,比“红卫兵”组织“历史使命的完成”提早了半年。政治生命的结束是继器官的衰退被确诊之后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死亡。那是猝然的死亡。那一天离我14岁的生日还差五十天。那一天,母亲从办公室带回来的一张《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报告文学。那篇题目费解的报告文学将一个费解的数学题目带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经历了无数政治的奇迹之后,中国的孤独第一次被一个纯科学的奇迹驱散。“赛先生”的幽灵又开始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七十年代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春天”:科学的春天。
我急不可耐地去寻找《文汇报》,因为我听说那里刊登了那篇报告文学的足本。足本的开头既是对我的诱惑又是对我的羞辱,就像所有不可企及的美的事物。它是一组数学公式,那个奇迹的核心部分。我被这神奇的开头迷住了。原来数学也是一种语言,原来文学可以从数学开始。那篇报告文学成了我见到的第一部后现代的作品。
政治生命的死亡没有引发我丝毫的悲痛。因此,我不可能像那些千篇一律的悼词最后号召的那样“化悲痛为力量”。我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语言和新的隐喻。它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种新的语言直到八十年代还是政治试卷中“试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分析”的对象,直到它最后被“时间就是金钱”或者“效率就是生命”进一步升级。“金钱”和“生命”的隐喻将语言带到了七十年代的对立面。七十年代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和“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年代。
1978年5月6日的一篇日记显示了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对“力量”的向往。在回顾了一段时间来自学的进度之后,我这样写道: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有很多更具体的想法也不时地在我的心中出现。《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提到的那“一步之遥”给我无穷的鼓励。而且我非常想在不久之后就走上通往北京的道路。
在把数学提到中学优秀的水平之后,我打算从物理、化学、外语这些学科突破。
母亲不赞成我今年考大学,那么我必须做好明年考的准备。
数学用许多轶事点缀我的1978年。其中,那一年的全市统考最为精彩。考试的最后阶段,全年级的老师都围到了我的身旁。因为试卷中最后有一道30分的大题(一道将对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极值结合在一起的题目),它的难度令所有的数学老师惊慌失措。他们在等待我的灵机。他们寄希望于我能够为学校争得荣誉。我的每一步推导都引起老师们的骚动。当我的卷面上出现了解题的关键步骤时,老师们发出了恍然大悟的惊叹。那一次我的得分将近满分,与第二名的分数相差32分。
数学教给我节制和逻辑,我相信这是文学的根基。写作是对语言的苛求,进而也就是对写作者自己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一生将是这苛求的祭品”。这是七十年代对我的宣判,是无法推翻的宣判;数学还告诉我“捷径”的奥秘。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所有解法中,一定存在一种最好的解法:它最简洁、最漂亮、最令人意想不到。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问题和解决之间的这种捷径。同样,在文字的组合中,也一定存在着对生活最准确的捕捉和对语言最到位的操纵。这文学里的“捷径”是上帝的作品。不过,写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怀着对语言的无限热爱和敬畏去努力接近这部作品。
为了备战“明年的”高考,我需要自由和基地。工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将暂时空置的住处借给了我。每天晚餐之后,我就钻进“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在那里苦思冥想,勤奋演算,刻苦“攻关”。但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我的道路。一天晚上,我在房主的一摞旧书里发现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它与我好高骛远的天性一拍即合。我贪婪地攻读起来,对作业本上“和差化积”与“积化和差”的练习失去了兴趣。很快,我也对在十五岁进入大学(甚至对上大学本身)等世俗的目标失去了兴趣。
但是,爱因斯坦带来的不仅有相对论,还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崇敬、对和平的憧憬以及对压抑个性的教育的讨伐,还有他学生时代的“成绩平平”。在七十年代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从爱因斯坦的物理转向了他的传奇和思想。我开始迷恋“理想实验”以及不容易转化为“生产力”的纯粹的知识。我开始热爱艺术、崇敬哲学、憧憬和平、讨伐教育并且准备变得“成绩平平”。爱因斯坦在七十年代的出现为我在八十年代的“反潮流”和弃理从文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自杀又一次惊动了我。死者是父亲的同事(厂部的一个科长)。他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门栋,是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并且很礼貌地打招呼的“叔叔”。有一天,父亲谈起那位“叔叔”因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积极表现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几天之后,父亲又带回了那位“叔叔”最后的消息:他从招待所三层被隔离的房间跳了下去。父亲还提到了他溅散的脑浆,等等。那天中午,我悄悄跑到招待所的后面。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工厂的第一年就被安排住在那里。我在那里找了几圈,根本没有找到脑浆的痕迹。我有点失望。我目测了一下三层到地面的距离,那显然不应该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换任何一个其他的部位触地,那位几天前还对我点头微笑的“叔叔”都不可能用那样暴力的方式变成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