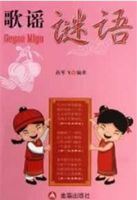在七十年代初期,川医是我们这些三四年级孩子心目中最具诱惑力的地方之一,就像极喜欢在黑暗中聚在一起听鬼故事,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停地打抖,在神经就要崩溃时等待结局。传说这些老建筑群的很多教学用的解剖室,里面成天摆放着一排排的床,上面覆盖着白布,遮蔽不严的白布下面会露出一具具尸体。每天晚上12点钟声一过,就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推门而入,啃咬每具尸体上的肉。第二天,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尸体残缺不全。
我第一次认识荨麻(四川叫喝麻)这种有毒植物,就是在川医的外墙下面。那阵子成都的很多公共建筑都是刷上了白石灰的竖条格子墙,远看像是很粗的甜水面条。我的大腿可以穿过砖头隔出的空隙,但脑袋和身子却钻不过去。这种墙很矮,大多不超过2米,而且很多都破旧损坏了。我们这些孩子踩着砖缝就能轻易地翻过去。在人民公园后面,靠近钟鸣老家的那段墙和劳动公园(青羊宫)的一段墙好像都是这样。那次我们班的彭智、崔拐拐、罗鸿、戴永建几个决定下午逃学,到川医去看尸体解剖。我们几个人中先有一个要翻过去,看看有没有巡逻的民兵,都传说如果被民兵抓到,要被捆起来用荨麻条拷打。和荨麻接触过的皮肤会红肿起来,痛痒难忍。建娃翻了过去,确定没有人,我们才先后跳了进去。记得我拿了个纱网子,一个瓶子,准备顺便到川医里面去打点红砂虫喂鱼。我那天就跳进了一丛荨麻里,先是不知道,然后手和脚全完蛋了,又痛又痒,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掌往头发里使劲擦,试以缓解症状。
下午四五点钟,天气阴沉,校园里极其安静,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看尸体的气氛。我们几人沿路都不说话,提心吊胆地往钟楼摸去。
1972年,川医学校刚复课不久,来的都是各地进修的医务工作者,人员极其稀少。我们悄悄进了钟楼附近的那些老房子里,走廊里阴森森,一股股难闻的腐朽气息和地板的嘎嘎声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甚至听得见自己的血在血管里哗哗地响。每个房子的门都关得死死的,从裂开的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隐隐约约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走动。
几个人赶紧脚踩脚冲出了房子,沿着房子外墙,再一扇子一扇子地寻找。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到真相。在一座老楼边上,有一排像新搭建出来的宽大平房,一大排窗子,玻璃上都刷着白色油漆,窗下是一条排水沟,边上栽着一圈齐胸高的万年青。
这些窗已经失修了,歪歪斜斜关不严缝。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房子里一排床就在窗附近,最近的离窗台只有两三尺远。从床上凸起的白布就知道,下面就是我们急于想发现的东西。
我们选了一扇窗子,不太使劲就拉开了。几个人挤成一团,伸长脖子,睁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房子里头。在浓烈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尸体就在我们面前,盖着一张污渍斑驳的白布。他的双脚跷得高高的,朝向我们。房子里光线昏暗,隐约看得见很多瓶瓶罐罐里面泡着一些发白的东西。房子里的腐朽气味更浓了,煞得人流眼泪。我们几个人中,建娃最胆大,他找来一枝树条,把手伸进窗里,用树条将尸体脚上的白布慢慢挑了起来。
所有人的心跳都停止了。挑起来的白布下面,一只脚露了出来,脚趾甲又脏又长,脚板上的肉干枯、发青,大脚趾背上还有几根黑毛。建娃挑尸布的手停止不动了,僵在了那里。这时—“当”的一声巨响,头上钟楼的大钟炸响了。不知谁大喊一声:“鬼来了!”我们“哇”的一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撒开脚不要命地四处逃开了。
在1974年小学毕业前,我还有几个著名的逃学案例,如拉了班上七八个男生到跳伞塔撮鱼被老师告上门来,当着全家和左右邻居的面被妈妈按在凳子上打屁股;到火车南站爬火车差点摔断了腿;等等。但都比不上这次刺激、过瘾,让人终生难忘的逃学。
逃学真的是实践自由之旅,是冒险之旅(老师要告状,妈妈要打屁股),也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一个学童离开了每天两个必去的点:家和学校。对他而言,他出走的对象和道路即是心灵中最想探索的地方,是梦想之地。当他离开家,装着要去上课或离开学校假装回家,而心中暗想着将要到达的地方,其心中的快乐和狂喜是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后果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逃学的路上,你能感觉到天空更湛蓝,能听到很远的火车声,嗅到未曾闻过的花香气息,期盼遇见料想不到的人,发生永生都不再可能发生的事。逃学其实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多次逃学,为以后大学时代的大逃学(经常从南充逃到重庆或逃回成都,最远一次逃到了二千公里外的海南岛)和再后来的更大规模逃亡或曰流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逃亡的真理就是,生命由自己做主,命运不被别人掌控。1984年底,我弃家跑到了北京,住在李六乙的宿舍里。到天津和胡冬瞎混,再到东北和郭力家、吕贵品、徐敬亚喝酒。第二年夏天,搞诗协办刊被停,半年内走完了整个南中国。此刻李亚伟的一句诗在我耳边响起:“我在逃亡中深深地感受着自由”。
我为什么手短
如果全民公投允许重活十年,并任意选择,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在“七十年代”上打钩。从1969年到1979年,一个人从七岁到十七岁,多么快乐啊!没心没肺地玩完了而又不担责任!干了那么多捣蛋的蠢事,在道德上却没有明显的负罪感。不像我们的爷爷那辈子,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时代混乱而变迁巨大,因此命运难以定夺,有人穿起了草鞋爬过了雪山草地,有人穿了皮鞋留在了城里,我那爷爷左右为难,留在了湖南衡阳的乡下继续教私塾,最后抱憾终生。我父亲那辈因为自己选择了,穿了布鞋,两兄弟十六岁那年离家朝北远走,先加入国民党军,在两党的大决战前夕选择了共产党军,一路往南打下来,解放了西南。这一变换的选择,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付出了超乎他们想象的沉重代价,然后抱病猝死了。当然,我们也不像哥哥姐姐那帮,一腔热血洒向了文革,贞洁献给了知青,最后当了工人或嫁给了农民。
1960~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后,我才姗姗来迟。我是家里的老五,也是幺儿(1980年代任中国幺儿协会会长),我哥哥姐姐都很惨,靠我最近的哥哥万里1960年生,出生时只有三斤多,脑袋上居然没有一根头发,抱在手里,红扯扯的没有肉,像只刚剥了皮的兔子。睡了一个多月的保温箱后,样子还是像个外星人。那些天妈妈吃了一些胡萝卜和十个臭了的鸡蛋,这还是单位发给的仅有的营养品。相当不错了,要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在啃树皮、吞观音土、吃死人肉啊!
我闪过了这致命的一刀。1962年夏天,我胖乎乎地生出来了。妈妈没有多少奶,那时住在重庆的石板坡,离重庆市看守所只隔几个门牌号(28年后又重归故里)。单位隔壁有个卖花生酱的铺子,家里每天都要打几缸子,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我被这营养品灌得又白又胖。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天生的毛病,可能是那时吃花生酱吃出的问题。比如有早起症(早7点前起床就头晕、拉肚子)、东方午休麻痹症(典型的民族临床症状,那时也是国家型疾病,八亿人民都是病友。主要源于营养不良)、晕书症(读书时想打瞌睡)、多动症。这些毛病变本加厉,以至祸延至今,我坚持认为是出生时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的原因而肥胖的,上帝给予了补偿性惩罚。但我妈妈很久以前告诉我另一个有关我出生的版本,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人的来生前世可能是多方位的。
1961年下半年,父母发现已怀上了我,决定不要了。因为在一年前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刚刚生下了我哥哥万里,母子的身体都很差。兄弟两人离得太近了。我的生命是个意外,不在受邀迎奉之列。刚开始我妈妈并不知道,我有绿豆那么大的时候,有了端倪。妈妈开始有些发烧,以为是感冒,吃了许多感冒药。过了些日子,又开始胃痛,以为是肠胃炎,又吃了乱七八糟的抗生素消炎药,治不好,还让中医大夫扎了几天银针。后来才发现那就是一个我在从中做鬼呢!
我妈妈决定打胎了。先是用三七掺酒打,这是打胎的猛药:用一块三七在一只有烈酒的粗碗里使劲磨擦。一次五钱酒,一天三次,连续三天,让我拖着一具全尸出来。几天过后,见没有动静,又用了一招更狠的,从一个从四川马尔康高原转业的骑兵连长那里要来了一个麝香,闻了一天,还吃了指甲盖那么大一块。这虎狼药下去,一棒子非打出来不可了。见又没动静,爸爸心生怜悯,说不定是个女儿呢?那时爸爸可能想要一个幺女来给几弟兄压阵。但所有人都劝,吃了这么多药,折腾了这么久,这孩子受了这么多的罪,早已废了,就是能生出来也是个瓜娃子。那时全家人都很紧张,捏了一把冷汗。
我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知道了为什么只有人类刚出生的时候才是双拳握着,牙关紧咬,眉目深锁,两腿呈骑马状跨着: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是一座西藏密宗的忿怒尊。
这种表情和姿势说明了两样东西:从一个温软的怀抱降临到一个注定要艰辛一生的世界上;另一个则是在降临之前就提前受到了种种磨难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可能属于后者吧。
反正生下来了,全家人失望又担心,又是一个男的,虽四肢齐全,但不知以后有没有后遗症,脑袋瓜不瓜。我真的应该在大夫倒提双脚打屁股让我哇哇大哭时,大声朗读一首骆耕野的成名诗《我不满》,或出示一本张小波、宋强他们弄的《中国不高兴》。我不知道我刚出生时是不是眉头锁得更深,双拳比别人捏得更紧。
这场意外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我的眉头长大后怎么也打不开了,天天皱着,好像有国家大事非考虑不可。从小到大,这眉头给我带来了一系列被误解的烦恼。每当别人找我谈话,我这该死的皱得很深的眉头都让别人以为我在表达不满、轻蔑和不屑。结果是双方大吵大闹,如果是太太,则非闹得要离婚不可。最后我非要大吼一声:“老子天生长得就这样子,妈的,随你便!”
至于双手,则更是悲惨。可能是紧紧扭住母亲身体不放的原因,把手弄坏了,影响了发育。等长大后才发现,我两支手臂不仅长短不一样,居然还比正常人短了一大截。只要是买了有袖子的衣服,肯定要去裁缝店改短:左手剪2公分,右手剪3.5公分。北京新天地三楼改裁衣裤的店铺里,我成了他们必须认真善待的老顾客。
这双近乎半残的手,肯定是当时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对那么多汹涌而来的洪水猛兽,只得死死抓住妈妈的身体,怎么也不能松手。这不是十几年后的跳桥啊,下面有水接住。这是跳崖,只要一松手,死亡翻江倒海而来。
由于手短,双臂在肩膀下面哈起,走路或说话激动时两手的挥舞动作,朋友们都说像个大猩猩。由于手短,钱、权、女人、事业等大凡人生主旋律的东西都抓不住,绝大部分都流失了。但我在妈妈肚子里学会了征服人生的一招,只要抓住了,就打死也不松手。
一个伟大的时代,给人以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思想、工具和基因。从七岁到十七岁,七十年代给了我决心改变不公平世界而发奋努力的抱负,有了这座城市里史地知识前三名的最好头脑,以及一米七八急躁多毛的体魄里面灼烫而可控的精液。
回想整个七十年代,她更像我的父母,我的朋友和兄弟,像日夜暗恋又不知其人是谁的情侣。她就在我的三十年前慢慢长大,离我越来越近。就在我纵身跳下大桥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