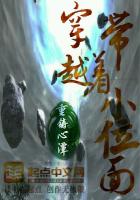拉开清朝宫禁的帷幕会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从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第一帝顺治起,直到康熙初期,在群臣中,每次上朝都会看到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洋大臣,他身着石青色的朝服,头戴薰貂皮制作、顶为镂花金座,上面饰有一颗璀璨东珠的朝冠,朝服上前后绣有展翅欲飞的鹤,脖子上挂着闪亮的红宝石朝珠,他就是钦天监汤若望,这是一个中文译名,因为Adam听起与中国的姓“汤”音相似,入乡随俗便取了这个中国名,他的原名应该叫约翰·少尔·冯·贝尔(JohannAdamSchallvonBell。)
这位汤公进入中国得到朝廷的重用,官至一品,开创了由西洋人直接掌管钦天监大权,一下成为“通天”的角色,连顺治大帝也称其为“玛法”,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对其更是敬重,“愿先生以女儿相待”,这位“欢洽如家人”的汤公,还可以免其常例,随时入内宫,而顺治皇帝也常去他的寓所观览他的教堂、书房及花园,有时还既进便餐,这种关系看来非同一般。一位外国人怎么会得到中国至尊和广大老百姓的崇敬,给予他这么高的待遇和荣誉呢?
汤若望是继罗马传教士利马窦之后,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的。
崇祯年间,大科学家徐光启,这位万历年间的进士,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已经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接着在不到一年时间又兼任文渊阁大学士。
徐光启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农学,他还致力于天文学、数学。较早的时候,他师从罗马来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是介绍和吸取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的一生著作很多,如编著了《农政全书》、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译著了《几何原理》等等。
正是应这个徐光启的邀请,汤若望才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参与编修《崇祯历书》,可惜那不是一个莺歌燕舞的时代。他的命运在这里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将明朝推翻了,徐光启、汤若望的《大统历》的编修工作自然就此流产了。
接着,在硝烟与厮杀中,努尔哈赤的第14子多尔衮——他15岁时被封为贝勒,幼年时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因此得到他父亲的钟爱和器重,年仅17岁就随皇太极出征,功勋卓著,晋升为“和硕睿亲王”,这是满洲贵族的最高爵位、最年轻的大将和“巴图鲁”。
1644年,多尔衮接受了降清汉官、汉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进取中原。多尔衮作为一介武夫,再没有比在战场上驰骋、厮杀而痛快的事情了,他立即打出了“救民出水火”的旗号,整肃军纪,亲戴“大将军印”,四月初七于盛京祭天,七日出师进军山海关,在吴三桂的引导下马不停蹄,一路顺风直指京都。
1644年5月2日,多尔衮统率的八旗大军,在明朝的文武遗臣隆重的仪仗接迎下,进入北京,入武英殿。
在此之前,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掠夺,汤若望所在的宣武门外教堂毫无疑问也是打击、砸烂的目标,在一片狼藉中,汤若望脑子里一片茫然,不但他的基督教文化不能在华传播,就是自身的安全性命也无保证了。
他面对四方,高仰着头颅,伸出双臂,向着青天口中呼叫道:“主啊……救救我吧!”
天主是仁慈的,他得救了,不过不是被天主而是被一位中国教民、明朝的遗民、原宫廷的一位官员李祖白救的,他家就在教堂附近,西单的斜街口内。那是一座大宅院,他的母亲信天主教,请来汤若望在他家里避避风头。
全家人对这个外国传教士极其恭敬,主人同仆人一起为其操办生活,尽量让饭菜适合这个日耳曼人的口味。
“中国好,京都好……”汤若望一遍又一遍的自我祷告:“中国的朋友更好!上帝会把和平、福祉带到这里的。”
他在这个四合院度过了几天难忘的生活,清晨到主人的后花园中读书,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地方,早饭后继续学习,安排的是中国文化,从天文到地理典籍,涉猎范围很广,午后他便安排时间向这个家庭布道。
一天,主人从外面神色慌张地回家,叙说外面发生了一件恶劣的事情,一个外国人被杀害了。他们担心汤若望的安危,感到这种动乱不利于汤若望,劝他是否考虑返回德国。
“不,不,我要在中国工作下去!”汤若望坚定地说:“这种动乱在欧洲不久之前也发生过……我不认为奇怪!”确实,16世纪的欧洲,如同中国政局一样,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在中国是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连年征战,威胁着大明江山;而此时欧洲政教之争,疆土之争,宗教之争,正处于交织、交替之中,而且越演越烈,爆发了一场德意志人民争取自由、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1523年—1524年)。他本人就是在这个历史舞台悲壮的一幕下,诞生在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城堡之中。
“谢谢,谢谢!”他面对这些黄色皮肤、善良的中国人说:“我的任务是将福音传给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可现实是,一个泱泱大国的京都一片混乱,到处漂着硝烟、血腥、抢劫、掠夺、烧杀……
不久,又一件事惊动了京都,说清军已从东面过了山海关,势如破竹,明将吴三桂已向清军投诚,由他带路正向京都进发……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里,一面白色龙旗出现在京都的紫禁城上,接着一队队手持弓箭,腰挂腰刀的清军骑着蒙古马开进城来。李自成的大顺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满鞑子来了!”劫后余生的人们望着这支胡服骑射的军队,不知是喜还是忧,市民们的心情在这个时候真是复杂极了。
这时,清军中的一位年轻将军在武英殿里为了稳定局势,发布了他的第一号公告王令,言明清军入关是为了“除暴救民,灭贼以定天下,为尔等君复父仇。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烧民舍,不如约者,罪之……”
9月19日这天,北京城内热闹起来,人们从千家万户走出门来,看皇帝去天坛祭天,然后祭宗庙、社稷,举行入主中原登基大典。
汤若望在市面稳定一些的时候便离开了西单回到宣武门内的教堂。他一觉醒来天下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大清皇帝已经定都燕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个新的朝代宣告建立。
京都的市民们关注着这个变化,作为西方传教士的汤若望更是十分关心这个变化,他对多尔衮的一号令很赞赏。同他私下里往来的原明朝一些官吏又被清廷招进了宫。而且汤若望看到他认识的原明大学士冯铨已被授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士心得则民心得”。汤若望经过一段阴郁的日子心情终于开朗了,他重新振作起来信守其志,打算在这个迷人的东方国度里,开拓传教领域,广布福音,去奉献天主赋予他的生命和才智。
他想到他的使命,心中愉快起来,回忆起他得到耶稣教会总会长的批准启程来华时的隆重场面。
1618年4月16日,这一天里斯本的码头上集聚了几百人,在这里,耶稣教会为远行的使者。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告辞仪式。汤若望的亲人、好友都争先恐后进行吻别,表示对他的尊敬和崇拜。码头上圣歌朗朗,直上云天。传布和平的使者们,他们的双足是多么可敬可亲啊!
起锚的炮声响了,“善心耶稣号”远航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驶向波涛万顷的大西洋。这只船上连同水手共有三百多人,他们将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半年,才能到达东方华夏大地那块神秘的土地。
经过半年的航行,这年的10月,“善心耶稣号”到达印度果阿。他们将在这里休整、度假。
1619年5月,赴中国的船继续它的航程,航向直向东方。两个月后,汤若望终于结束了海风、海潮、恶心、呕吐、头昏、失眠的折磨,进入中国南海,在澳门登陆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欧洲大陆。四十年后,这位“长须、碧眼”的中西交流史上的纽带、桥梁、好朋友长眠在阜成门外三塔寺,他的墓碑上有康熙皇帝的祭文: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西洋教士的圈子里经历过大顺军的骚扰,大多数人采取着观望的态度,主动想同当局取得联系,苦无良策,既不能孟浪、唐突、冒险而行,又不能旷日持久地观望下去。正在这时,多尔衮向京都又发出一个公告,意思是说,随着大批的满洲、蒙古旗兵进入北京,住房已成大的问题,他要求城中非满洲人在三天内通通搬迁到外城去,把现有的住房腾出来给大兵和满洲官员们。这个命令给北京城内的非满洲人一个大震惊,一场百姓比李自成进入北京还要慌乱的局面出现了,满街是搬家、逃难的人,谁都不敢违抗军人的命令,谁也都晓得这位满洲正白旗主的厉害,人们到处争相搬迁。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自然也是内城,按照命令也属搬迁户。因此,教堂也卷入了搬迁的恐慌、忙乱之中。而汤若望这时所想的不是怎样搬迁、到哪里落脚,他的思维一下跳出了这片混乱,他仿佛看到了别的,看到了一条新路,看到了他未来宣教的场合、他的目标。
汤若望向朝廷呈奏折,要求天主教堂不搬迁,这引起了他的同伴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的极度担心,认为会由此引起更大的祸端,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是不是冒险?人们传说,清兵是杀人不眨眼的!再说朝廷的搬迁命令,无人敢于拒绝……
善良的传教士们都对汤若望进行责备,认为此举凶多吉少。
汤若望心境十分平静,他说:“我递送奏折时,亲王亲自接见了我。”
亲王忙了一天的公务,直到晚上才想起汤若望送来的奏折,马上派侍卫转达到皇上那里,请他旨谕。
多尔衮从武英殿走出,一看天色几近寅夜,但他仍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没有疲劳之感。他这才想到,好几天没去看他的嫂夫人了,何不就此走一遭儿,同时把他今天接见一个“洋大学问”的事向她介绍一番,看看她的意思。
“我们新朝刚刚建立,需要各种人才,哪怕鸡鸣狗盗,有一技之长就要接纳。”皇太后说。
第二天一大早,汤若望就到礼部候旨,不出他所料,皇上的圣谕下了。他像获得了一件珍宝,一边走,一边在心中呼唤:“主啊,你把黑暗驱走,带我进入光明……”
现在是朝廷的命令颁布的最后一天,唯有宣武门内的这个教堂纹丝没动。清兵围住了这里,堂内也进去了一大帮子清兵,几位教友正在虔诚地向大兵解释,请求宽容,留情。可是清兵怎会答应,正要下令动手,门外走进了汤若望,只听他高声呼道:
“皇上有旨……”
清兵一下愣住了,睁眼一看是皇上的旨谕:
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这时,准备占房的清兵在章京的指挥下,没有二话儿地退出了教堂。
清廷对于这个曾奉前朝的“洋大学问”是怎么看的呢?
多尔衮主张:“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他对明朝的降将、降兵、官员,予以大胆录用。
一天,多尔衮又来到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卧室,他们一边喝着马奶茶一边聊天。
“你前天说的那个‘洋大学问’……”博尔济吉特氏说:“他写的奏章我看过了。是个人才。”博尔济吉特氏说:“‘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我们正需要历法啊!”
“是啊,这么大的国,不能没有一个好的历法,特别是中原人,他们盖房、造屋、出行、婚、丧、嫁、娶、访亲、探友、剃发、打井……连跟女人行房都要挑选适宜的、吉利的日子,历法不准怎么行。”
不用说中原汉人,我们满人、蒙古人做什么大事,也离不开历法的,你带兵打仗,第一需要的是历法,时辰有了差误,那不就要贻误军机吗?
多尔衮说:“明朝好多典籍毁于战火,惟万历时故籍存,我想我们应该有一套新的天文历法。”
清廷决定招纳这位“洋大学问”时,汤若望更以积极态度向清廷靠拢。他把从万里以外的家乡带来的新仪器献给了朝廷。同时又呈上奏折,说他预测到将有日食月食发生,并附上了详细报告:
臣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
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现览。
1644年,“洋大学问”汤若望又向朝廷进呈三大仪器:
混天星球一架。
地平日晷一件。
望远镜一台。
除了仪器之外,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旧历法的七大谬误之处。
皇上和博尔济吉特氏、多尔衮、济尔哈郎都先后参观了这些“洋玩意”,对历书范本更感兴趣。
济尔哈朗说:“他的书写得头头是道,不知他说的可准确?”
博尔济吉特氏说:“这不要紧,到时候让九王派几个人看看就是了。”
1644年初一日,多尔衮命大学士冯铨率领一班子人马,有钦天监官员,还有汤若望一同登上观象台,当场验证那种推测日食的结果是否准确。
京都人们说起日食,人心惶惶,称这是“天狗吃日头”,大街小巷敲锣打鼓、烧香祈祷,都怕被“天狗”吞下。
汤若望对此只是一笑,他什么都没有说,径直登上天象台上。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惴惴不安,大统、回回和西历代表人物,他们的历法都将面临一场严峻的实地考验。
大统历的代表拿出了自己所测的日食起复时刻与方位,接着回回历的代表也拿出自己的东西。
钦天监的报时官员不断向冯铨和在场的人报告时辰,大统历所报的时辰过了,日食没有出现;回回历的时间也已经过了,日食也没有出现。汤若望所报的时辰到了,随着报时官的宣布,“天狗”出现了……
回到朝内,大学士冯铨如实向朝廷回奏真情:
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
这位“洋大学问”为什么预测得那么准确呢?原来他用的虽然不是欧洲最先进的方法,但他应用的“密合天行”推算法比起中国当时的诸种预测法先进得多,有充分的说服力,朝廷在这时对汤若望作了明确表态:根据上述认识,朝廷才决定颁旨试行,“乃以新法造《时宪书》颁行各省。此我朝用西人治历之始。”(这里的“时宪”两字,是睿亲王多尔衮所赐。其含意在“以昭朝廷宪天义民”之意。)
不久,朝廷正式颁发了对汤若望的任命:
钦天监信印着汤若望掌管。凡该监官员俱为若望所属。叫嗣后一切占候事宜,
悉听掌印官举行,不许紊乱。
钦此
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历史跟这位远道而来传播福音的神甫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奉罗马天主教皇的派遣,为的是来东方布道,不想做官,却一下被任命为朝廷重臣,这使得他一方面受宠若惊,他巴不得一有机会就接近最高统治者,向他宣示致意,布施福音,使其皈依天主教,一方面感到困惑,做梦都没有想到皇上会启用一个外国佬掌管这样重要的部门,不过用的是他对天文方面的学识,而不是它的教职。他想干的事业是传道,他在诚惶诚恐中镇静下来,表示辞谢,向皇上上奏疏。
……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报官之理。况臣迭遵督率直职掌之旨料理历法无难,至于掌管印信,臣何敢当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良……
看了这位神甫的奏章,朝廷中昼夜想向上爬升的官员予以冷笑,骂他“傻鸟!”心里想,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太大了,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做官油水多么大,有差银俸禄,有奴仆,有小妾,有轿子座,有房子住,有人给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