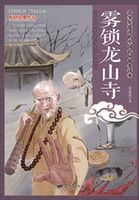一
第一次见到张家白时,我知道这是将与我有故事的男人。他正在把手伸向一张老唱片,而那张录制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唱片,也是一直是我要找的。
程砚秋的《春闺梦》仅有这一张,我们同时把手伸向了那里。
我对他说,先生,我找了它好久了,至少有一年了。他看了我一眼,散淡的眼神寂寞着。我也是,他说,为一张老唱片,我常常会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转。
我们谁也没有想放弃,从十三岁喜欢京剧以来,我就迷恋在那些老唱片里,其实我可以听现在程派五小们的唱片,非常清晰质量又好,但是我偏偏喜欢那些几十年前的老声音,丝丝连连地穿越了时空而来,有的声音只是一种感觉,根本听不清,可我喜欢。
这样吧,他说,不如,你去我那里去听。
就这样认识了张家白。总穿亚麻色裤子和白毛衣的男子,一个做着广告公司摄影师却喜欢着古老京剧的男子,如我一样,沉迷在几十年前的故人声音里。
彼时,我从美院读完全部油画课程,正在准备去巴黎深造,那是艺术的梦想之都,在申请签证的这段日子里,我整天在街上转悠,为的是把能买到的老唱片全收集起来到巴黎去听。
而张家白是二十八岁的男子,有着干净忧郁的眼神,在我们相爱之前,我问他恋爱过没有?他摇头。我怎么会信,二十八岁的英俊男人,开一辆不错的本田汽车,广告摄影的新宠,不曾恋爱,怎么可能?但他屋里确实没有女人的痕迹,有过女人痕迹的屋子我看得出来,即使没有女人的东西,但气息总是有的。
那么干净雅致的屋子,只是白,到处是白,被子毛巾甚至沙发地毯,甚至那些白得有些瘆人的白窗帘。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唱机里正放着《白蛇传》,正是断桥那一段,白素贞唱着:“我本峨眉一蛇仙,为谁相思到凡间。”
我怀疑不是在人间,因为面前站着穿白毛衣的男子,他张口便是:“啊,娘子,你来了。”
只为这句话,我在瞬间爱上了张家白。
没有一个男子有这样前生来世的感觉,但是他站在门前叫的那一声娘子,让我在这个早春的夜里,泪湿春衫透。
终于有一个人,这样懂得我。
爱情就是这样吧,久久等待总也不来,来了时,居然只是一个刹那,有时候我就那样发着呆盯着张家白,然后说,官人,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是的,我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穿白衣的男子呢?
二
更多的时候我与张家白是一起唱戏的。
我们唱得最多的是《白蛇传》。常常,我会唱断桥那一场,舞起水袖忧伤地说:“红楼交颈春无限,谁知良缘是孽缘。”又唱:“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进雄黄,你伤心将我诳,才对星盟誓愿,又随法海进禅房,你忍心叫我断肠,夫妻的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还有小儿郎……”我唱得泪眼婆娑,他听得亦是双眼泪湿,我常常想,我和张家白,怎么会是今世之人?甚至活得没有一点烟火气息。
即使我在厨房里看着他慢慢用小火为我煲汤喝,我亦是觉得不在人间。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他与爱玲最欢爱的一段,他写:我与爱玲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常常在张家白做饭时我会从后面抱住他,然后问:张家白,这一切到底是真的吗?
我很怕离别,怕我的签证下来。
但张家白说,当然不是真的,我们是人妖相恋,哪会有结果?你是人我是妖?我问。
不。他说,我是妖你是人,我才是《白蛇传》中的那个白素贞。我笑他胡说,他用京剧中的念白说了一句许仙曾说过的话:我的娘子是假的,可她的情意是真的啊。
我的情意是真的。所以,我扑到他怀里落泪,让他发誓只对我一个人好,因为自始至终我不信他没有谈过恋爱。
更多的时候,我缠在他身上不肯下来,真的似一条蛇,因为我总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种游离。
甚至,曾有三天我们没有下床,打电话叫了外卖,吃过饭之后,我们继续在床上,即使什么也不做,即使只那样拥抱着,张家白伏在我耳边说,玉良,为什么,我们的缠绵会是这样?一片又一片。像开花的树,不是一朵,是千万朵。
那是因为我爱你啊。我说,我喜欢这样一片一片地。
谢谢你,给我这么多。
他居然说到谢谢。我生气,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谢谢。他扭过头去,取了烟给我,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学会了吸烟,一种凉凉的薄荷烟,吸到肺里后,像是爱情的味道。
就这样,他一只手搂着我,一只手拿着烟,黑暗中,两支烟一闪一闪,像小狐狸的眼睛,他突然问:玉良,我要是死了,你会想我吗?
这样的问总像一把剑插到我心里,我用吻封住他的嘴却感觉到有什么咸咸的东西流到我嘴里,明明我没有哭。
张家白在哭。他哭了。
我见不得男人哭,一点点地吻干他的泪说,张家白,我不去法国了,我要嫁给你,给你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像你,女孩像我,我要和你慢慢到老。
老?张家白忽然笑了,你说,人老了会是什么样?
我奇怪他说话总是这样颠三倒四。
秋天的时候,我的签证下来了,父母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我对他们说,我不想走了,我想嫁人。
三
再度缠绵的时候我说起自己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妹妹,还有一直疼爱我的外婆。因为与自己的恋人说这些事的时候会有一种贴心的温暖,仿佛已经把他当作了家里人。
但对于他的家人,他只字不提。
我问了,他便显得极其烦躁,甚至失手打了东西,我从后面抱住他,一起看院子里那棵美丽的银杏树掉叶子,为什么,张家白会缄口不提他的家人?但我还是对他说,明年春天,明年春天我们就结婚吧。
他沉默着,一直没有给回答我。我卖了画,然后一个人跑到谢瑞麟的金店里订了两只戒指,十分美丽而惊艳,像我,也像他。
冬天很快就来了,法国的那家学院给我发了邮件,希望我尽快去报到,否则真要错失良机了。我没有告诉张家白,我只告诉他我订了两只美丽的戒指。
我看到他眼神黯淡,好久,把我轻轻地抱在怀中,再然后,是更紧地抱住了我,甚至我都勒疼了,好像是怕一撒手,我就会跑了。
那天,他把那张老唱片送给了我,程砚秋的《春闺梦》。我嗔笑他,反正就要嫁给你了,放到谁那里还不是一样的。
张家白的生日就要到了,我偷偷买了一件礼物给他,是一条皮尔.卡丹的皮带,是的,我要拴住这个男人,这个我喜欢的爱抽薄荷烟的男人。
当我提着生日蛋糕和皮带开了张家白的门之后,我看到了电影中的一些情节,一个妖娆的女人正在张家白的床上与他纠缠。
我的蛋糕掉到了地上,那上面的奶油摔变了形,张家白三个字歪歪扭扭了,是的,在我心中,他歪歪扭扭了,甚至一钱不值。
那条皮带,被我剪成了若干断,像婴儿的尸体,不成型,那么绝望地散在地上。
我早应该知道,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我怎么可能是他第一个女人呢?
再说,他的职业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美艳的女人,让他不动心怎么可能?
甚至,我连一句无耻都没有骂他就下楼了,风很大,雪不知什么开始落的,落到脸上硬生生地疼,我好像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声“娘子”,还带着哭腔,但我疑心是自己的幻觉,我与张家白,从此隔了千重山万里路,不再有任何关联。
我再也不是他的娘子。
我只是断桥上那个心碎的女子。
白素贞曾悲切切地唱:纵然是异类,我待你的恩情非浅。我掏出兜里那两枚精致到悲哀的戒指,把它们抛到了我路过的雪湖中,那不过是想证明地久天长的道具,有谁,还想要这样的道具?
四
五年之后,我带着自己的法国老公和一岁的孩子回北京开画展,五年前的一切,早就随着巴黎的浪漫云淡风轻。
凭着记忆,我画了一个男人头像。
因为那样忧郁而绝望的眼神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导师说,玉良,你这幅画是最让人落泪的,因为那男人的眼神里既有爱又有绝望。
我画的是张家白。
那是初到巴黎时画的,每画一笔,我的泪就落一串,我知道,今生今世,我是最后一次画这个人。
我的画展很成功,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去画展与人合影留念。在张家白那张画前,很多人围着看,其中一个男人说,也只有张家白有这样的眼神吧。
他叫出张家白的名字时我愣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画的是谁。
我看着他,你认识张家白?
是啊,他说,我们是中学同学,他后来来了北京,不过现在也许早就在疯人院了。
疯人院?怎么会?
他们家族中的历史,所有人到三十岁都会精神分裂,无一幸免,他姐姐和哥哥都是三十岁那年疯掉的。
我待在大厅里,像棵失去了水分的花。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真的,二十八岁以前,他没有爱过,而生日那天的一幕,明明是他演给我看的,因为,他知道我会去的。
疯掉?是的,一个知道自己要疯掉的男人怎么会轻言爱情,而我给了他致命的诱惑,我们是一类人,喜欢着那些老唱片,喜欢着《白蛇传》。
他果然是妖啊。他说过妖与人是不能相恋的。他说过的。
那张叫《悲伤》的画卖了十万块。法国的老公问我怎么终于舍得卖掉了?
我没有答他,因为在我心中,那张脸已经刻进心里,如影随形。
而那张他给我的老唱片,每次听我都会有泪浅浅地浮出,程先生幽咽婉转地唱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