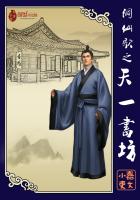“吧唧”一块肥肉准确地丢进大盆。我喘了口气,想着伊凉的话,思考片刻后对她说:“拿猴子练习,应该容易命中,但你要尽量射击它们的头部,心脏位置是其次。假如哪天,你们面对的也是狙击手,即使先命中对方的心脏,他若意志力惊人,仍可利用死前的8至9秒钟时间,捕捉到你的镜像将你射杀。对狙击杀手而言,爆头是首选的射击位置。”
傍晚的太阳格外红,余晖里卷带的风,好似破旧的空调器,吹在裸露的皮肤上,一股儿凉一股儿热,撩拨人的心绪。只有我自己知道,现在是在和死亡赛跑的搏命线上,任何不必要的歇息,或者不合理的行为而导致时间浪费,都将增大我们遭遇危险的概率,使整船的人丧失生命。
甲板上的光线,由暗红转为黑红,夜晚很快就要像幕布一样垂下来。芦雅和伊凉停止了射击,脸上带着充实和解放的欢愉,背起狙击步枪,和我一起将杀死的咸水鳄拖进舱内大厅。
鳄鱼在屠宰时,散发的气味儿格外浓烈,估计方圆一公里范围内,多数食肉动物都能嗅觉得到。幸好大船是在河流中央,若是在森林附近的陆地上,危险性就难以想象。
拖着最后一只三米长的大鳄,我和芦雅、伊凉三人一起,行动快速地往舱门里拽。两岸的树林里,在夜幕完全降落下来之前,已经有大范围的异动。那些夜间开始活动的大型猎杀动物,鼻息出奇灵敏,我很怕它们会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大船甲板上。所以,为了安全,我们还是早早地进入船舱,将舱门锁住。
大船在辽阔且深不见底的森林大河中央,即使夜里会出现能爬树和游泳的丛林豹,也只能远远站着大河两岸,挺着鼻子冲大船望梅止渴。除了有制空权的禽类,水中或陆地带爪的猛兽是很难爬上甲板的,我暂时没什么可担心。但就在我们把最后一条未宰割完的鳄鱼拖进舱门之时,金属门板垂落下来的一瞬间,一只呼呼拍打着翅膀的飞禽,仍然悄悄地落在了船尾。虽然我无法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但那团漆黑的影子,犹如一丛低矮的灌木,着实不小。
鳄鱼的烂脑袋,一滑过门槛,舱门几乎是应声而落。我不想再提起沉重的舱门去甲板上看个究竟,我想这一大团会飞的黑影,应该只是想在我宰割鳄鱼的位置捡些细小的肉屑,假如它长了凿子嘴,还可以刮食凝固在甲板上的鳄鱼血。如果我出去生硬地将它赶走,等我一关上舱门,它又会重新落回到甲板上。况且我此时已经非常疲劳,不想去理会这种琐事。
可是我又有点担心,因为森林里有很多食肉动物一旦吃得心满意足,就会在附近逗留守候;更可怕的是,万一再惹上那些类似蚂蚁那样、有侦察兵属性的凶猛生物,彼此传递信息,到时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生物,把甲板活活堵死。希望那些血肉斑痕,能在夜间被那些飞禽啄食干净,免得引发无穷后患。虽然大船和水的连接处,仅有首尾两根粗大的锚链,但也最有可能成为危险的导火索。不过,若是几只幼小爬虫顺着金属锚链爬上来,对我们倒构不成多大威胁。
池春把整艘大船的犄角旮旯翻了个遍,仅仅找到二十斤左右的食盐。她告诉我,这条船没有冷冻室,厨房里仅有一台两立方米大小的冷冻柜,大船抛锚后,为了节省电源,也已经断电两天了。
这些情况,令池春很焦急,但也是我之前考虑过的,靠咸盐腌泡抑制鳄肉变质是不可能的,冷冻更不可取,我们还得依靠过去在山洞居住时的方式,将鳄鱼肉曝晒和烘干了储藏。只要我们的食物储备充足,再解决大船的动力问题,就可以朝我们家的方向前进,离开这座充满野蛮和死亡的原始荒岛。
晚餐的时候,由于鳄鱼肉是从活体上刚切割下来的,所以煮出来格外鲜美。我还让池春给大家增添了夜宵,补偿几日来每个女人被亏欠的肠胃。
诱饵笼子提上甲板后,发现沧鬼已经咽了气。他身体的边缘部分,已被鳄鱼们啃得露出了森森白骨。这老家伙的脑袋顶上,给小鳄鱼细长的嘴巴扯去厚实的一块皮肉,露出颅骨的凹槽里,汪着一滩凝固的血水。
沧鬼的脚掌和脚后跟也不知去向,只剩下肿胀着的黑色血管和筋骨,如拉断的电缆线裸露在旷野,颤巍巍地抖动。
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大厅中间宰割剩余的几条鳄鱼。池春知道,这么多肉一定要靠明天太阳的烘烤,才可以保证大船远行前的补给。所以,为了让我少些劳累,她又发挥她的领导天赋,带动其他女人们一起参加劳动。
女人们此刻像渔夫们勤劳的妻子,吃饱喝足后无怨无求,七手八脚地跟着一起忙碌。她们把木盆里的鳄鱼肉抬起来翻扣到小圆桌上,然后和池春一起,拿着厨房的刀具切成一片一片的,为明天的工作提前做第一道工序。
芦雅和伊凉两个小丫头,虽然练习了一天的射击,但也不肯闲着,一起参与到加工食物的行列。我想让她俩的双手接触一下血液和碎肉,找找感觉,这对将来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很有帮助。
到了后半夜,困乏的女人们都去睡了,几张圆桌上堆满切好的肉片,只要明天的太阳足够毒辣,把这些小圆桌抬上甲板,再找些干净的木板松散地摊开来就可以了。这时我也着实有些累了,想睡上一会儿,便找块个门板儿,垫在舱门处的楼梯口,抱着填满子弹的冲锋枪,准备挺到天亮。
大船内部的每个角落都由池春指挥着,打扫抹洗得格外干净,消毒液的味道还依稀萦绕在鼻尖。
“噗噗噗噗,咕隆咚咚。”今晚的天气,应该月朗星稀,不会有雨点和海风。这种不寻常的异响,急速地撞击着我的耳膜,听起来像一只只大笨鸭从树上跌落的声音,可因为马上扇动了几下翅膀,看来摔伤的可能性不大。
我急忙跑回睡舱,从池春睡着的小板床前取了那个小镜子。池春是个极其注重仪表的美丽女人,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她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格外娇媚动人,这个小镜子,便成了她每日醒来观察面容的私家宝贝。
回到舱门口,像上次窥视鬼猴那样,把木棍夹住的小镜片,从舱门开启的缝隙下悄悄递送出去。我双膝跪着顶在楼梯沿,使劲儿弯腰弓背,歪着脖子和头,半只眼睛对焦在折射的小镜片上。
这次倒不需要闪电的恩赐,灰青的夜空中,挂着一轮扁圆的黄月,好似怀孕八月的妇人肚子。偶尔几抹阴云,像流浪的帆船,从光亮处经过。
凉飕飕的风,夹杂着虫鸣和鱼儿在河中甩尾的水声,从门缝下挤进来。小镜片中的世界,一点也找不到白天的景象,仿佛我此时正窥视着另外一个世界,神秘且充满敌意。
“呼呼,噗噗……”又是两三只拍打着翅膀的黑影,从月光下模糊映射着的小镜片上划过。但我依然看不到落在甲板上的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忽然,我双臂的寒毛立起大半,此情此景,远比对付人类要刺激得多。
小镜片来回摆动,捕捉可以看到目标的镜像,只见河对岸的树冠,仿佛在一夜间蹿高了很多,把那颗黄色的月亮也挡在枝头后面,如无数锐齿形的小叉,捅进了一块奶油月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