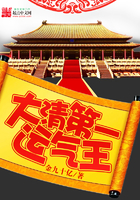黑子驾着严守大给的木船从绿河口进到蒲圻,沿途见村问村,见寨子问寨子都没找到玉荷。他在蒲圻城里遇到了一个叫麻子张的汉子,两人很投缘,相谈中知道了他是朱晓梅的丈夫。麻子张是专门进山收山货的人,他坐黑子的船沿绿水河收了不少山货。
这天黑子催促麻子张上船去绿水河上游去寻找玉荷,随后麻子张提出不去咸宁城直接进通城崇阳阳新等地去看看。黑子不明白问道:“就从这里进山不行?”
麻子张道:“如今只有通过咸宁进去,从绿水那水路不好走,如果不驾船要翻山越岭,搞不好遇到绿林好汉我们两就玩完了。”
黑子道:“那你为什么说不去咸宁可以呀?”
麻子张道:“不去咸宁不等于不去它周边啊,操近路不是一样的吗。”
黑子笑道:“你怕我遇见了朱晓梅,怕我把朱晓梅带走,我可没那缺德,既然你对朱晓梅好我也高兴,高兴她嫁给了个知道疼她的男人。”于是,求麻子张道:“你再不要水性杨花了,去关心朱晓梅。”沿途麻子张爱采花问柳,黑子知道他是个在外浪荡惯了的人。
黑子把朱晓梅当成了自己的妹子托付给麻子张,麻子张感动了。表态道:“只要我有口气我一定对朱晓梅好。再说男子汉在外面那没有点韵事的呀,不难在外面的寂寞日子怎么打发,真有柳下旬坐怀不乱的事情吗,这只说明他是个太监。”憨憨一笑后道:“在外面没法,露水夫妻使得要个把不然在哪里落脚呀,可对自己家的老婆那时始终不渝的。”
黑子想到自己不也是同麻子张说的一样吗,就道:“玩是玩,过家是过家两码事情,你能分得开就行。”结着话锋一转,“你是不是原先有老婆找朱晓梅当二房呀?”
麻子张叹口气道:“过去苦,人又这样你说能娶到媳妇吧。说不好听的良家女子怎能看中我呀,就拿林竹山婆娘来说她不也是把我拿来解闷吗,她肯真心跟我好吗,要是那样早就跟我跑了。”
黑子道:“那个林竹山的老婆?”
麻子张笑道:“在别人家住了一夜还不知姓名啊。”
黑子才知道要为自己献身而不肯留名的女子是林竹山的老婆。忙问道:“她叫什么?看样子不是山里人怎么与林竹山一个猎户是一家?”
麻子张一笑,“她叫文青青,是个风尘女子,艺名叫月里桂,你看她皮肉不是那么娇嫩吗,别人可是汉口黄陂街里的一枝花啊,好多进城卖山货、贩鲜鱼的都喜欢去哪里散心。”
黑子记住了文青青这个女人名字,难道她可是文老板的女儿不成,他盼望的是世间同名同姓的人多,不是文老板的女儿最好,口里却道:“贩鲜鱼我也贩过,黄陂街我也去过怎么不知道哪里有这些板眼啊?”
麻子张笑道:“那里是乡下女子为了备嫁妆特地来做事的地方,再说有能力家的女子那个来这呀个地方卖身她真实姓名我也不知道,来的都是穷得很的,又想找个好男家的女子。”
黑子道:“窑姐还有你说的样子,卖身未出嫁!”
麻子张笑道:“你不懂吧,我可是个跑四方的见得多,女子出嫁如果没有陪嫁的男家不会善待的,至于钱的来路可以说亲戚给的、借的都行,没有钱万万不行,这就是潜规则。”
黑子道:“真有这事,不好解释啊!”
麻子张道:“一般都是娃娃亲或指腹为婚,有的男方后来家境贫穷就同楚剧张大洪被岳父辞掉一样;女的为了盼久的婚姻只好走这不了,当然是人不知鬼不晓啊,这大个汉口就一定被熟人碰着,那也太不走运了。”
黑子打破沙锅问到底,“那还有呢?”
麻子张道:“你莫看那些有眉有眼的女大学生一身傲气,有的是攀大款才有钱读书的呀,说白了是那些有钱人的玩物,连个小妾、二房都当不上。”
黑子叹口气道:“看来女子最苦,男人还可以卖苦力,她们没有四两力,咳,这世道。”这时也到了咸宁火车站附近,马上要拐到去山里方向大道口。
这时黑子见一家三口,男的挑着担子,女的把头巾拉得很低背篓背着衣物、怀里紧紧抱住孩子,在那低低的头巾下黑子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女子快步跟前面挑担子的男子挤进了火车站。
黑子要返回去,也要去火车站被麻子张拉住了,“往这边走,走快些今天可以赶到一朋友家过夜。”
黑子道:“我看到了一个熟人进站了,我去打个招呼。”说完了要向火车站去。
麻子张死死地拉住黑子“你不想找你老婆了,熟人有么事可以打招呼的,搞不好把你找老婆的事情给耽误了。”其实他看到了朱晓梅在火车站带着儿子在卖盐茶鸡蛋,不想让黑子碰到。其实朱晓梅抱着儿子是去赶火车的,她与麻子张的一位熟人约好,搭火车去湖南。
黑子一时没想到会是玉荷,可玉荷看到了黑子,她要火速离开冤家的视线,为了新的未来、为了儿子她大胆而又痛苦地割断了对黑子的那份思念之情。
黑子在麻子张死缠硬拉下踏上了进山之路,久久回忆那一瞬刚间的眼神,是熟悉,可不相信会是玉荷,因为在玉荷眼神里从未冒出如此强烈自信、充满希望、温柔体贴的眼神。
与麻子张从山里回到蒲圻,麻子张把山货叫来搬运运到了。
朋友有遇有分,在此黑子与麻子张分手了,不过他相信玉荷还在鄂南那个腰子角落里,可是鄂南太大了,山也太多了,每个山要去那得好长时间啊,他想到了在湖边镇的弟弟,还有目前下落不明的么妹;除此,还有老藉的祖父母。他赶回绿水河,好在那木船还在,他打扫了后又启程沿绿水上行,找遍绿水沿岸村庄,可惜还是没有见到玉荷。
黑子在这鄂南一晃就是几年,这几年自己是生活没有定所,在船上吃喝安息。可是那木船已老朽了,看来要好好维修了,再者这船是自己没经过闫晏擅自驾了出来的,几年了也还还给别人了,就是再好的朋友不能失信于别人啊。于是他决定暂回湖边,找严守大借个好点的渔船,那船有中舱棚子。这中舱棚子是固定的,内面铺有很平的木板,白天是休息与吃喝的地方,晚上把铺盖一放就是个小房,可以日不晒雨不淋。不像这闫晏的木划子,不仅成旧,而且没有中舱棚子,晚上只好把找到的几捆稻草铺在舱内睡觉。
在这船上几年,是日晒雨淋,下雨时只好用油布包裹铺盖,不管日夜只要遇到下雨,只好穿上蓑衣;白天倒好说,要是晚上,那慢慢长叶真难熬啊。这几年,自己身体还健壮,风里雨里挺过来。最让人不安的是,李吉他们一伙掌了权,可是现在军阀各地为王,各地出了好多揭竿而起的大小军阀与军棍们,老百姓陷入了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真是,要是遇到了李吉,一定好好质问下,你们得了天下又如何。
前不久,在绿水听到了有了新的一拨人,他们跟土匪与国民党不一样,说是为穷人的。黑子笑了,世界上没那好事,从盘古开天地,无禄不起早,谁去用生命去换来老百姓的福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