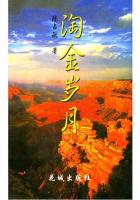岳剑忠在一家茶话室的包间里跟程枫见面。
程枫带来一大包手帕。
他对岳剑忠说:“你要我收集手帕,是不是跟白莹的死有关?”
岳剑忠拍拍他的肩膀:“你这个记者真了不起,快成为侦探了!”
他告诉程枫,白莹在熟睡中被人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巴,白莹拼命反抗,咬下了手帕的一角,但因反抗无效被闷死。
岳剑忠拿出那块布质碎片:“它嵌在白莹上颌门牙上,被取出来作为重要物证。”
“能找到相同类型的手帕,就有可能追踪凶手。”程枫也以“行家”的口吻说。
“正是。”岳剑忠有些激动地说,“这是白莹在濒死期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线索!”
程枫将带来的手帕,一条一条地摊开放在桌上。
岳剑忠和他一起,将这些手帕跟白莹咬下的手帕一角逐一进行比对。
这些手帕因质地和花色差别太大而被否定。
当程枫再拿出一条手帕摊开放到桌上时,岳剑忠兴奋地说:“有门了!”
程枫也说:“这条手帕还真靠谱!”
“从白莹咬下的手帕一角有两道金线来看,好像是这种类型的手帕。”
岳剑忠再次将两者进行比对。
程枫也凑过去看了看,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只是相似,而不是完全相同。”
“但这条手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岳剑忠将这条手帕收起来,“阿枫,谢谢你了!”
“不必谢我。这些手帕都是刘艳收集的!”
“那就请你代我谢谢她了!”岳剑忠问,“你同刘艳的关系进展如何?”
程枫莞尔一笑:“原来只是想借用她的电台跟你们联系,现在真的是那么一回事了!”
案情跌宕起伏,云波谲诡,岳剑忠忙于应对,几天都没有回十月初五街跟童娟见面了。
今晚他刚进门,童娟就挖苦道:“大侦探,你可是个稀客,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
岳剑忠没有答话,略显疲惫地坐到沙发上。
“白莹死了,你刚抓到的线索又断了。”
童娟忙着给他倒茶。
“谢谢。”岳剑忠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茶,“真香!”
“大侦探,我在这个时候选择到东亚歌舞厅参加歌咏队,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吧?”
“确实如此!白莹是那里的舞女,她的死说不定跟东亚歌舞厅有什么纠葛,你正好可以帮我摸摸情况。”
童娟拿出岳剑忠的那本《刑事侦查学》,翻看了其中的几页,边思索边说:“凶手为什么要杀死白莹?白莹这一死,对谁最有好处?”
“这个问题提得好。阿娟,看来你阅读这本《刑事侦查学》不是硬啃书本,而是勤于思索、联系实际。那么你说说,白莹之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认为,想得到油库坐标的人,是不会杀死白莹的。只有知道油库坐标藏匿地点、甚至已经拿到油库坐标的人,才会谋害白莹,杀人灭口。”童娟认真地说。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岳剑忠赞许道,“白莹以死告诉我们,油库坐标已经不在她手里了!”
“能够知道油库坐标去向,或者已经得到油库坐标的人,一定是认识白莹、甚至是她最信赖的人。”童娟进而分析道。
岳剑忠顺着这个思路说:“这个人或是自己动手谋害白莹,或是雇凶杀人。”
童娟自忖道:“白莹的交游甚广,会是哪一个呢?”
岳剑忠说:“阿娟,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而夺回油库坐标,是你参加东亚歌舞厅时尚歌咏队额外的重要任务啊!”
童娟凝重地点点头。
岳剑忠向她投以企盼的目光。
少顷,童娟问:“大侦探,白莹的祭奠会明天开,你去不去?”
“当然要去,”岳剑忠肯定地说,“明天的祭奠会,白莹生前的好友都会参加,她那个最信赖的人也可能会去,这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
“可惜我明天不能去。”
“为什么?”
“周经理此前就作了安排,明天歌咏队有专场演出。”
白莹的祭坛庄重而华丽,在鲜花的簇拥下,白莹的遗像凄清地微笑着。
祭奠会还没有开始,许多人就来到会场。岳剑忠问韩雪,今天的来宾都是哪些人?韩雪向他介绍,来宾中大部分都是我们东亚歌舞厅的同事——舞女、歌姬、乐队成员和工作人员,还有白莹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
人们议论纷纷:
“谋杀一个住医院的病人,太残酷了!”
“这个凶手真可恨!”
“抓住他的话,一定会判死刑吧?”
“那当然,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明知白莹被绑架过,她住医院又不派人保护,警察厅太不负责任了!”
时辰一到,东亚歌舞厅经理秘书罗西娅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宣布:“白莹小姐祭奠仪式开始!请东亚歌舞厅经理周福源先生致悼词。”
周经理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祭坛,环顾全场,清了清嗓子,语速缓慢地说:“在南国的天空下,一颗艳星陨落了!日月黯然失色,为她表示悼念;濠江掀起波涛,为她奏响哀乐。白莹是我们的舞国皇后,她跳的艳舞,舞步独特,粗犷奔放,令观众为之倾倒。她在台上跳舞时如此认真,休息时还忙着替客人送饮料,表现出崇高的敬业精神。白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广大娱乐业人士树立了楷模。她的生,如夏花一样的绚丽,她的死,像秋叶一样的静美。白莹小姐,安息吧!”
周经理的悼词令来宾为之动容。
告别的哀乐悲壮婉约,像沉重的铅液缓缓流淌在庄严肃穆的会场上,人们依次走到祭坛前,点燃香火,向白莹的遗像致敬。
女宾们面对白莹的遗像,幽幽地啜泣。
参加祭奠的宾客越来越多,新点燃的香火越烧越旺。
岳剑忠机警地扫视着每一位来宾,并不时地向韩雪问些什么。
一位青年男子走到祭坛前,点燃香火,双手合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白莹的遗像。
他的目光阴郁而痛苦。
这引起岳剑忠的注意。
蓦地,这位青年男子的双手剧烈地颤动着,表情愤怒,眼睛充血,紧紧地盯着白莹的遗像。
他忽然紧闭双眼,两只手抖动得更加厉害了。
过了好半天,他才睁开眼睛,朝白莹的遗像三鞠躬,转回身子,分开众人,默默地走了。
岳剑忠悄声问韩雪:“他是谁?”
“我也不认识,”韩雪思忖片刻,“白莹当过陪舞女郎,可能是她的客人。”
“能打听一下吗?”
韩雪点点头。
在周曼兰祭奠白莹时,韩雪主动告诉岳剑忠,她叫周曼兰,也是我们东亚歌舞厅的舞女,但大家都讨厌她,因为这次周经理发动跳艳舞,她第一个表示拥护。但她对白莹还不错。
周曼兰祭奠完毕,等了一会,李明秀匆匆从外面走进来。
周曼兰埋怨道:“明秀,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李明秀气喘吁吁地说:“陈所长把我拖住了。”
周曼兰不满地说:“这个人真是,大白天也不让你休息。”
李明秀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快去祭奠白莹吧!”周曼兰催促道,“我在外面等你。”
李明秀走到祭坛前,点燃一炷香,却不急于插进香炉里,将它拿在手上。
青烟在空中飞扬缭绕。
李明秀的哀思也像青烟一样。她想到白莹惨遭不幸,自己的前途也捉摸不定,百感交集,悲从中来,禁不住呜呜咽咽地低泣着。
她将手中的一炷香插进香炉,掏出手帕揩拭眼泪。
这条手帕跟程枫提供的手帕属于同一类型,但与白莹咬下的手帕更相像。
岳剑忠的眼睛顿时睁得滚圆。
莫非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岳剑忠悄声问韩雪:“你认识她吗?”
“认识,”韩雪说,“她叫李明秀,是白莹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东亚歌舞厅的歌姬,但现在被一位老板包养了。”
“那她现在不上班了?”岳剑忠问。
“她是‘专职情妇’。”韩雪说。
时尚歌咏队的专场演出完毕,田芳芳对童娟说,担任艳舞教练的余江,自己开办了舞蹈训练班,教授西洋舞蹈,可以去看一看。童娟看到时间还早,就跟她一起去了。
余江二十八九岁,身材高大健壮,眼睛深邃明亮,脸庞轮廓分明,颇具男性魅力。
他正在教学员们跳一种组合舞,四个人一组,在音乐声中一进一退,动作整齐,姿态优雅,舞蹈的节奏像时钟上的摆一样。
余江见田芳芳、童娟进来,向她俩挥挥手示意。田芳芳还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不要停止跳舞,随即跟童娟走到墙边,在长椅上坐下来观看。
这时,一位青年男子(他在白莹的祭奠会上因表现与众不同引起岳剑忠的关注)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冲到余江面前,厉声问道:“余江,你上星期天晚上到圣玛丽医院去干什么?”
突如其来的状况令余江惊讶得像挨了一闷棍,说不出话。
正在跳舞的学员们都停了下来。
“你上星期天晚上到圣玛丽医院去干什么?”那个青年男子又问。
刚回过神的余江说:“方刚,你想怎么样?”
余江知道对方的名字,说明两人互相认识。
“你上星期天晚上去了圣玛丽医院,第二天就发现白莹死了,怎么解释?”方刚质问道。
因提到白莹的名字,田芳芳、童娟对视了一下。
“方刚,你说什么胡话?我上星期天晚上根本没有去什么圣玛丽医院!”余江辩解道。
“你去过!我找你两天了,今天才找到你!”方刚的语气十分肯定。
“我没有去,你看错人了?”余江提高了音调。
“肯定是你,不是别人!”
余江缓和了语气:“现在不争论,等我上完课,再坐下谈行吗?”
“好吧。”方刚坐到椅子上。
余江继续教学员们跳组合舞。
童娟指着方刚问田芳芳:“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田芳芳悄声答道,“但不熟。啊,他跟刘涛经常在一起。”
童娟回到姨妈家跟岳剑忠碰面时,将这个意外获知的情况告诉了他:有人指认余江在白莹死前去过医院,这个人跟刘涛很熟,名叫方刚。
李明秀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听唱片。
门铃响了。
李明秀坐起来,心里很纳闷:晚上八点了,还有谁来找我呢?陈所长说他在家陪老婆,今天是不会来的呀!
门铃又响了。
李明秀关掉唱机,冲着门外喊道:“哪一位?”
门外有人答道:“是我,刘涛。”
李明秀打开门:“是阿涛呀,你今天晚上不演出?”
刘涛站在门口说:“白天已经演过了,周经理叫我们晚上休息。”
“晚上不演出的日子真是难得。”李明秀深知娱乐业从业人员的艰辛。
“是呀。你曾经对我说,你的老板有事不能来的时候,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无聊,想找个人谈谈心,排解寂寞。”
“对,我说过。”
“我今天来,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
“你要是忙,我就回去了。”
“我正闲着没事干,你来得正好。请进吧!”
李明秀将刘涛请进屋,随手把门关上。
刘涛坐下后,李明秀提议:“我们一起喝点酒怎么样?”
“好主意!”刘涛很高兴,但转而一想,“只是不知道你的老板今天晚上来不来?”
“他说今晚在家陪老婆,不能来。”
“那太好了!”
李明秀拿来一瓶葡萄酒和两只高脚杯,往杯里倒了酒。两人举起酒杯。
“阿涛,我们在干杯之前,你得说点什么?”
“说什么呢?”
“怎么,难倒你啦?平时你不是挺会说话吗?”
刘涛想了想:“这是葡萄酒吧,我就吟一首关于葡萄酒的诗。”
“好哇!”
刘涛清了清嗓子,用拖长的音调吟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诗太伤感了!”李明秀说。
“但这也是对当代的写照啊!”刘涛还沉浸在诗的意境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将士们征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亲人们在想念他们,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我们有幸生活在澳门这个孤岛天堂里,在举杯畅饮的时候,难道不应该缅怀他们吗?”
“经你这么一解释,我倒认为你选的这首饮酒诗还真有现实意义。”李明秀由衷地说。
“哎,阿秀,唱一曲怎么样?”刘涛问。
“行啊!”李明秀爽快地答应,“唱什么呢?”
“怎么?你这个歌后也为难了?”
“你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爸爸妈妈不幸被日机炸死,我和多病的哥哥相依为命。有一首歌叫《思乡曲》,它的内容和我的身世相仿,我就唱这首歌吧。”
刘涛鼓掌欢迎。
李明秀唱道:
村前几户人家,村后几树桃花,爸爸和哥哥种田,我和妈妈采茶。
春天里桃花芬芳,夏日里小鸟歌唱。
妈妈许我长大,嫁给心爱的情郎。
谁知平地起了风波,山坡里放了一把野火,爸爸妈妈死了,只逃出我和哥哥。
白天乞食四方,晚上睡在弄堂,看不见我的家乡,每日里东飘西荡。
李明秀唱罢,眼角闪着晶莹的泪花。
刘涛受到她的感染,也陷入沉思中。
少顷,他才说:“阿秀,唱得太好了!”
“也许是有感而发,才唱得投入。”李明秀端起酒杯,“不说这些了,我们干杯吧!”
“好,干杯!”
两人各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李明秀在斟酒的时候说:“我们听听唱片怎么样?”
“好啊。”刘涛说。
“你喜欢听什么?”
“电影《古塔奇案》的插曲《秋水伊人》。”
“我也喜欢这首歌。”
李明秀找出唱片,摆放到圆盘上,然后扶正机头,放下唱针,顿时,如泣如诉、婉转动听的歌声从喇叭里流泻出来:“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
李明秀又往两只酒杯里倒酒。两人一边听唱片,一边谈话、饮酒。
门铃突然响了,李明秀吓了一跳。
刘涛问:“谁在按门铃?”
李明秀颦蹙眉头:“不会有人来呀!”
门铃又响了。
“真的有人来了。”刘涛说。
李明秀竖起指头贴在嘴唇上,示意刘涛不要说话。
她走到门边:“是哪位?”
陈飞在门外答道:“是我,老陈。”
李明秀心里咯噔了一下,随即装作高兴地说:“您来了太好了!请等一下。”
陈飞问:“阿秀,你在干什么啊?”
“我正在换衣服。”
“我俩什么时候忌讳过换衣服呀!”
“不过,还是请您等一下。”
“噢,那就依你吧!”
李明秀悄声对刘涛说:“不得了哇!”
“谁来了?”
“我的老板。”
“你不是说他今晚在家陪老婆,不会来的吗?”刘涛问。
“是呀,他怎么又来了呢?”李明秀也很纳闷。
“让他进来吧,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事。”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说不清楚呀!”
“那我得赶快走。”刘涛站起来。
“你怎么走?”李明秀提醒道,“他把门堵住了,你出不去呀!”
“那怎么办?”刘涛走到窗前,向下面望望,“这么高的楼房,我不能跳窗户,跳下去准会摔死!”
“是呀,怎么办呢……”李明秀焦急地搓着手。
“要不,学电影里的那样,我躲到床底下?”
“不行,不行,还是学戏剧《柜中缘》,你躲到大衣柜里去吧!”
陈飞在门外催问:“阿秀,衣服换好了没有?”
“快好了!”李明秀打开大衣柜,示意刘涛躲进去。
刘涛缩了缩鼻子:“好大的气味呀!”
“柜子里都是些高档时装,有什么气味?”
“纺织纤维的气味嘛,我最害怕这种味道!”
“将就一点,快进去!”
李明秀将刘涛往柜子里推。
刘涛被迫躲进柜子里:“那你快点应付他呀!我闻长了柜子里面的气味,会发生变态反应的,到时候可别把你俩吓坏了!”
“别耍嘴皮子了,克服一下吧!”
李明秀关上柜门。
陈飞又在催她:“阿秀,你今天换衣服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呀?”
“我正在穿你最近给我买的那套时装,正在试镜哩!”
李明秀走到茶几边,把刘涛含过的烟蒂衔在嘴唇上,使烟蒂沾上口红。她对酒杯也做了这样的处理,然后将门打开,让陈飞入室。
“陈所长,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李明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娇声娇气地对陈飞说。
“别总是陈所长陈所长的,就喊我飞哥。”
“好,飞哥,晚上好!”
陈飞反身将门关上:“阿秀,你怎么没有问我,说今天不来,怎么又来了呢?”
“我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我巴不得您天天来。”
“是这样的吗?”
陈飞坐下来,跷起二郎腿。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李明秀给他冲咖啡。
“但我要告诉你,本来我今天晚上要去家里陪老婆,但她临时接到亲戚来的电话,到氹仔打牌去了。”
“氹仔离市区够远的。”
“是呀!她今晚肯定回不来,所以我就到你这里来了。”
“这样真好。”
李明秀将咖啡递给陈飞。
“那你想不想我?”
陈飞呷了一口咖啡。
“当然想,”李明秀也坐下来,“当女人不容易,生在乱世的女人更不容易,像我这种唱歌的女人特别不容易,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客人,如今我只服侍您一个人,您却这么照顾我,让我过上幸福生活,给我哥哥治病,知恩图报,是人之常情。”
“这话很中听。”
陈飞走到茶几边,看到两只酒杯,拿起其中的一只,问:“阿秀,有谁来过吗?”
“嗯,歌舞厅的同事来过。”
“男同事还是女同事?”
“当然是女同事。这不,香烟屁股和酒杯上还沾着口红哩!”
陈飞看到烟蒂和杯口上确实沾有口红,说:“你的女同事来了我欢迎,要是男同事来了,我就不放心。”
“怎么会呢?”李明秀直摇头。
陈飞又坐下来,端起咖啡喝了几口。
“我有时猜想,你这么年轻,会不会趁我不在的时候,跟年轻的男人在一起?”
“绝对不会!除了您,我还从来没有对别的男人有过好感哩!”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您正因为年龄大些,饱经沧桑,才有一种成熟的男性美;而年轻的男人涉世不深,像毛孩子,我怎么会喜欢他们呢?”
陈飞高兴了:“你这话倒说到点子上去了!当今的许多年轻人,不思进取,不学无术,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比如说,你们歌舞厅的刘涛,就属于这种人,我很讨厌他。”
李明秀一惊,不由自主地看了大衣柜一眼。
陈飞没有注意李明秀的眼神,却说:“阿秀,去把我上次没有喝完的酒拿过来,我想喝两杯。”
“嗯。”
李明秀拿酒过来,给陈飞倒酒。
“你也喝一点。”
李明秀顺从地说:“好。”给自己倒了少量的酒。
陈飞问:“阿秀,我不来的时候,你有些寂寞吧?”
“那当然。独守空房的滋味可不好受。”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相依相伴,我也不舒服呀!”
“那您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去?”
“我何尝不想?我是个公职人员,只有离了婚才能再娶。”
“那您为什么不离婚?”
“阿秀,你有所不知,我的这个老婆,是我上司的女儿,我怎敢提出离婚?”
“那您当初为什么要跟上司女儿结婚?”
陈飞问:“你要听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李明秀说:“当然要听真话。”
“是啊,我们的感情已到这个份上了,我要对你讲真话。”
“那就讲吧。”
“我讲了,你可不能对我另眼相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怎么会呢?”
陈飞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说:“我上司的女儿其貌不扬,但我的上司想找个青年才俊做女婿,我当时刚来澳门,仪表不错,又有学位,被上司看中,而我在澳门没有背景,正想找一个靠山,于是两好合一好,我就做了上司的乘龙快婿。”
李明秀同情地说:“这真是难为您了!”
陈飞叹了一口气:
“是啊,结婚十年,没有真感情,我十分苦闷。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澳门成了孤岛天堂,美女如云,很多人趁势换老婆,梅开二度,三度,甚至四度,我真羡慕他们!但碍于上司的原因,我动弹不得。幸亏遇到你,我这像荒漠一样的心才得到滋润……”
陈飞说着,就要去搂李明秀。
突然响起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