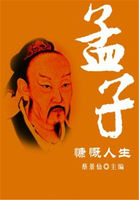林肯创建的党派把大会搬到了与佛罗里达大陆仅两条堤道相连的小岛上。自我隔离效果不错。总统提名当晚,自由城临近的黑人区发生暴动,迈阿密联络警长沃尔特·黑德里杀死了4名暴动者。全国媒体大力关注的依然是可笑的帽子和虚华的演讲,并未对此多加注意。迈阿密的另一个大事件也基本隐藏在幕后:尼克松忍受着缓慢而肮脏的羞辱,日夜为他本应已经到手的东西努力着。尼克松的策略人把政纲听证会都设计好了,接着里根结束了8州旅行,在7月31日周三现身。
8月5日的周一清晨,共和党会议小岛外传来新闻,《纽约时报》的马尔科姆·布朗在玻利维亚监狱里采访了一个年轻的法国马克思城市战理论家雷吉斯·德布雷:“他被新左翼奉为至圣……他受人尊敬的父母是富有的巴黎律师,已在两街区外订了旅馆,两天一次给他提供食物和酒。”当日清晨的《时报》还称如果明智的话,尼克松可能会选一名自由派做副总统候选人,可能是洛克菲勒或林赛。每个还在支持他的保守派都想看看他把灵魂卖给了谁。
保守派深受民间传说影响,传闻过去的大会都被“纽约的少数秘密造王者”破坏了。“诈欺在进行”这个短语响遍了白沙海滩、蓝绿色泳池、粉色大理石门厅和供给高层人士的早餐上。
木槌落下,会议开始。迈阿密大主教做了祈祷:“我们的心很沉重……恐惧的乌云笼罩着许多市民的心。”
接下来,约翰·韦恩念得声情并茂:“我斗争了很久才决定站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因为我和孟加拉虎一样不懂政治。”他说约翰·伯奇会有时会出现在里根的宣传片里,尽管“我读了一些评论,一些左翼朋友说我在做最后一搏,我对此表示疑问。”
洛克菲勒抵达时宣布,他得到的坚定拥护代表是里根的两倍。这个声明在韦恩获得的持续掌声中显得令人生疑。
而里根最近拜访过的南方代表反复告诉他,如果他宣布竞选,他们就可能转投给他。下午4点,里根回到迈阿密海滩,在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了竞选消息。
据瑟蒙德的心腹哈里·登特说,接下来的事情他从未见过。凭空冒出大批里根支持者。问及如何反应时,里根答道:“天,我很吃惊。像从天而降一样。”
尼克松的人尽量保持镇定,提醒自己,记者常制造冲突以证明对得起自己薪水。他们在67年初争取到的新奥尔良政治宠儿正准备为尼克松声辩,首先是塔沃议员,然后是马里兰的阿格钮州长,俄克拉荷马的杜威·巴特利州长和肯塔基的路易·纳恩州长。
尼克松抵达了迈阿密国际机场。原计划由媒体在竞选飞机出口处作现场直播,但没人预料到飞机一路顺风,把他送到得早了些。尼克松耐心地在座位上等,然后大步走下舷梯,就他“迟到”一事致歉,说他亲爱的佣人马诺罗·桑切斯和卡斯特罗领导下他的古巴难民妻子取得市民身份,他去参加仪式,刚刚返回。
他僵硬地说:“这标志着旅途的结束,还有,我们认为国家自此走上了追寻新领导权的道路。”谨慎推进的人群狂热地欢呼起来。尼克松强迫自己保持微笑,头脑中重复着瑟蒙德议员的低语:人群包围着他,是在恨自己错信了“狡猾的迪克”。
尼克松的车队驶向了焕然一新的希尔顿广场。每座天桥都有保安监视,直升机在头顶轰鸣。另一群“自发聚集”的人群等在入口。一辆货车门开了,放了一把气球。尼克松容光焕发,好像毕生从未见过这般景象。有人觉得每时每刻都可能发出枪响:想要射杀尼克松,现在正是时候。
晚上的会议沉闷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通过电话向人群演说。镜头对着停车场,里根的车得到了南方代表源源不绝的支持。这位老演员散发了全身魅力。怀特就里根会如何获胜做了解释,这与南方代表的“团结方针”相关。如果大部分代表投了一位候选人,他在代表团中的获胜就毫无悬念了。怀特称佛罗里达、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代表团主席都已承诺,如果里根勉强未达到多数票,他们会把决定性一票投给他。里根请求所有代表都做出类似承诺,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很多人说“我们真的很想投你,议员,可——”他们都收到了瑟蒙德的电报,称,“不论在越南,还是最高法院、军事优势、财政和分权政策,尼克松的定位相当成熟。他是1968年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国家需要他,而他需要迈阿密的我们的支持。大会见。”他们也收到了瑟蒙德的电话,因为没留书面记录,所以说得更直接:“投里根就等于投洛克菲勒。”这正中保守派疑心:如果大会演变成多次投票的混乱局面,东部媒体造王者可是什么都做得到的。
当晚的瞩目点揭晓时,里根的竞选车顿时放空了。“女士们先生们,我向你们介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伟大的共和党人,亚利桑那来的下任议员,我的朋友与同僚,尊敬的巴里·戈德华特!”
大会中心迅速移了过去:“我们要巴里!我们要巴里!我们要巴里!”
希尔顿广场,尼克松的队伍也被里根热潮惊得目瞪口呆。会议中心,南卡莱罗纳代表团的电话响了,是约翰·米歇尔找哈里·登特的。他们老板次日要约见一面,而米歇尔想把时间提前到现在。
登特和瑟蒙德十点后到了尼克松套房。他们一直在反复核实动摇的南方代表团,企图熄火。一般登特先与他们谈,开很多身为议员开不起的条件。瑟蒙德再讲些战争的老话,强调尼克松已经承诺通过他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小计划,并许诺:“尼克松不会强加什么。”而尼克松则是事后才听到这些。
他们都隐约知道彼此的困境:瑟蒙德豁出去给一个自己选民不信任的人作担保;尼克松则慷慨地许诺未来共和党内的南方议员席位。开会时,他们不多谈什么,只交换眼神。这就是他们要开会的原因。
瑟蒙德得到了承诺,然后在尼克松手里塞了一张纸。
周二清晨报纸头条:“哥伦比亚当局草拟惩戒改革措施”;“市长命令,杀死沃基根纵火人”。里根和瑟蒙德见了一小时面。如果在传播的新流言是真的,里根就要熄火了。传说他将会是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里根拿讽刺堵住了公众的嘴:“就算他们绑了我,堵住我的嘴,我也会扭扭耳朵说出‘不’字的。”登特内心有点失落,他每分每秒都感觉得到尼克松的颓势。
但尼克松正准备兑现给瑟蒙德的承诺,这一招可能会逆转下滑趋势。他曾面向每个南方代表承诺,会回应他们的任何问题,和1964年那个羽翼未丰的海军老兵一样。当年,他想当国会的头头,便拿着海军帽去乞求小心眼的南加州财阀;而现在,为了他早该得到的东西——他的提名和折磨南方佬的权力,他不得不再次去求南方共和党人。
他首先与六州代表谈了话,接着又与其他六州代表碰了头。第一次会面中,只有在场人士知道他说了什么。第二次,《迈阿密先驱报》弄进一只录音机,将对话内容发表在了次日晚间早版的报纸上。
只听登特首先说:“我们别无选择,想赢的话,只有投给尼克松。我们必须摒弃情感,用理智决定。相信我,我热爱里根,但尼克松是对的人。”
然后尼克松开门见山,谈到最关心的副总统问题:“我保证,我不会用任何会分裂我党的人。”
一位北卡代表问尼克松是否接受“仅因种族融合政策就强制学生乘坐校车”。尼克松说:“北部也有同样问题……我并不认为您将南方或是北方拿来说事的做法是妥当的。”
接着,他说:“一个孩子要与其他大两三年级的孩子一起,还得融入一个奇怪的群体。我认为校车接送会毁了孩子。学校的目的是教育。”
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常出言不逊,而他已能出色利用这一点。他有意绕进一个圈子,称学生需要校车接送的唯一原因是要强制种族融合,尽管最高法院的新肯特郡决议显示,通常,校车只是强制种族隔离的工具之一。
他以尼克松式的装饰音,翻来覆去说南方共和党的老一套:“不管是当地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国内法庭还是法官,我都不认为他们比你们当地的校董事会够资格做出决定。”黑白混居住宅问题:“和枪支管制一样,应该在州一级处理,而不是提升到联邦级别。”他做了结语,称尼克松政府决不会向“某些特殊民权群体的需求”屈服。离开时,他挽着瑟蒙德的臂膀。
投票日在周三。
洛克菲勒的经纪人伦纳德·霍尔与里根的克里夫·怀特是朋友,共同对付尼克松,商议拦截他的首次投票胜利。他们都相信,一旦首轮胜出,之后便势在必得了。怀特打电话约区域负责人五点会面以做最后一搏时,他发现,要将里根和洛克菲勒加在一起,洛氏争取到的代表远远不够。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怀特说,“我们收拾行李打道回府,或者继续努力,希望事情有转机。”
突然,奇迹出现了。《论坛报》晚间版刊发了唐·奥博多佛的报道,标题为“哈特菲尔德当选副总统候选”。
狡猾的迪克终于被抓了现行。怀特抢了2000份论坛报,要一小队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志愿者私下塞给每位代表,扭转他们的看法:尼克松背叛了他们,他选了个鸽派当副总统。
会议开始。唱“人人之上”歌,与会人员起立鼓掌。没完没了的提名演讲、“演示”和每个提名的许多附议演讲,大部分都是仪式性的,立即被荣誉人撤销。
唐在表决前几小时就想知道会议情况。登特认识此人,便生出了一个反击里根的好主意。他把唐逼到了乔治亚和路易斯安那代表团汇合处。尽管一片嘈杂中唐听不真切,他还是说了些赌300块的事情。唐觉得他在开玩笑,就离开了。登特拿起扩音器,宣称唐拒绝拿钱冒险,不肯赌哈特菲尔德会当选副总统。
消息散播出去:唐只是另一个东部媒体记者,习惯耸人听闻,他的话不能当真。于是,对抗尼克松最后的火焰也被扑熄了。
1点19分,点名开始。拥挤的套间中,尼克松与其他人坐得很远。
第一轮,他得了692票,以过半数26票的平平成绩获选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党内基本无人支持,他就这样被送上了大选的赛场。每个人都和迪克·尼克松过不去。
洛克菲勒得了277票,平均每票花了28881美元。
里根的拖车里,怀特的十五岁女儿伤心不已。父亲无法宽慰她,但里根可以。他搂着哭泣的少女,轻柔地说:“卡洛儿,上帝知道他的安排。这次的舞台不是我们的。”
尼克松用了新方法挑选拍档:他模拟投票,测试得票人数,没得到满意的人选。所以他只剩自己的判断了。他已心中有谱,但不好直接公布出来。
他在周四清晨召开了第一次“协商”会议。出席成员全部来自内部团队,比如霍尔德曼、莫瑞·斯坦斯和帕特·布坎南。他们说了自己倾向的人选,没提到尼克松想要的名字,所以他就自己说了:“阿格钮怎么样?”
没人想到过这个人。没人熟悉他。尼克松谈到了他优秀的提名演说,其他人都不大记得了。尼克松召集了来自关键几州的第二群人,其中比利·格雷厄姆牧师出席,自由派全部缺席。他要他们提议人选,但想要的名字依然不在其中,所以:
“阿格钮怎么样?”
尼克松于下午1点抵达希尔顿舞厅,与等待的记者会面。记者们抽烟、等待、抽烟、玩了两小时的猜副总统游戏,没人猜到那个名字。当尼克松公布时,下面全是迷惑神情。
尼克松总是一见钟情。他认识阿格钮没多久,但感觉很亲近。他们有共同的根:都是杂货店的孩子,父亲管教严格,都靠打工一路读上来,都是二战的下级军官——奋斗者、勤学者、满怀怨恨的局外人。阿格钮是希腊移民的儿子,上法律夜校。“斯皮罗总是干净利落。”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说,“他从不吵闹……喜欢读书。”而尼克松是学校唯一戴领带的孩子,常偷偷溜走,一个人坐在被父亲改成杂货店的教堂钟楼里。
两人最终见面时,都经历了共同的创伤——洛克菲勒的羞辱。1967年,作为新任州长的阿格钮以洛克菲勒为模型塑造自身:制裁水污染、撤销死刑、取消全国最后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会、通过混居住房法规和心理健康、饮酒和公路相关的大项目。自然,要在洛克菲勒的总统检阅队伍中好好定位。
然后就是3月21日,他叫了安纳波利斯国会的全部新闻人来看洛克菲勒的电视参选宣言,却被洛克菲勒的一句“明确不会参选美国总统”羞辱得无地自容。
约翰·米切尔抓住了机会,邀请阿格钮来纽约会见尼克松。他们一见如故。他们有同样的愤恨,也有同样的对手。“正直人社”扩员了。
阿格钮在文化形态上有保守之处。他最重大的斗争是反弹球机运动,他对混居住房的提倡是最局限的一类。
他相信反对者从来都是得寸进尺,国家充斥着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再不后退一寸了。第一次处理学生暴动时,他在陶森州立大学表现得冷静而镇定。第二次是在布伊州的一所黑人大学,学生坐在校舍中,抗议校舍年久失修。他公布了三小时的最后期限,要求“不择手段将学生移出校舍”。于是,与尼克松首次共进午餐的一周后,阿格钮作为逮捕了227名大学生的法律秩序先锋,登上了报纸头条。
无论是属于“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的信仰可以用一个词总结:秩序。他对秩序有着地道的狂热,反对任何“越界者”。他夸耀自己一尘不染的衬衫、折得整整齐齐的裤子和毫无褶皱的西服外套。他的一个郡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野营两周后,他极其渴望工作,径直回了办公室。之后,老板阿格钮命令他回家,刮完胡子才能回来。
阿格钮憎恨胡须。很多人都讨厌胡须。这解释了他州长竞选的自由派风格: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乡下人,想要得到人们尊敬。马里兰的种族主义者是全国最暴力无序的,而阿格钮反对的正是他们:“在马里兰,”他的宣传广告如同吟诵,“极端分子,长袍身影,面目模糊的幽灵……狂热分子。”他请选民想象,如果马哈尼赢了,“当他在全国人面前出洋相时,”他们将会多么窘迫。
现在,阿格钮站在迈阿密海滩的讲坛,接受副总统提名:“能站在这里,我非常意外……”
帕特·布坎南之后为1972年大会写了一份计划备忘录,建议所有的演讲都要按照尼克松1968年的提名接受演讲来:“既精确又高深,观众在合适的时机鼓掌欢呼。”每晚都在电视前收看共和党大会的人不太多,但尼克松的提名演讲至关重要,人们会看的。这时他将再次向他们保证,在尼克松领导下,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会再次安静下来。
他以“能统一自身的政党将会统一美国”开始。讲台上,瑟蒙德坐在他的旁边。
“当我们审视美国时,看到的是浓烟和火焰中的城市。”
“我们听到晚上的警报器响,看到美国人死在遥远的战场上。”
“看到美国人彼此仇恨、扭打、在自己的国家互相厮杀。”
“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些时,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在痛苦中哭喊。”
“我们走过这么多路,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