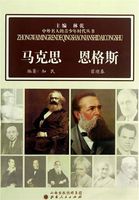很久以前的1967年2月,《时代周刊》描述了越南农历新年的魔力:
“每年灶神受玉帝召唤重返故土之时,越南人便会卸甲归家,纵情庆祝,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他们戴着龙面具起舞,燃起蜗牛壳和火药赶制的爆竹,大吃烤肉和蜜饯。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篇文章接着报道,说许多越共战士趁这四天的停战假期纷纷投诚。
今年却不同往常。美国人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了停战的一线曙光,西贡的妇女却在花篮和衣堆里藏匿了枪支、弹药、地雷和手榴弹,间谍也伪装成出租司机和面条小贩,准备反抗美国使馆。他们成功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军队以八万五千兵力占据了44个南越首府中的39个。新年攻势好似潮水,浇灭了停战的希望之光。
政府被迫在公关上大下功夫。总统公告全国,说越共的进攻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威斯特摩兰司令说“敌人即将被击溃”。约翰逊内阁首席越南意识形态顾问华尔特·罗斯托称这次进攻是“胡志明一生中最大的低级错误”。
这场战争的残酷消耗对于双方都是前所未有的。美联社的彼得·阿奈特在槟知首府目睹了数以百计的焦黑的尸体残骸。一位少校解释说:“要挽救这座城市,就必须摧毁它。”一位美联社摄影师和CBS一个摄制小组抓拍到了一个场景,一个南越高级警官正杀死一个双手反绑、平民打扮的人。《读者文摘》登载了敌人的野蛮行径。照片刊在坚定拥护越战的报纸头版上,供人们早餐时间仔细阅读。《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横跨四版,标题为:“约翰逊承诺绝不‘屈服’”。
溪山基地543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七天内遇害,政府将动用战术性核武器保卫被围困的基地。面对记者关于这些传言的质问,约翰逊承诺绝不屈服。被称作“美国最可信的人”、CBS新闻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离开办公桌,到了西贡。他播报了一篇前所未有的社论:
“越共是如何出其不意地展开了如此规模的攻势?……毕竟,城市应该是安全的……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唯一理智的抽身之道是谈判,不是作为胜利者,而是作为维护承诺并奋力捍卫民主的可敬之人。克朗凯特为您报道,晚安。”
旧历新年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60%的人认为自己是鹰派,24%属于鸽派。而这个比例现在成了41对42。总统支持率一路降到了40%以下。只有26%的人赞同他战时的作为。
罗伯特·肯尼迪于2月8日在芝加哥讲话,称:“我们的敌人残暴肆意地在南越展开袭击,最终击碎了政府的幻想……我们之前企图依靠军事力量解决争端,而这是要靠南越人民的意愿和信念才能解决的。他号召包括越共在内的和平谈话。对于压根不把越共看作合法政治实体的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记致命重拳。他右翼的老朋友全都抛弃了他。他们打电话给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称肯尼迪是叛国贼。而这对于他左翼的支持者来说只是增加了他的魅力。他暗示总统在撒谎,总结道:“只有真相才能令我们解脱”,这是否意味着他会亲身上阵竞选总统呢?
理查德·戴利市长站上了演讲席。众所周知,戴利认为战争正渐渐变成民主党的灾难。如果没提前试听肯尼迪的反战演说,他能允许他说出这种话吗?年轻记者彼得·哈米尔从伦敦寄了一封信给肯尼迪:“如果一个15岁的孩子要在莱普·布朗(以宣扬暴力闻名,曾被列入FBI十大通缉名单)和肯尼迪之间做选择,他可能会选择理智的一方……而要这孩子选择莱普·布朗或是约翰逊的话,他就只能手持左轮投身暴力了。”更年长理智的肯尼迪助选人员尽量不要他知道这类事情,救世情结对于议员工作有害无益。但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新闻秘书弗兰克·曼凯维奇偷偷把信给了肯尼迪。肯尼迪把它放在手提箱里,读了一遍又一遍,把它传给朋友看,思索着是不是越南新年改变了美国,而使得这种新政治成为未来的潮流。
有些人确实深信不疑。大学生、主妇、明星涌入新罕布什尔州,支持麦卡锡。“再不回华盛顿工作”的赌咒犹在耳边,国会山助选人员就已经收好行李,要为他工作了。这个冷漠的明尼苏达州人获得了11%的支持率,看来大事已定。“他人看起来不错。”州里的一个主妇说。她在一个购物中心碰到过他,但不大记得他的名字了。麦卡锡认为自己的魅力缺陷是一种优势。尽管新罕州2/3都是天主教徒,他也拒绝提及自己信奉天主教。这个古怪的政客从不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但这也是他的一个强大之处。普通的政治家很容易变得谨小慎微,而他不会。1952年,他在国家电视台与另一位麦卡锡议员辩论,后者正为尤金·麦卡锡这种自由党人“丢掉”了中国而愤愤不平。曾经的教授尤金毫无幽默感地做出回应,毫不畏惧地回击:“‘占有’人民,我们没这种政策。”
他讨厌参议员,把参议院叫作“地球上最后一个原始社会”。他会为一部艰涩的税法提出一个出色的修正案来帮助穷人,而后表决时却并不现身,以此讽刺那些批评他的同僚。他更关心知识分子的意见,发表诗歌公开攻击自己的同侪:“冥顽和盘尼西林/是那些老家伙超越我的资本。”然而与其他议员一样,他也坚信自己会当总统。1960年他抱怨:“我有汉弗莱两倍的自由党精神,有赛明顿两倍的智商,有肯尼迪两倍的天主教信仰——可为什么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
同年,他因发表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提名演说名动全国。演讲中,他赞扬了阿德莱败而犹荣的高贵精神。他的发言表现出自由党结构上的弊端:将荣誉看作目标本身。而1968年,对于自由党人来说,他作为勇于在越战的耻辱中接手总统一职的唯一人选,无疑魅力非凡。他们全都睁大眼睛期望着这个男人,这个认为荣誉演说无需掌声、总是提起某些名声不显的罗马皇帝的男人。
年轻人拥入新罕州为他工作。要鼓励这种热情是相当冒险的,许多中年人把反战的年轻一代全看作嬉皮士,自己臭烘烘,还想要五角大楼围着他转。麦卡锡精明的经纪人负责大学志愿者事务,他要他们剃掉大胡子,换下超短裙,按性别分区——“只要有记者报道我们在这里鬼混,我们想要的一切就全完了。”年轻人还自觉禁了酒。当地助选团邀请记者参加他们的宴会。华盛顿记者被宴会的场景震惊了,这一邀约成了竞选的关键一招。看到年轻人整洁得体,《华盛顿邮报》记者玛丽·麦格瑞撰文表达了赞许之情:“显然,他在填补代沟与教化反对者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月23日,北朝鲜捕获了美国一艘名为普韦布洛号的间谍船只,而总统对此无能为力。接着,1月30日,即越南农历2月13日,美国民主行动委员会以65对47的投票支持麦卡锡。在沃尔特·克朗凯特爆炸性的播报中,总统面色憔悴,深怕自己会像威尔逊在第二任任期里一样,再发场心脏病或中风。他说:“我已经失掉了美国中层阶级的支持。”沃尔特·李普曼撰文称总统的再选“只会加剧而不是遏制党内的分裂”,而且罗伯特·肯尼迪不应该等到1972年,那时民主党早因“另一个毫无信任、分帮结派和互相辩诘的四年”毁了。
白宫竭尽全力为总统挽回新罕州的颜面。他曾在总统选举上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如今却不顾一切放下自由世界领袖的职责,跑去曼彻斯特办公室秘书那里登记做候选人。接着,他发动新罕州的民主党州长和议员仓促地组织一场“约翰逊式的竞选”来保住麦卡锡预期的11%的得票。
州长金的预言高得离奇:麦卡锡会赢得40%的选票的。麦金太尔议员把麦卡锡叫作“逃兵役的和逃兵”的候选人。在美国向胡志明市的寺庙里投掷炸弹展开报复时,肯尼迪传奇的讲稿撰写人理查德·古德温表明自己是麦卡锡的志愿者。他告诉麦卡锡的新闻秘书、年轻的芝加哥人西摩·赫什:“我们就凭这两台打字机来推翻政府。”
他并没有确切地说“我们要选麦卡锡”。
约翰逊的支持者对这种局势漠不关心,甚至有些敌视。有人认为肯尼迪诬陷麦卡锡是“掩护候选人”——即一个强势对手在阵前拖住对手,而最有希望获胜的则在后方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成熟。肯尼迪反复声称自己不会“在任何欺骗性情况下”竞选,但他也雇了一个记者,拟了个首要入选条件,公开诋毁麦卡锡,同时进一步攻击总统。继总统拿“连德州博蒙特也有盗窃发生”的说法回应了西贡政府的腐败问题后,3月7日,肯尼迪在参议院说:“就算博蒙特有盗窃,美国孩子也不会因此而死。”
肯尼迪阴魂不散,拖着麦卡锡竞选。麦卡锡精明的经纪人对此持积极态度。他们贴了一张海报,并排印着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肖像,写着“1963年之后,美国怎么了?”还有一张,印着麦克阿瑟将军抽烟斗的样子:“任何在亚洲大陆上宣称美国占领权的人都该去查查脑袋是否出了问题。”它们采用软宣传策略,而并不直接为麦卡锡说话。
最后一周周末,来了4500位志愿者,差不多是投票人数的1/10。他们被简单地告知:“不要与任何人争辩。”“只提醒人们,越战造成了通胀。”据《纽约时报》报道,威斯特摩兰还需要206000名士兵。在初选的周二,下雪了。而约翰逊和越共都知道,变化多端的天气总是站在反叛者那边。
游击队员满怀希望地聚集在曼彻斯特的谢拉顿·韦伐若旅馆,等待返乡。据通报,支持数字由30%,40%到了45%。欢呼的声势是任何政治记者都前所未闻的。麦卡锡的票选达到了42.4%。约翰逊试图表现出不以为然,称:“把20%叫作压倒性胜利,40%就能获得选民授权,60%就算一致通过的,也就新罕州这一个地方了。”麦卡锡联合竞选的经纪人提醒记者小心被骗:“历史上第一次,大部分国民都相信自己被政府给骗了。”
这至少提供了一种解释。此后,两位民意测验专家理查德·斯卡蒙和本杰明·瓦滕伯格对数据做了深入调查,发现麦卡锡得票中,60%的人投给他是因为约翰逊在越战上的进展不够快,而并非因为麦氏多“富有自由精神”。斯卡蒙和瓦滕伯格在两年后出版的一本书《真正的大多数》中令人信服地提出,他们投给麦卡锡是因为已经“受够了”。他们认为麦卡锡能改变现状,而现状是:全国的人都气得发疯。
理查德·尼克松通常更了解深层动态。他在新罕州赢得了79%的选票获胜,但边喝茶边看报的人们没怎么留心。他依然是他们最喜欢的笑料。
人们第二喜欢的笑料现在是罗姆尼了。不在威斯康星挤奶时,他就不停地往新罕布什尔跑,好像丝毫不知道自己败北的事情。他似乎觉得只要握遍全州人的手,就不会失败了。这徒劳的举动在一次玩鸭柱保龄球时暴露无遗。他第一次扔出了9分。整理球具前,他不停地扔,又扔了34次。
尼克松没有这些多余的动作。他在最后一刻宣布自己竞选总统,在2月2日抵达新罕州。同日,完全秘密准备的、宣布他参选的150000封信件寄达了新罕州85%的家庭。当晚午夜,他抵达波士顿,未加通知就住进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睡了个好觉,准备他在曼彻斯特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时间定在下午,而通常选举发布会都是清晨很早就开始的。他表明了自己反洛克菲勒和罗姆尼的立场,宣称只有“初选的决定性胜利者将会、也理应获得提名。”他在康科德做了开场演说,还进行了中场休息。1960年时,他几乎把自己逼死,而今年,他要避开这些错误。
500名新罕州共和党人做了长时间的录音面谈,在纽约的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录音文本。结果令人沮丧。
“他是个失败者。”
“坦率地说,我觉得他把握不住这个机会。”
“别骗自己了,退出吧。”
加门特在沙子中淘到了金。“他证明了自己能行。”录音中有个人说,“之前他是被打败过,可他会回来的。”加门特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两道线:“就是它!”他们能就此做些文章。尼克松——像丘吉尔、林肯一样,是个会卷土重来的男人。
2月2日,150000新罕州居民读到了这则消息:“在华盛顿的14年里,我学到了作为一个总统,面对重大抉择时应如何从容应对……过去的八年,我有机会实践自己所学的东西……我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些答案。”他的竞选海报宣告:“握手解决不了问题。要认真思考——毕生思考,时刻准备。”
他在康科德的演说充斥了闪光的理想主义:美国正经受“精神危机”,总统丧失了“民族之魂”。国家需要一位领袖,能够“托起疾驰的梦想”。随后是一场很不尼克松式的宴会——一个免费吧台,面对所有记者开放。他四处走动,大咧咧地拍背,讲着笑话,倚在椅子上随便地聊上几句。他许诺这次竞选将会是他进行过最开放的一次。记者被吸引了,围在吧台边即兴编了首小诗:新尼克松——“你所见过最新的。”
尼克松次日早晨第一件事,是在被记者和狂热选民发现前偷偷溜走。实际上,这是他进行过最隐秘的一次竞选。
这次竞选的创意出现在去年秋天的“道格拉斯下午访谈秀”。尼克松坐在道格拉斯节目的化妆椅上,随意地与一位年轻的制作人谈起,利用参加访谈秀这种伎俩来获得68年大选胜利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这位名叫罗杰·艾尔斯的26岁制作人并未如他所想发出笑声以示尊敬,相反,他对尼克松展开了说教:如果还认为访谈秀是一种伎俩,就别想当美国总统了。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回溯了尼克松1960年选举时一次摄像机前的失误,那时他还在念中学。然后,不知怎么地,他到了纽约,受邀为媒体团队负责人弗兰克·莎士比亚工作。莎士比亚是CBS一个部门经理,有传言说这个金发男孩有一天会取代总裁。他是威廉·巴克利的朋友,一心想要摧毁自由党。要不是他最终发觉自己的第一人选罗纳德·里根太经不起历练,他可能已经成功毁掉自由党了。
他年轻的追随者艾尔斯是个电视制作天才,将道格拉斯从一个费城当地佬变成了全国流行人物。每个工作日,171个城市的六百多万主妇在电视机前停下熨斗,等待着自己的偶像。要执行新尼克松的新点子,艾尔斯再合适不过了。艾尔斯、加门特、莎士比亚、雷·普莱斯、尼克松的一个年轻律师和汤姆·埃文斯在CBS的一间放映室里碰面,如同足球教练般回顾了整场比赛——尼克松7小时的电视亮相。媒体能让巡回演说家尼克松看起来像个真诚卖力的诉讼当事人。非正式场合中,他在摄像机面前表现得更好,眼睛直视着提问者。他们确定了他的这种形象作为1968全年的形象。
但他也有对头。事先毫无准备的提问——这本是新罕州竞选的一大看头,现在变得低俗起来了。他们做了创新:即兴提问环节会被事先拍好。只有他们才能掌控大局。
尼克松把全权交给了团队。“我们要围绕电视展开竞选。你们只要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