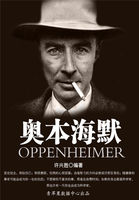1966年,这个国家为了瓦茨暴动而忧心忡忡。“警车时不时地爬上人行道,驶过废墟,小心地穿过小巷和商店的后面,它们急速地飞奔到各个地方,寻找躲藏着的年轻人。”《华盛顿邮报》引用一位被警方搜寻的年轻人的话说:“他们总是在那些老地方寻找,他们不知道,每一次和上次都是不一样的。”《时代周刊》也援引了一名洛杉矶警察的话:“外面还有更多的枪。去年夏天,他们洗劫了这个地区每一家当铺和运动商店。”
这名警察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一遍:“外面还有更多的枪。”
关于瓦茨暴动的意义,人们有着激烈的争论。好斗的黑人称这是一场“起义”。“我把燃烧弹投掷到了他们的正前窗,”一个年轻人对一个CBS记者骄傲地回忆道,“可以说我们打了个平手。”伯克利的一伙儿激进分子,自称“越南纪念日委员会”,他们给瓦茨暴动人员拨款,并发表声明说:“1965年夏天洛杉矶暴动和越南的农民起义有着相似之处。”“如果洛杉矶的暴乱暴露了联邦当局在处理种族隔离、贫困以及住房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如果这次暴乱刺激了新想法的诞生,”一位哥伦比亚的教授这样说道,“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补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但是在这场辩论中,保守派处于支配地位。他们的代言人是威廉·派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如同是参加竞选职务的候选人一样,制定出党的路线:是民权运动的过错。是这些人宣扬了“如果你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那你就不必遵守法律”。是这些人,逼迫负罪感十足的“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从而使得他们的行动得到认可。派克把他对于暴乱根源的描述呈交给了布朗州长研究瓦茨暴动的小组:“有人扔了一颗石头,就像公园里的猴子那样,所有人都开始跟着扔石头了。”他坚称,除非有正派人士采取激进的措施,否则这些“猴子”就会不断增多,直到他们自己门前的台阶上都是。因
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他在一个月之内收到了四万条祝贺短信。
在三月份的时候,几乎又爆发了另外一场骚乱。这次是由于在一些墨西哥后裔和黑人孩子之间爆发了地盘之战。超过一百名防暴警察迅速涌进了事发现场,成功地封锁了周边,媒体史无前例地报道的所谓“第二次瓦茨暴乱”在还没开始之前便已经结束了。但是这次骚乱在校园中引起的涟漪和争吵却并没这么快结束。而且这些争论很快便传到了萨克拉门托和华盛顿:国家立法委的人指责帕特·布朗州长用来治理第一次骚乱的6150万美元开支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原本计划好的关于民权运动的白宫会议现在无限期延迟。《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科茨描述了他从读者那里收到的惊恐电话:“我的妻子刚刚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死了五个人了。那些骚乱分子现在全城都是。这次我打算给自己弄一把枪了。”
一月份的时候,罗纳德·里根发表了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资格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指责了最初的瓦茨暴乱,说“在任何情况下,公众都应当坚持向政府讨要说法而不是暴动”。他现在公然批评布朗州长。《纽约时报》刚刚报道过二月中旬加利福尼亚的州长竞选,当时它曾经评论道,自从演员罗纳德·里根“通过那戏剧性的、精心演练的电视节目,宣布进入竞选角逐”以来,一直没能得到什么关注。现在它的报道说,“在星期二的暴力事件发生后,今天出现了猛烈的政治交火。”里根指责布朗明知有麻烦,还是执意离开加州;布朗则轻蔑地表示,如果他对瓦茨暴乱中的每一条消息都作出过度反应,那他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
布朗并不觉得需要为自己做什么辩解。很显然这个州不会忘记他1950年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情形。当时他是以宣扬法治的律师身份出现的。而且他作为州长,曾经亲眼见证了处决红光劫匪卡里尔·切斯曼,他看到了他的共和党前辈们——从埃莉诺·罗斯福,到比利·格雷厄姆,出于慈悲情怀而为他求情。
里根在共和党里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旧金山的前任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让这两个人自相争斗吧。他在和里根的竞争中是最主要的领先者——《纽约时报》认为,他能很容易“赶上里根的演讲技巧”。在一篇列举里根多方面的缺陷的时候这样说:他与极右主义和戈德华特选战的不良关系;有前途的年轻中立派把里根看做是一个“拥有着近乎恐怖的某些东西”的人;他所犯的是新手般的错误。“要知道,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你还需要再看多少次呢?”他在一次演讲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就是凭借那一点,《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说,里根的竞选很快便会“跌落到极点”。乔治·克里斯托弗开玩笑说,如果布朗知道什么是为他好,那他最好为里根工作。
布朗的确正在那样做。尼克松可能要参与竞选,一个年轻的助理被派去观察尼克松的出场的表现,但是却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被与会者攻击或者追问时,他便会崩溃……
“有些人并不认为总统是一个独裁者,有些人则意识到联邦应当和州之间有必要保持密切的合作,这些人是不会接受他对于约翰逊总统以及布朗州长的攻击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里根作为州长会做些什么。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和我们与华盛顿的工作关系,他什么也做不了。”
里根并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政治家。让人振奋的只有他的成就。他在1959年议会的第一个任期是加利福尼亚州史上成就最多的一个时期:为了发展经济和保护消费,他设立了许多大胆的新机构;由上至下行政机构的重组;增加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医院、精神病院和戒毒中心设立新的基金;颁发禁令,禁止在招聘的时候实行种族歧视;为学校提供了大量新的基金;新建了大量的高速路、铁路、隧道和桥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成功地筹集了17.5亿资金,并且截止到1972年,向南加州运送了1亿加仑的水。在这个州里有1650英里的免收费高速路,其中1000英里是在他主导下修建的;他下令建设大学,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足够容纳25%的高中毕业生进入世界最为优秀的公立大学深造,并且学费全免;新增了20万个工作岗位。如果他并没有新颖的方法,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办到的呢?在他的治理下,美国最大的州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了。让这个演员拥有这一切吧:中产阶级非常清楚,不会信以为真。他已经为自己建了一个梯子,以后可以借着这架梯子向上攀爬。
这一切的确都让他发展起来了。
一个被称作“加州行动联盟”的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禁止法官逃避任何有关色情的案件。他们的宣传广告中声称,色情小说家极为擅长“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对于“强奸、性变态和性病”的泛滥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他的活动家则开始攻击一本教材:一位叫做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黑人历史学家所写的《自由国度》。他们所印刷的小册子上面坚称,这本书“毁掉了美国过去的骄傲,展现出了一种负罪感,嘲弄美国的正义,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敌视宗教观念,过分强调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突出负面例子,批评经商和自由创业,玩弄权术,煽动阶级仇恨,歪曲事实,”并且“推崇不实的宣传和废话”。
在黄金州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道德恐慌的季节,并且通常情况下,加利福尼亚会引领这个国家的潮流。这个国家最高的私立学校联合组织发表一份声明,担心“学生对于性采取了一种‘可怕的’态度……因为缺少道德准则”。但是其他人将这种发展趋势看待为文化健康的表现。例如,一个研究精神病的教授也于三月份在亚利桑那州医疗协会上称赞“垮掉的一代”,说他们“使人们加速改掉一些中世纪的习俗”,尤其是在性问题上。一个《民族报》的作家声称,那些辍学来“寻找自我的孩子,可能要在许多方面比那些留校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有希望的道德模范”。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直白地预言一个真正道德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很不幸的是,他们的预言彼此之间却互相矛盾。
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不可协调的道德观便会招致暴力。
在圣迭戈,一个恐怖分子将燃烧着的油布扔进了圣迭戈民权组织驻地的窗户内。在宝马山花园,也就是里根住的地方,五十个孩子举着标语,在一所高中门前来回游行,标语上写着: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留长头发会不利于学习。在底特律,一个少年当着一千多个聚会者的面射杀了他的宠物兔,并且哭喊道:“这个集会真是扭曲,让人憎恶。这个集会虚假、伪善,简直是个笑柄。”
一个新的反战组织出现了,W.E.B.杜波伊斯。林登·约翰逊的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控制着这个组织,把它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工具。理查德·尼克松称其为“极权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取的名字会给我们的支持者和其他的优秀市民造成困惑”(因为这个组织名字的英文发音就好像是“搞男孩俱乐部”)。人们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个由他掌控的色情组织:男孩俱乐部。在圣弗朗西斯科,一个右翼的恐怖分子用莫洛托夫鸡尾酒烧毁了杜波伊斯的总部。在布鲁克林,这个组织的成员被民众暴打。
《时代周刊》在4月8号的封面上印了一行鲜红的字:“上帝死了吗?”虽然上帝没有死。但这并没能阻止四处涌来的抗议信。这些信指责“《时代周刊》的这则报道充满偏见,支持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非常让人震惊,而且很不符合美国的作风。”俄克拉荷马州的部长竭力争取发起一项运动,谴责“南方政府高层的传教士”——白宫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因为他的行动“给这项工作带来羞辱,并且有辱耶稣的圣名”。
然后便是那些像伯克利的学校。1964年的一天,一辆警车驶进校园,拆散了一个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台。这一点和大学里允许支持政治的政策相违背。警车立刻就被成百上千的学生围在了校园的主广场上。他们开始爬上车顶,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要求获得自由演讲的权利,并且要反抗非法权威和丧失心智的官僚主义的盲目作风。然后成千上万的学生占领了管理大楼。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演讲运动”是一种道德超越。对于街上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从来就没钱上大学的人来说,这纯粹是因为那些大学生被宠坏了。紧接着就是“肮脏演讲运动”。这次的运动开始于几个愤怒的小孩子,他们坐在学生会的台阶上,布告上涂满了脏话。几十个孩子集会支持这项行动。
那些愤怒的人全都感到这一切是互相关联的:肮脏,犯罪,“孩子”,对于公认的宗教信仰的咒骂。这一切都和“自由主义”有着些许的联系。帕特·布朗是个“自由派”。结果自由派的敌人,罗纳德·里根的表现也不算太差劲。他给那些所有的政治愤怒提供了出口,这些愤怒在他出现之前完全都算不上是政治问题。
美联社的比尔·博亚尔斯基顺便采访了里根走过诺沃克的郊外的场景。那里是蓝领工人的聚集地。“政治新闻记者通常都认为,那个地方的人群的反应几乎就是当地公众观点的科学数据。”人们这次显得十分谄媚。在伍德雷克购物中心,里根脸上洋溢着谦逊的笑容,他开始发表他关于福利的高成本的看法。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他们发狂了。诺沃克地区四分之三的人是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即使是理查德·里根也感到有一点点吃惊。帕特·布朗因为受到了来自共和党保守派萨姆·约蒂提名者的突然挑战,而被迫参与初选。一个月之后,他也来到了诺沃克。同样的人群却激烈地质问他,声音大得高过了话筒。
马丁·路德·金当时在芝加哥。1956年,埃莉诺·罗斯福说,如果芝加哥能够率先解除种族隔离,这将为南方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戴利市长回应说,芝加哥并不存在种族隔离。1956年,迪克·格雷戈里率领的反种族隔离游行安静地经过戴利在布里奇波特的房子,临近学校的女生在跳橡皮筋的时候哼唱的歌曲是:“我想成为亚拉巴马的骑兵/我真的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因为要是能成为亚拉巴马的骑兵/我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杀死黑鬼。”但戴利市长在公开场合仍然声称芝加哥没有种族隔离。
马丁·路德·金曾经相信,这些贫苦的北方黑人们也会因为“南方黑人的斗争而获得好处”。然而他不断地看到芝加哥划出“黑人隔离区域”。在一月份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家人在罗登附近租了一套有四间房的无电梯公寓。在他们搬进去的那一天,记者们涌进来报道。他们注意到了周围散发着尿臭味,整个厅堂只有一盏灯,以及还有传言称这个街区被黑势力控制着。这是马丁·路德·金在数月之内最后一个公共关系的胜利。
戴利市长比那些南方的乡下佬郡长都要难对付,他总是能打败外地的自由派——就像前一年,约翰逊总统的教育行政长官宣布他将从有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里撤走联邦的教育资金。戴利市长给总统打了个电话,这位行政长官立刻被撤职了。
到了三月下旬,马丁·路德·金的运动看起来已经处于下风,在这一次的面对面中,他似乎已经要一无所获地撤退了。但是他正在改变他的计划,他发起了一次国会辩论。约翰逊总统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介绍了他所提议的《1966年民权法案》。这个法案的中心措施,民权法案第四款,旨在让住房歧视非法化,不过才刚刚提出便已经宣告死亡了。毕竟,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市议会通过了一项黑人与白人混居的法律,即使是在自由派占优势的伯克利,市民们也会利用一切可用的民主手段,去破坏这项法令。而这还是在瓦茨暴乱发生之前。
在委员会听证会上,保守派的反对党引用自由派最高法庭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1963年判决时候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个原则是我们法学系统的基础。”由83000人组成的全国房地产联合会组成了一个游说团,来到华盛顿,想证明“民权法案第四款”有着内在的“邪恶性”,它的通过会“鸣响私有财产所有制的丧钟”。它不合宪法,霸占市场,这种做法会导致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财产——他们的家产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