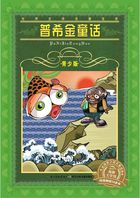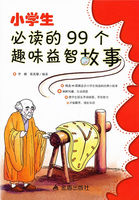“我们赞赏古希腊的悲剧;不过仔细考察一下,我们更应该称赞能够产生它们的时代和民族,而不是称赞某些个诗人。要知道,尽管这些剧作之间可能有一点差别,尽管这些剧作家中的某一个可能显得比另一个伟大一点,成熟一点,但它们统统都只有唯一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它们都一样地大气、雄伟、健康,都表现了完美的人性、卓越的生活智慧、高尚的思维方式和纯粹而有力的人生观,以及诸如此类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品质,不仅显现在由我们承继下来的希腊悲剧中,也存在于他们的诗歌和叙事作品里;除此以外,在古希腊的哲学家、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在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造型艺术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些品质。如此一来,就不能不相信,这些品质不仅为某些个别的人所拥有,而是属于整个的民族和整个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蔚为风尚。
“你再看彭斯。他之所以伟大全由于:他先辈们的古老歌谣仍然活在民众口中,他还在摇篮里就听见吟唱这些歌谣,他是在这歌声的熏陶下长大,并把这些典范的精髓融进自己的血肉,他由此而获得了一个可以踩着继续前行的鲜活基础。再说,他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自己写的诗歌在民众中立刻找到了知音,他很快便听见田野里割麦子的农夫和捆麦秸的农妇与自己应和,还有一跨进小酒馆,快活的伙计们也唱起他的歌迎接他。在这样的气氛下,自然会有所成就!
“相反,我们德国人的情况是何等可悲啊!—— 我们的古老歌谣同样出色,可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有哪些还活在民众中呢?赫尔德及其后继者不得不从头开始收集它们,以免它们被遗忘;随后它们被印了出来,让人至少在图书馆里还能找着。再往后,比尔格尔和弗斯写出了多么棒的歌啊!谁能说,他们一定比杰出的彭斯逊色,他们的作品一定不如彭斯的富有民歌风呢?然而其中流传的有多少,由流传而得到民众应和的有多少?—— 它们被写出来了,印出来了,藏在了图书馆里,这就是德国诗人通常都有的命运。—— 我自己的诗中又到底有多少活着呢?不错,也有这首那首不时地让一位漂亮姑娘站在钢琴旁边唱一唱,但在广大民众中却无声无息。回想起旅行意大利期间聆听威尼斯船夫唱我《托夸托·塔索》中的片断,我真是说不出有多感慨!
“咱们德国人还生活在昨天。尽管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努力提高文明程度;但是还可能要过去几个世纪,我们的同胞才会有足够的修养和较高的文化,才会实现修养和文化的普及,以至于广大民众都能像希腊人似的崇拜美,都会为一首动人的诗歌欢欣鼓舞,到那时人家才会讲我们:他们早已经不是野蛮人。”
1827年5月6日,星期天
(《威廉·退尔》成书缘起;歌德重申自己做诗不从观念出发)
再次在歌德家聚餐,出席的仍为前天晚上的那些客人。谈话多与《海伦》和《托夸托·塔索》有关。随后歌德告诉我们,他在1797年曾计划将《威廉·退尔》的传说写成一篇六音步的叙事长诗。
“在那一年,”歌德说,“我又去那几个小州和四林湖游历了一次,那儿美丽迷人、气势雄浑的自然风光再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受到诱惑,动了要把那变化无穷、无与伦比的美丽景致写进一首诗里的念头。而为了写得更生动、有趣和吸引读者,我觉得最好能给这极不平凡的场景和土地配上一些同样非凡的人物,于是想到了威廉·退尔的故事,感觉它再合适不过啦。
“退尔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位魁梧有力的壮士,一个自得自满、懵懂淳朴的汉子,他作为搬运工往来于各州之间,到哪儿都有认识的人,都受到人们喜爱,与此同时也乐于助人,一直不声不响地干自己的营生,只知道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从不关心谁当主子,谁做奴隶。
“作为对立面,盖斯勒在我想象中虽说是个暴君,但却属于较随和的那一类,有时一高兴做点好事,有时一高兴又做点坏事,平常对老百姓及其福利和疾苦漠不关心,好像他们压根儿不存在似的。
“然而人性中更高尚和更美好的表现,诸如对故土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和在国家法律保护下获得的安全感,以及身受异族奴役和虐待所感到的耻辱,最后还有终于奋起摆脱异族统治的意志和决心,所有这些高尚而优秀的品质,我都打算赋予那几位高贵的男子,即著名的沃尔特·富斯特、施陶法赫、梅尔西塔尔等等,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英雄,才是我心目中行动自觉的崇高力量,相反退尔和盖斯勒尽管也不时地出现在台上,整个而言却主要是被动的人物。
“我已满脑袋充塞着这美妙的题材,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出为它写的六步体诗句。我常看见清朗月夜里的静谧湖面,高山深谷中的月华雾霭。我常看见旭日照耀下的满湖波光粼粼,常听见树林中和草地上生命的欢呼雀跃。然后我想象有一场暴风雨,一场生成于峡谷然后向湖上袭来的风雨雷电。当然也少不了悄无声息的夜晚,以及为参加秘密集会而行经道道危桥、条条小径。
“我把这一切都对席勒讲了,在席勒心里,我的这些风景和我的这些人物便汇成了一部戏剧。由于我自己有其他事情,写作叙事长诗的计划一推再推,最后便把我这个题材完全让给了席勒,他呢跟着便完成了那部很值得赞赏的戏。”
大伙儿很有兴趣地听着,都为从歌德口里知道了内情而感到高兴。
…… ……
谈话转到了《托夸托·塔索》,有谁问歌德想在剧中表现的是什么观念。
“观念?”歌德应道 ——“我可不知什么观念!我了解塔索的生平,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把这两个很独特的人物及其品性糅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剧中的塔索形象,我还给了他一个平庸的对立面安东尼奥,对于后者我同样也不缺少原型。除此而外,菲拉拉宫廷中的礼仪应酬和谈情说爱,跟魏玛这儿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有理由讲我的这部剧作:它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顺便说说,德国人啊真是些怪人!—— 他们到处寻找深刻的思想和观念,给什么都塞进深刻的思想和观念,因而把生活搞得难上加难。—— 唉,你们终于该鼓起一点勇气啦,要大胆相信自己的直觉,想快乐就快乐,该感动就感动,让自己受到振奋甚至获得教益,让自己胸中燃起熊熊火焰,勇敢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只是别老想如果不存在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这一切都是空的。
“你来问我,我想要在《浮士德》中体现什么观念。好像我自己对此真的心中有数,并且讲得出来似的!—— 从天庭到尘世再到地狱,这必定意味着什么;然而却并非任何的观念,而是剧情的发展过程。再说,魔鬼赌打输了,一个努力摆脱迷雾、永远自强不息的人有望得救,这固然也是一个切合实际、能给大家某些启迪的好想法,但却不是一个可以成为全剧特别是每一场的基础的什么观念。我在《浮士德》中表现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光怪陆离,要是我真能用唯一一根贯穿始终的细线把它们串在一起,那确实一定会成为一个绝妙的玩意儿!
“总而言之,”歌德继续说,“我作为诗人的特点,不是力求去体现什么抽象的东西。我只是在内心中吸取印象,而且感性的、鲜活的、可喜的、形形色色的、多姿多彩的印象,一如我活跃的想象力所能提供的一切一切;我作为诗人要做的仅仅是,在心里对这些观感和印象进行艺术的整理加工,然后再生动地将其表现出来,以使其他人在听到或读到时也获得完全一样的观感和印象。
“即或我作为诗人有时也想表现某个观念,那我所写的也只是一些小诗,一些内容极为单一和一目了然的作品,例如《动物的变形论》《植物的变形论》和《遗嘱》等等。至于篇幅较大的作品,我有意识按一个贯穿始终的观念写成的大概仅有一部,那就是我的《亲和力》。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因此好理解把握一点;不过我并不想讲,它也因此更成功一些。我的想法倒是:一部作品越是难理解把握、曲高和寡,才越成其为杰作。”
1827年6月20日,星期三
(拜伦的《该隐》;泽尔特的建筑和音乐才能)
已经摆好供五个人用餐的餐桌,凉爽的房间里却空无一人,在炎热的夏天让我感觉很舒服。我走进餐厅旁边那间铺着地毯,立着一尊巨型朱诺胸像的屋子。我在屋里独自踱了一会儿步,歌德就从他的工作室里走了过来。他亲切热情地招呼我,对我表示欢迎。他坐到窗户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对我说:
“请你也去搬把椅子来,咱们坐在一起说会儿话,等着其他人到来。我很高兴,你到底还是在我家认识了施特恩贝格伯爵;他又走了,我呢又恢复了习以为常的活动和平静。”
“在我看来伯爵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我说,“学识同样也非常渊博;不管我谈哪方面的问题,他都总是在行,谈什么都透彻周到,轻松自如。”
“是的,”歌德应道,“他是非常了不起,在德国交游广泛,影响巨大。作为植物学家,他以自己的《史前时代的植物》这部著作享誉全欧;同时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矿物学家。你了解他的生平吗?”
“不了解,”我回答,“可我很乐意知道他一些情况。在我眼里他既是位伯爵和社交名人,又是知识渊博、有多方面建树的学者:如何能身兼二者在我是个问题,很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随后歌德就告诉我,伯爵年少时怎么给送去当修道士,在罗马开始了修行,可后来奥地利赢回了某些特权,他便也去了那不勒斯。歌德就这么往下讲,讲得生动有趣而又重点突出,不啻一部人生传奇,完全可以媲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而要在这里复述出来,我则感觉无此能耐。聆听着歌德,一种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心里充满了对他由衷的感激。话题转到波西米亚地区的学校教育及其突出的优点,特别强调了它们十分重视审美教育。
小歌德夫妇和乌尔莉克小姐也进来了,我们于是坐到餐桌边。谈话变得热烈而富于变化起来,不过活跃在北德某几座城市的虔信派教徒,总是一个反复提起的话题。谈到这些小教派如何造成了一个个家庭的不和和分裂。我讲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我曾经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因为没能使我相信他的教义,就几乎跟我绝了交。我讲:
“这人深信不疑,人在世上的所有善行、贡献、功业都毫无意义,唯有基督的恩典,能帮助人赢得神的眷顾。”
“有位女友也对我灌输过类似的思想,”小歌德夫人接过话头,“可我总不明白,这所谓善行,所谓恩典,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所有这些东西,”歌德说,“所有这些畅行当今之世,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说教,纯粹是个大杂烩;而你们呢,也许谁都不知道它的来历。我告诉你们吧。关于所谓善行的说教,就是要人通过行善积德,施舍捐赠,把遗产留给教会等等,达到赎补罪孽进而获得上帝恩典的目的;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可路德派的新教徒呢,出于反对派的立场则唾弃这一说教,而代之以宣扬人必须全心全意地认识基督的功绩并分享他的恩典,如此一来自然也就会行善了。事情就这样清清楚楚;可今日之下全都混为一谈,张冠李戴,谁也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没有说出来,而只暗自想道,自古以来宗教观念的分歧就离间了人类,使其相互变成仇敌,是的,甚至人类的第一次杀戮,就是由敬神方式的偏差引起的。我讲,近几天我读了拜伦的《该隐》,特别欣赏这戏的第三幕和这一幕对主人公杀死弟弟的动机的交代。
“可不是吗,”歌德说,“交代得太棒啦!实在是美丽动人,举世无双!”
我接过话头:“《该隐》一开始在英国却遭到了禁演,可现在呢又人人都在读它;尤其是年轻的英国人,他们外出旅游通常都带着《拜伦全集》。”
“这也挺愚蠢,”歌德说,“因为归根到底,《该隐》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新意,有的不过就是英国的主教们本身宣讲的那些东西。”
用人通报缪勒首相驾到。他跨进屋来,坐在我们桌旁。随后歌德的孙子沃尔特和沃尔夫冈也先后蹦蹦跳跳地进来了。沃尔夫冈缠着缪勒首相。歌德道:
“去把你的留言簿拿给首相先生看,请他看你的公主,看施特恩贝格伯爵为你题的词。”
沃尔夫冈跑上楼去,很快取来留言簿。首相细细看了附有歌德题诗的公主肖像。他继续往后翻阅,发现了泽尔特的题词并大声念了出来:要学习听从!歌德听了笑道:
“在整个留言簿里,这可是唯一一句理性的题词。是啊,泽尔特总是那么了不起,那么不同凡响!眼下我正和里默尔一起整理他的信函,发现里边有不少宝藏。特别是他在旅途中写给我的那些信,更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因为他作为杰出的建筑师和音乐家,优越之处就在于从来不会失去对那些重要事物的正确判断。一当他来到一座城市,站在一些建筑面前,这些建筑仿佛自己就会告诉他,它们身上的价值在哪里,缺点又在哪里。城里的音乐协会也马上邀请他去到他们中间,在大师面前袒露出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如果有速记员把他跟自己这些音乐门徒的谈话笔录下来,那我们就又有了一篇独一无二的文字。要知道在这些领域中泽尔特是天才而又伟大,说出话来常常一语中的。”
1827年7月5日,星期天
(拜伦的天才和癖好;《海伦》的结尾和艺术虚构)
今天傍晚在公园里遇见歌德,他刚乘车兜风回来。车从我身旁驶过时他招手示意,要我上他家里去。我于是立刻转身走向他的府第,在门前看见了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歌德下了马车,我们跟随他登上楼梯,到所谓的朱诺厅里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我们刚谈一会儿,缪勒首相也来了,立刻参加我们的谈话。话题围绕着一些政治问题:惠灵顿公爵出使圣彼得堡及其可能的结果,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希腊迟迟未能获得解放,把土耳其人限制在君士坦丁堡,等等。还谈到了早先拿破仑统治下的年代,特别是关于昂贤公爵和他冒冒失失的革命行动,更谈得很多很多。
随后转到了一些较为平和的话题,特别是维兰特在欧斯曼施德特的墓地怎么也谈不厌。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讲,他正着手给墓地围上一圈铁栅栏。他当着我们的面在一张纸上绘出草图,帮助我们对他的设计意图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缪勒首相和库德莱总监告辞了,歌德请我跟他再待一会儿。
“由于我的生活跨了世纪,”他说,“每当想起纪念碑和塑像什么的就难免产生奇怪的感觉。想到一根纪念某位杰出人物的铸铁像柱,就难免心中不出现它被未来的军人推倒和砸碎的联想。库德莱替维兰特墓建造的铁栅栏,它们在我脑海里已变成未来骑兵们马蹄下闪亮的马蹄铁。我呢,还可以讲,类似的情形我已经在法兰克福经历过一次。再说,维拉特的墓地也离伊尔姆河太近啦;河水流经时转了一个急弯,如此下去恐怕要不了一百年,就冲到了死者的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