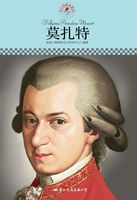她和建军在大街小巷转了一阵,确信无人尾随,才把车子一直开到花园饭店的大门口。父亲正在这饭店的露天茶座里等她。她从父亲平静的眼神里,看得出他已经和香港方面接上了头,而且顺利。她坐在父亲身边,要了饮料,建军则远远地坐在茶座的另一端。
父亲问:"你和肖童今天都干什么了?"
她回答:"没干什么,我们一起在宾馆里呆着。"
父亲说:"你待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明天早上再回去。今天晚上你跟着我,我们另外找地方住。"
欧阳兰兰怔怔地想,肖童果然不幸言中。她问:"为什么要另找地方住?"
父亲打开皮包,递过一个信封,说:"香港方面按照我的要求,都安排好了,我们明天一早乘头班火车到福州去,然后从那儿直接飞汤加,那种小国,护照好办。
护照和票你都收好,万一我和建军出了意外,你就拿上这个护照和机票,按这个路线自己走,在汤加会有人接你。"
欧阳兰兰接了那个信封,既兴奋又疑惑,她问:"您不是还要帮石厂长往香港出一批货吗,您不管了吗?"
父亲疲惫地说:"我都联系好了,老黄和姓石的已经从新田出发了,明天早晨香港方面在海上接货。如果姓石的没出问题,那就是老黄命大,他会跟着货一起过去。以后也会到汤加来找我们。要是姓石的出了问题,那老黄……唉,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欧阳兰兰心里隐隐有点难过,尽管她并不喜欢老黄,但父亲的语气仍使她心里掠过一丝物是人非的悲凉。想想自己,又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她不由感叹一声:"还是香港人利索,护照机票,一下子全替咱们办妥了。他们还真给您办事。"
父亲冷笑:"他们不敢不给我办,我要出了事,他们也不安全。他们的情况老黄、建军不了解,我可是全都门儿清,他们不能不担心我这张嘴到时候会跟公安说什么。再说,我对大陆的这种买卖太熟了,他们以后还用得着我。将来把大陆这条线再做起来不是没可能的事。"
欧阳兰兰也笑笑,打开信封,一样一样查看着里面的东西:护照,从广州到福州的火车票,从福州到汤加的飞机票。还有钱,一小叠又新又脆的美元。护照用的是假名字,上面既有入境的印鉴又有出境的印鉴,还有一些在其他国家出入境的记录,伪造得足以乱真。她——鉴赏,似乎觉得还缺了什么,凝神想想,忽然猛醒,豁然变色。
"哎,怎么没有肖童的护照,他怎么走?""兰兰,"父亲板着脸,"你别再糊涂了,咱们只有这一条路了,活得成活不成在此一举,为了咱们的安全,现在只能甩了他。"
"不行。"欧阳兰兰的心一下子乱了。"我不能甩了他,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她拉住父亲的手,"爸爸,我求你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你!"
父亲的态度缓和了一些,说:"兰兰,跟我们一起走是绝对不可能了,就是现在我同意了,护照也来不及办,机票也来不及搞。如果这次我们能出去了,以后可以再想办法把他也办出去。那时候就简单了。"
"不行,爸!"欧阳兰兰急得眼泪几乎掉下来:"咱们一走他到哪儿去?让公安抓住还不得枪毙了,我以后到哪儿找他去?"
"兰兰!"父亲突然目露凶光,"是我重要还是他重要!"
欧阳兰兰红了眼圈也红了脸,她几乎叫喊起来:"这关系到我今后生活的大事,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她说完跑出了茶座,跑到了花园里。她以为父亲会跟过来劝她,但父亲没有。
他阴沉地喝完杯里残剩的咖啡。把桌上的信封收在皮箱里,然后结了账,向建军使了个眼色,建军出去了。父亲这才走进花园,走近她身边,用令人不敢相信的冷漠的口气,在她身后说道:"那你就找他去吧,我和建军自己走。就算我,算我没你这个女儿!告诉你,我现在怀疑给公安局的那个电话就是他打的。不怕死你就找他去吧!我,还有建军,我们不会跟你去垫背!你……好自为之吧。"
父亲拎着皮箱走了。他的话故意说得冷静,但那声音几乎哆嗦得失了调子,这是欧阳兰兰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对她如此冷酷无情。他的面孔和声音陌生得让人不寒而栗,一下子打垮了她的任性和激动,让她心寒让她恐惧让她只能唯唯诺诺。
是的,父亲说得明白,现在就是想把肖童带走也没辙了,因为护照和机票都没有他的。她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她只能扑在栏杆上无声地痛哭。
建军已经在饭店的门口叫好了一部出租车,父亲上了车,坐着,没有急着开,他们等着她从饭店的大门里丧魂落魄地跟出来,低眉垂首地蹒跚着上了车子。
出租车离开了花园饭店,绕了几条街,把他们带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东方宾馆。
他们从新田开来的那辆子弹头面包车,就扔在了花园饭店的停车场上。
在东方宾馆开了房间,父亲亲自督着她给白天鹅宾馆的肖童打了电话。电话拨通了,她问肖童在干什么,肖童说没事在看电视,在等你。她想哭但忍住了。她按照父亲替她编好的说法骗他,她说,我在我爸的一个朋友家呢。他们要玩儿麻将三缺一,你就先睡吧,我明天一早就回去。肖童问,你那边有没有电话,有事的话我好找你。她看着父亲的眼色,支支吾吾地说,电话呀,人家家里的电话不想告诉别人,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回去,你先睡吧。再见,晚安,我爱你!
挂了电话,她又想哭,眼泪在眼窝里转着圈,没出来。她想,和肖童的这一场爱,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时至此刻她不能不承认,肖童至今也没有真正地爱上她。
但是,她的追求。努力,和计划,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她得到了什么?难道只有一个孩子吗?如果没有了肖童,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又算是什么!
这个晚上父亲就住在了她的屋里看着她。他们几乎都是一夜未眠。早上早早地,父亲就把她叫起来,他和建军寸步不离地带她下了楼。建军在服务台结账,父亲和她坐在大堂的沙发里等。建军不知是因为什么账目搞不清,跑过来对父亲说,可能上一个房客还留了一笔账没结,让父亲过去核对一下自己的消费。父亲去了,皮包和手机都放在茶几上。欧阳兰兰左顾右盼见父亲没有注意,便拿起手机,快速地拨了白天鹅宾馆的电话,她知道这是和肖童最后告别的机会。
电话打通了,接到了肖童的房间,她一听到肖童的声音就止不住想流泪,肖童在电话里问:"兰兰吗,你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她哆嗦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肖童……,再见了,你千万,保护自己,实在不行你可以再回西藏去,你找钟老板让他再把你藏一阵。我会回来找你的……"
肖童在电话里沉默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你告诉我,兰兰,你在哪儿?"
"我,我在,在火车站附近。我要走了,我会来找你的,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就这样吧。"
她不等肖童回答就挂掉电话,因为这时她看见父亲和建军已经结完了账,已向这边走来。她把电话在原位放好,料想父亲没有发现。
父亲走近了,毫无察觉地拿起皮包,收好电话。他的神情已明显轻松下来,对着女儿笑了一笑,说:"走,我们去吃个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