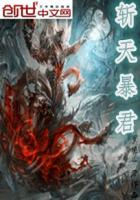不难看出,借宗教情绪挽救邪恶的现实,达到使社会人人自由平等的目的,建立良好的道德王国,是卢梭推崇宗教的根本原因。
在《田惠世》中,巴金以它的亡友林憾庐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充满爱心,慈祥的老人田惠世。巴金本想在书中驳倒主人公的说教,结果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同他的合流了”。田惠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就是卢梭的所谓“人类的宗教”“他在心里否定了父亲所信的教义,他更不重视礼拜和祷告以及一切近乎荒诞的传说。他和许多非宗教者做了朋友,可是他没有放弃诵读福音书的习惯,他认为这是同‘主’晤谈。”田惠世“抓住的只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爱’字”,他爱家庭,爱事业,最重要的是爱国家,“全部时间用来助人,爱人,尤其是爱穷人”。他热心公益事业,为贫苦人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以致开了顾客盈门的药店却入不敷出,他办《北辰》杂志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像照顾孩子一样关爱它的成长。对他来说,“爱使生命繁荣,失去了它,生命就得枯萎”。巴金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一个基督徒的描写,又通过他与冯文淑的对话,力图写出信教者与非信教者基于爱的沟通;正是因为爱才使田惠世这个虔诚的信徒与冯文淑等青年在救亡图存之际携起手来。
巴金的爱的哲学是与平等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卢梭为自由和平等而建立起一种社会契约,无政府主义提倡个人绝对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而在基督教中人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
克鲁泡特金谈到基督教的平等原则时说:“在基督看来,一个奴隶和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是平等的弟兄,都是上帝的子女。基督教导人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孔子虽然讲“仁者,爱人”,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又讲“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别异的,因而儒家是爱有差等的。不仅爱父母与爱别人差异甚大,而且在君主与臣民,君子与小人,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而巴金呼唤人人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他的人类之爱就必然是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爱,而不是传统文化那种有等级差别的爱了。
巴金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时候,正是他反抗传统最激烈的时候。
大哥的自杀,中断了巴金与大家庭的最后一点联系,他笔下的高家成为传统势力的缩影。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实际上是专制的王国。在和平的表面下隐藏着仇恨的倾轧和斗争,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囚牢里挣扎以致死亡。高家老一辈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千方百计扼杀青年人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在婚姻大事上,“当事人反而作了不能过问的傀儡,而且从前做过傀儡的人如今又来使别人做傀儡了。”他们可以随意安排女性的命运,梅、瑞钰、蕙等美丽善良的女性就因此葬送了性命。至于鸣凤、婉儿等奴婢,更可以随意欺凌,像物品一样赠送他人。高老太爷和克安、克定们并不是有意要虐待哪个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觉新大婚,高老太爷十分高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给孙子带来的痛苦。他爱孙子孙媳,相信自己有权支配他们。他把丫头送给冯乐山也不是有意要害她们,只是认为自己比她们高贵,对她们理应有支配权。高家的生活就是巴金自己家庭的写照。他这样回忆祖父的死:“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卫道者那样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
巴金以争取自由幸福为要义,就是要达到人人平等,摆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束缚。他还借用屠格涅夫的话说:“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三少爷觉慧与婢女鸣凤真心相爱,鸣凤被逼投水自尽后,觉慧发出了欲哭无泪的忏悔。
觉民、觉慧做为家族中的晚辈,在年节时按礼向祖宗牌位和长辈们磕头,但当长辈们凶相毕露,摆出架势要吃人的时候,总是他们首先想到反抗,最后俩人都成了家庭的叛逆者。奉行作揖主义的觉新则容忍了传统伦理的暴虐,既害了别人也葬送了自己。在讲述青年的悲剧命运的同时,巴金一方面揭露旧道德之下伦理制度的虚伪冷漠,一方面呼唤青年们打破枷锁,追求平等与互爱。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传统伦理等级制度进行揭露和控诉是作家的当然使命。从《灭亡》、《新生》到《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巴金都希望用平等的原则代替虚伪的等级制度。他的这种爱和平等的观念,则是受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的影响,而这两者都涉及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精神。正如基督教的博爱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一样,巴金的爱的哲学也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有爱心之人也必平等待人。
爱与平等构成了巴金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
三、罪感与忏悔
忏悔是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基督徒向上帝赎罪的一种形式。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忏悔已成为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不断自我反省、净化灵魂的方式。卢梭曾在《忏悔录》中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会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的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的写了出来’。”事实上,忏悔是卢梭在西方文化转型期对基督教遗产的继承和弘扬。当法国的启蒙哲学家忘记宗教的终极关怀和救赎传统,在理性的旗帜下大声斥责宗教时,卢梭用忏悔意识把宗教情怀引入世俗的道德实践,使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变为对人的现实行为和精神世界的反思。
巴金的罪感意识更多源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思想。民粹主义思想从卢梭那里就萌芽了,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日内瓦共和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以自己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而自豪。
卢梭民粹思想被俄国知识分子接受,并与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东正教精神混合了起来,使民粹主义成为19世纪俄罗斯富有民族代表性的革命思潮。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重要作家和思想家,都有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者们相信,在人民——主要是农民——中保存着真正的生活意义,俄罗斯的灵魂隐在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赫尔岑在农村公社中看到了蕴含的个性与社会性、普遍性原则合理共处的可能。巴枯宁相信真理潜藏在劳动人民中间,在最贫困的群众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民中藏有俄罗斯宗教的真谛。民粹主义者感到知识分子与人民是脱离的,他们在人民面前永远负债。有教养的上层人的罪孽在于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建立在对劳动人民剥削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应该偿还这个债务。民粹主义者拉甫洛夫的《历史的信札》成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手册。这本书出于在人民面前知识分子有罪并必须为这个阶层向人民赎罪的道德动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于是忏悔贵族的形象被创造了出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罪孽并在内心忏悔。东正教宣扬的忏悔意识在另一个层次上凸现了出来,向人民——上帝进行忏悔。
这种忏悔意识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托尔斯泰是巴金接触比较早也非常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巴金都读过。他说自己是“流着泪”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复活》。巴金发表的第一篇与外国文学家有关的文章是1922年的《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早期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性文章,也引用过托尔斯泰关于爱国主义和自由的论述。30年代为反击文坛对托尔斯泰的污蔑,巴金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托尔斯泰虽然以基督的教义救世,但是却猛烈攻击现实中充满陈规陋习的教会,他同情农民的不幸处境,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为贵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恼。这些问题在东正教道德强调的博爱、宽恕和忏悔中都被解决了。《一个地主的早晨》中聂赫留朵夫在自己的庄园中经历了改革的失败。《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在做出同样的挣扎后皈依了上帝。《复活》书名本身就表达了东正教反复阐述的拯救、复活、升华的主题,还引用了《马太福音》中的四段话,于是聂赫留朵夫成为忏悔贵族的代名词。巴金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译过《罪与罚》第二章。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死后的荒诞世界的预见并没有感染巴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忏悔成癖的性格显然对巴金有影响。
巴金很早就为自己出身于黑暗社会中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苦恼和羞愧,认为上等人是有罪的,自己应该赎罪。从早年的创作到晚年的《随想录》,巴金几乎一生都处在忏悔之中。他说:“我们的长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灭亡》中李冷兄妹立誓献身的一瞬,正是巴金的写照:“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家》中觉慧对鸣凤的忏悔与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悔罪就有相似之处。
托尔斯泰从原罪的意义出发,主张宽恕他人和勿以暴力抗恶,而从小生活在基督教氛围中的克鲁泡特金,也对原始基督教的宽恕加以肯定。但成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巴金却无法像他们那样宣扬宽舒,于是他又为自己的不宽恕甚至复仇、暗杀而感到犯罪:“我常常犯罪了!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的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的老师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巴金写作《灭亡》,希望大哥读后明白他的理想与志向,但他的兄长最终也没有读到这本书。被巴金称为“吾师”的凡宰特,怀着宽恕之心宣传无政府主义。
巴金在他被处以极刑之前收到他给自己的信,却没有机会与他辩论宽恕的软弱和无力。巴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难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那些曾经给予自己关怀和影响的人,但自己选择的道路又与他们的思想相背,也许他能通过这种忏悔缓和内心的矛盾与不安。
文学创作虽然给巴金带来了成功,但他更希望能够像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他痛苦地说:“话语并没有力量,我不知道我以后有没有用行动表现自己的日子,倘使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一生,也许是完全白费了。”这些忏悔是巴金对那些领他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的革命者而发的。正是高德曼、凡宰特回答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异国青年的来信,安慰了巴金的痛苦,改变了巴金的人生道路。巴金也曾发誓“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但“他的生性忧郁,他的纳于言,慎于行的个性都使他无法投身到实际的运动中去”。于是巴金留下了深深的忏悔:“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了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只要我能够回到生活里去,我决不再走从前的路了。我要忠实地去生活,去受苦,去拿行动来爱人,来帮助人,不再拿纸笔浪费我青年的生命。”直到巴金醒悟到“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幻梦”时,才终于选择了文学之路:“我愿意他们广泛的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的憎恨。”
巴金的前半生为不能献身于理想而深深地感到忏悔,当他进入暮年时,真诚的忏悔又一次充满了他的心灵,这就是《随想录》。《随想录》中有对国民性的反思,更有沉甸甸的自我忏悔与赎罪意识: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反思”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解剖自己》
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十年一梦》
巴金是在新时期之后,较早地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现代作家。和大部分指责他人的反思不同,巴金的反思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在“文革”中历尽磨难的自己。正是这种由己及人的精神弱点在“文革”中的表现,客观上给“文革”推波助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他在《怀念萧珊》中说:“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无论是为了家族的罪恶忏悔,为了没有实践自己的信仰忏悔,还是对人性普遍弱点的忏悔,巴金都希望通过忏悔摆脱心灵的痛苦,得到一点灵魂的安慰。不过,巴金的忏悔又与托尔斯泰有所不同。托尔斯泰一方面同情农民的不幸处境,一方面为贵族阶级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恼。聂赫留朵夫真诚地悔罪,他从宗教中得到启示,按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工作,从而在精神上得到复活,这是托尔斯泰为俄国贵族找到的出路,这种忏悔并不指向对社会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忏悔中以忍从为美德。而觉慧的悔罪则与传统的道德良心结合在一起,是他觉醒和反抗现实的开始。巴金晚年也在反省自己没有反抗的力量,反而在心灵的意义上助长了摧残人的强暴势力。
四、信仰与牺牲
基督教信仰具有强烈的迷狂性和排他性。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能与对上帝始终不渝的信仰相匹敌。耶和华宣称除了自己没有别神,耶稣告诫众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有足够的信心,没有不能做的事。便是叫一座山从这边挪到那边,山也必遵命不误。”而且,牺牲成为对信仰最重要的考验。耶稣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难于十字架,他的复活则使人坚定了他所传播的信仰。因此,耶稣无疑是西方世界中一位人所敬仰的为信仰而殉道的文化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