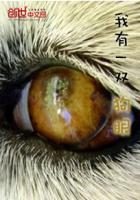杜光庭所宣扬的“心寂境忘”非常强调一个“忘”字,他说:“摄迹忘名,已得其妙,于妙恐滞,故复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总合乎道。有欲既遣,无欲亦忘,不滞有无,不执中道,是契都忘之者尔。”即通过既忘外境,又忘内心,忘之又忘而使人由纷纷扰扰的、令人痛苦不堪的现实世界而进入安祥宁静的“心寂境忘”而合道境界。因此,“忘”既成为在心理经验中展开的一种去除有执的重要方法,也成为“玄道自至”的重要前提。
如果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遗忘对人保持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一个人如果不具备遗忘功能,大脑就可能因载承的信息过多而精神负担过重,这不但会使人陷入色声等低级欲望之中而使人身心疲惫,更有甚者还会使人产生精神分裂。虽然杜光庭所说的“心寂境忘”也许也具有通过遗忘种种痛苦和烦恼以保持大脑的健康,使人的身心得以安然愉快,但他从信仰的角度宣扬的“心寂境忘”并不仅是要人忘记人生的烦恼,更是要人忘掉那些与自己的宗教修行目标关系不大的世俗事务,以保持修行的纯粹性,甚至连自我也忘掉。一旦“心寂境忘”、“玄道自至”
时,道教追求的理想之境也就实现了。这种通过层层否定而达到肯定,以直契根本目标的思维方式,构成了杜光庭重玄学的鲜明特征。
(第四节)言以明理,忘言契道
道教所信仰的对象“道”具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超验性,因而人们通过言语既无法全真地表达它,也无法真正地把握它。
对此,杜光庭也作了强调,他说,“非文字能诠,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献则臣献于君,道若可传则父传于子,斯固非可言传也。”言语作为工具性的媒介,其本身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可以描述事物及事物之理,但难以诠释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道。
“至道高妙,不可言诠,约妙与深,以玄为证言,深妙玄远,以明道体。故谓之玄。”因此,言语在道面前常常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英国神学家约翰·麦奎利就认为:“在许多宗教中,已出现了这种信念:宗教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言说的,或者说,撞击着人们宗教生活的实在不同于日常的客观经验,它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因此我们对它只有沉默。”但道教并没有完全沉默,道教重玄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力图运用“有无双遣”的方法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表达不可言说的道。杜光庭在继承前人的道言之辨的基础上,对于道与言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解说,从而丰富了重玄学的内容。
杜光庭对道与言的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法者,所以诠道也。
悟道则忘法。言者,所以观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滞于法,则道不能通。滞于言,则意不可尽。故令于法不滞,转更增修。于言不滞,旋新悟入。”即认为,言语教法可以用来诠道、观意,但要悟道、得意则必须忘言、忘法,因为任何言语在超言绝相的“道”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不周全,如果人执着于言,则意不可尽;执着于法,则道不能通。只有“于言不滞”,才能“旋新悟入”。
杜光庭认为,一般人并不懂得上述道理,他们“执滞于言教”,结果导致了“失至道之宗”。他说:“执滞于言教,则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说,能明筌蹄之用,则无封执之迷,亦无飘骤之害,而彰散润之德。”杜光庭以《庄子》的“筌蹄之喻”来说明,“言以明理”,因而“教必因言”;但是,如果“执于言”,则“又非教意”了。
他说:
教必因言,言以明理。执言滞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执,既得理矣。不滞于言,是了筌蹄也。筌蹄者,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失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筌者,以竹为之取鱼之器也。蹄者,以绳为之取兔之器也。鱼兔既得,则筌蹄可忘,若执筌蹄,乃非鱼兔矣。若执于言又非教意矣。
在杜光庭看来,虽然言语的功能就是明理,理必须要借助于言语教法才能得以彰显,但言语教法仅为明理的工具与媒介而不是教法之理本身。言语教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媒介和工具去把握终极之道。若执言滞教,执着于言语,拘泥于文字,那只会离言语所表达的意义越来越远,最终导致人忘记隐于言教背后的“至道”而误入迷途。因此,必须“忘言以祛其执”,才能得理、得意而不失道。
由是,杜光庭通过重玄学的方法进一步发挥庄子学说中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而强调了忘言以契真道,他说:
取鱼之器曰筌,以竹为之。取兔之器曰蹄,以绳为之。取鱼则器包其身,故谓之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则绳束其足,故谓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鱼兔。执筌蹄以为鱼兔,失之远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无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执言教以为道,亦失之远矣。夫至虚至静,方能集道,滞言束教,何以契真?至虚以忘言,至静以忘教,不可执矣。
在这里,杜光庭一方面强调,“道不可无言而悟,因言以宣之”,只有采用“以筌取鱼”,“以蹄取兔”的方法,以言语来立教宣道,才能帮助人悟“道”;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执言教以为道,亦失之远矣”,要求人们“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不要僵硬地拘泥于言语文字,而应该忘言忘教以契真道。
道作为一种终极性的存在,它既是万物之本,又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是心灵的一种本真状态。因此,杜光庭在说明应该“忘言契道”时特别强调了心悟。如何心悟?他在解释唐玄宗的“穷理尽性,闭缘息想”时引《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作了发挥。“易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者,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这里,杜光庭通过把万物之理与众生之性相沟通而把穷理悟道落实到了心性的修炼上来。由于玄理真性不可以言诠,因此,心悟也就必须“闭缘息想”以降伏其心,最终才能“穷达妙理,了尽真性”。他对闭缘息想作了细致的解说:
穷理者,极其玄理。尽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考幽洞深,可以神鉴,不可以言诠也。闭缘息想者,随境生欲,谓之缘,因心系念,谓之想。于此门中分为四别。一曰意随善境而生善欲,谓之善缘。二曰意随恶境而生恶欲,谓之恶缘。三曰心系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系恶念而生恶想。虽同因境所起,分为善恶。夫初修道者。既闭恶缘,又息恶想,以降其心。
心澄气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善缘善想,亦复忘之,穷达妙理,了尽真性。想缘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穷理尽性,闭缘息想也。
穷理是穷极万物之理,尽性是究尽生灵之真性。杜光庭沿续道教的传统,以客观世界为大宇宙,以人之一身为小宇宙,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而提出穷万物之理与尽众生本性是彼此联系、相互统一的,对于“考幽洞深”的玄理真性,只可以“神鉴”,而不可言诠,因而他强调“闭缘息想”。缘是“随境生欲”,指人心随境而生起各种欲望;想是“因心系念”,指心产生各种念头。“闭缘息想”就是要人止息各种欲望和念头,以回归人心本来的真性。
值得注意的是,杜光庭在这里运用重玄学而将缘和想依照善、恶“分为四别”而作了解说:善缘、恶缘、善想、恶想。他认为,修道先须闭息恶缘、恶想,以做到心澄气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然后还应进一步忘却善缘、善想,才能最终穷达妙理,了尽真性。他特别强调了“想缘俱忘,乃可得道”。如果说,闭息恶缘、恶想为遣有,忘却善缘、善想为遣无,那么,在遣有遣无的基础上,“想缘俱忘”就是非有非无,杜光庭通过重玄学的方法使心从向外追求转向了反归于自心。
在杜光庭看来,这种“忘言契道”的心悟是建立在心的直觉之上的,表现为一种以塞兑、闭目而摒弃了种种外来的感觉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内心体验。杜光庭说:“欲忘言者,塞其兑。
兑,口也。言语理绝,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闭其门。门,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兑则辩说不施,固无滞于言教。”他从塞口忘言、闭目忘象出发进一步将言与道放到心中来加以辩证,“无为之要诀之于心,以言而传斯非道矣。《西升经》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传。’《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滞于辩说非道也哉。”杜光庭认为,至道存在于人心,如果用形形色色的名言来传道,所传之言就不再是道。道只可用心来悟,却不能以言来传。
针对“教必因言,言以明理”而道又不可说的这种“说不可说”的悖论,杜光庭主张,“修道之士,因经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达妙门,不执言教”。他强调,“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则不烦,无为则不乱,故博于言教者,去道远矣。岂能得玄妙之道兮。”得道之要就在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行道。言教虽能帮助人明理悟道,但从根本上说,道是不可言说的,因此,执着于言教只会离道愈远,执着于言教只会妨碍悟道。杜光庭还从名与道、本与迹的关系对“说不可说”作了阐释,以引导人摄迹返本、复归于道:
道显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谓,有欲之机,兴于此矣。是迹从本而生也。若摄迹者,弃欲忘名,复归妙本。于道忘道,于名忘名,是谓还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沦滑,能返乎物初,可与言乎至道矣。
他还借《老子》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来加以发挥:
名者,正言也。标宗一字,为名之本。可名二字,为名之迹。迹散在物,称谓万殊。由迹归本,乃合于道,是知道为名之本,名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名是用来显道的。道显则名立,名立则人的欲望随之而生。由于道为名之本,名为道之末,因此要复归于道,不仅要弃欲忘名,而且还要“于道忘道,于名忘名”,乃可合于道。
总之,杜光庭的重玄学运用“有无双遣”的方法,通过对心境、言道关系的辩证,以说明主体之人要真正了悟至理真道,就必须通过对有、无的层层否定,最终“既绝俗学,不矜其智,不着有为,不着有法,不止于有,不滞于无,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杜光庭把灭除世俗烦恼视为是“不止于有”,将遣除人的心智视为是“不滞于无”,强调只有遣之又遣,“空有都忘”,才能真正“深入玄要”,达到契道的目的,而这都是在修心过程中实现的。一旦心寂境忘,实际上玄道也就会自然而至。这样,杜光庭通过重玄学而引导人们在心境上实现精神超越,也就为道教心性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