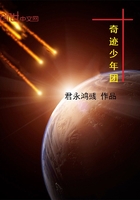孤独有时候就是头张牙舞爪的野兽,有空就大口大口地撕咬肉体。喘不过气?对空气发脾气?抓起手边的东西狠狠扔出去?又比如像现在,从指尖撕下一块皮。看着溢血的指尖突然觉得蛮脏的,每次去做指甲护理的时候都会被嫌弃,老板很直接地说:“小姑娘你就别啃自己的指甲了!多不健康!”为了改掉这个毛病,她拼命给自己找事干。
她应该是个清闲的女仆,除了打扫、吃饭睡觉上厕所,余下的时间都用来画画。花花绿绿的颜料脏兮兮地铺了一地,大大小小的画板歪歪斜斜地立了一墙,珑巫最大的兴趣就是讽刺她,指着画中形形色色的人说:
“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走在雪地里会被狼吃掉的,你怎么这么没爱心!这个老太婆,身边的鸡鸭看起来都快断气了!我还没见过谁画水果像裂开的半个脑袋!”
“要不你来画?除了吼你还会什么?”珑巫瞪大一双兽瞳龇牙咧嘴地喷回去:
“心里阴暗的怪物!我怎么会和你在一处玩!”
“是谁一天到晚往我画室跑?是谁说我应该被时时刻刻盯着?”
“谁时时刻刻盯着你了!丑丫头!”
“你漂亮得很,野兽!”
珑巫站在原地生闷气,半天憋出一句:
“你还是不高兴。”
现在有那么多时间画画,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女孩渐渐垂下扎着马尾的脑袋,盯着桌上的蜡烛沉默不语。窗帘拉得严实,烛光微弱随时可能熄灭,在黑暗的监牢里画画,确实开心不起来。每时每刻,她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看着恍惚的蜡烛就有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大喊的冲动,但是她知道,她不能。除了打扫,什么都不能做。
珑巫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太瘦了,半年来都没见长肉,骨架小小的,衣裙上染着洗不干净的颜料,每次看她端着餐饭走进屋的时候,心里就会产生从未有过的温暖。野兽一开始很不喜欢女孩身上的油彩味,时间久了竟然也会习惯,他没有因为这个去指责禾之,相反,每当闻到这股油彩味他就会感到莫名的熟悉和心安。
野兽安静地坐在一边看她蹲下身削笔,调颜料,用手背把额前一缕头发抹开。矮小的身影跑来跑去,突然停在他面前:
“喂!给我睁开眼睛,那盒玫瑰色的颜料呢?”
被她这么一吼,瞌睡虫全飞没了,珑巫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站起来帮着找。她总会絮絮叨叨地念这还是新的没用过,缺了这个颜色不行,朝他背后狠狠一推,气急败坏地说“你是不是把我颜料丢了”??????珑巫龇牙反驳,一人拿着一个烛台,翻遍了床底,沙发缝隙,洗漱台,甚至马桶里,那盒玫瑰色的颜料还是没找着。“哎呀”一声,女孩红着脸说“那个颜色早用完了,我还没换新的呢,忘了??????”珑巫黑了半边脸,一看她那副讨好的样子又把气放下了。女孩洗洗手,提着裙子跑到厨房抬一锅红烧肉给他。野兽眯起眼睛呷呷嘴,龇起牙露出鲜红的牙龈,吃相实在不敢恭维。酒足饭饱,腿一翘往沙发里一卧睡沉了。听着一阵又一阵呼噜声她忍不住笑起来,抱一床薄被盖在他身上,拿起画笔继续画着。
日子平静,********。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明白温水煮青蛙最可怕的不是青蛙死在锅里,而是青蛙贪图舒适忘记死亡的威胁。再次见到罗的时候,她终于从画画的梦中惊醒,在温泉里泡太久竟然忘了这里有个阴冷残酷步步算计的珑玥需要对付。
一条狰狞的疤痕从她的肩膀一直延伸到手腕,罗倒吸一口气。
“还疼么?”
“不会了,你看。”禾之笑着活动着左臂。
“我找不到你,一直等你回来。”
“对不起。”
烛光闪烁,空气里全是油彩味。罗靠在禾之的膝盖上昏昏欲睡,这个在异世唯一关心她的人如今和她一起关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笼里,如果可以她宁愿从未认识过罗,那她就不会因为罗耳朵下面那道淡淡的疤痕和指尖粗糙的厚茧感到心疼。
“我真的很想你。小时候我??????”
“罗。”
“恩?”
“小时候的事我不太记得,你会原谅我吗?”
罗直起身来,舔了舔干燥开裂的唇,欲言又止。
“你愿不愿意接受现在的我?我还是你的好朋友。”
那双粗糙的手骤然冰凉,她突然怨恨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伤人的话,但她确实没有与罗成长的记忆,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温暖做出该有的回应?有时候姐妹和朋友之间只差一个共同的故事而已。如果放在半年前,那个一心想回家,以为能回家的禾之面对罗的关心不会那么痛苦,当她再也回不了家,还被犯人似的关了半年,哪怕一个关怀的眼神,一句关心的话都会让她暖半天。罗的出现无疑让她又温暖又痛苦,如果罗知道她不是那个一起成长的伙伴,还会这样关心她吗?
她无法接受原本关心她的眼神变得冷漠,更无法接受原本展开怀抱抱紧她的人突然转身给她一个决绝的背影。可她又无法披着别人的皮囊接受本属于别人友谊,温暖和负罪随着罗的笑容与日俱增??????
那头野兽好几天都没来了,每次送去的餐饭却是吃完的。搞什么鬼?禾之喊着珑巫的名字,翻找地上乱七八糟的被子还是不见野兽的影。她顺着走廊到达最后一个没有找过的房间,伸手一扭,锁着。她砰砰砰地拍起门:
“珑巫?野兽!”
“生病了?快出来吃药!”
“你要是再不开门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门开了,屋里的黑衣少年不似以往的张牙舞爪,眼底青黑一片,萤黄的兽瞳中痛苦难忍。禾之冲进门,血腥味扑鼻而来。
“怎么了?”她碰了碰珑巫的肩膀,指尖冰凉黏腻——血?野兽被这么轻轻一碰一张脸立刻苍白如纸,弯着腰恨不得跪在地上,她伸手要去扶,珑巫粗着嗓子吼:
“别碰我!”
“到底怎么了!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兽瞳紧紧一闭,又无奈睁开。他撩起黑色的上衣,胸膛血红一片,被烧的,有些地方结了痂,有些还冒着血。禾之颤着往后退了一步,捂住口鼻几欲呕吐。
“珑梵的红宝石就在附近,我一靠近红宝石胸口就会被烧烂。他们竟然忍不住了,呵哼??????”少年有些踉跄地往屋子里走了几步,跌在地上,一对萤黄兽瞳盯着周围的黑暗。
“我的血脉宝石就在胸口这,这是我作为魔法师的一部分,也是野兽的一部分。有了它我是这世界唯一一个能在野兽和人类之间变换的魔法师。珑家血脉到我这产生了变异,每个人都想要我心上血石,这里藏着珑家血脉所有的秘密。”
“我的血脉石混合了野兽血统,与珑梵魔法师血脉相对抗,结果就这样,烧烂。珑梵要利用我抑制各方势力,但又想要我的命,怎么能让他得逞!你干嘛一副要哭的样子?哭什么!我终有一天??????”他似乎撕扯到胸口的伤,龇牙咧嘴地咒骂起来。
“想折磨我,我非要好好活着给你们看!”
他很疲惫需要休息,可是胸口的灼伤不可能让他好好睡一觉。珑梵的红宝石到底在哪儿?
珑巫抹了抹脖颈上的血,凸起的锁骨像两把尖刀。
“珑玥的如意算盘打得好,我偏不如他愿!小禾,这或许是个机会??????”
她浑身冰凉麻木,牙齿不自主地打起颤。
一只洁白的手取下墙上骷髅的黑眼,原是一颗玄**珠,里面水光之影瞬逝即过。他把魔珠轻轻放在绿焰法杖的凹槽处,细细观赏着幽绿与墨黑交织的光影。魔珠映出一双如寒冬般无情的眼眸,彻骨的寒香弥漫房间。黑暗中传出魔鬼冰冷的声音:
“逃?烂得那么快??????”
太阳藏匿,整个珑城笼罩在朦胧的银雾之中。黑袍被风吹起,袍上金龙像活了一般张牙舞爪。男人旁边站着一个金发少年,不过十四五岁却没有少年该有的蓬勃生机,和黑袍男人一样,目中洞藏寒风飞雪,深蓝风衣猎猎作响,白色领子像尖刀立在他的颈侧,被风吹得略微倾斜。少年手持一把立地绿焰法杖,杖上黑**珠翻滚不止。两人身后是一片波涛汹涌的黑海,海上黑烟时浓时淡。
野兽咆哮,珑家父子看向城堡顶部。
金色野兽立在倾斜的城顶上,似狮似虎,尖耳萤眼,五只爪子锋利如剑,森森獠牙沾染鲜血,目如火炬,燃着不屈愤怒的火焰。金色皮毛血迹斑斑,在诡异的天光下镀上一层银辉,野兽高昂头颅对着天际嘶吼不止,仿佛下一秒就要从两百米高的城顶扑下来。
“二弟,原来你不恐高啊。”珑玥声音不大,但是他知道野兽听见了。
“想死容易,挖了胸口的血脉石,找把尖刀躺上去。何必那么费力?”轻蔑冷漠的笑容浮上狭长的双眸:
“原来你怕剜心破腹之痛,想一了百了。”
珑梵挥了挥手,珑玥低颔后退。
“这么多年,也该成全你一回。临死之前和她见个面,毕竟她是你唯一的朋友,对么?”
摔在地上的女孩大概只有十岁,瘦弱的身板被手臂粗的锁链缚着,黑色的头发乱糟糟地腻在一起,双眼紧闭,脸上血泥模糊。破碎的衣裙下面露出青紫的小腿,荆棘勒进血肉,在细细的足踝上嵌了一圈。
兽血淋漓,顺着尖顶流下来,像一道道弯曲的血泪,野兽的吼声充满愤怒和悲伤。
“残忍?我说过,你在上面呆一天,我就在她身上弄出一道疤。你要么回屋去,她活,要么跳下来,她死。”野兽呜咽一声往后退,殊不知这一退让他半个身子掉在空中!兽爪慌忙抓住城顶边缘,粗壮的前肢慢慢撑起上半身,后腿蹬了几下。
有惊无险,野兽喘着粗气,血沫从口中不停冒出,他踉跄了一下,半边身体几乎瘫倒。
珑梵微微一笑:
“怎么?改变主意了?”
倒在地上的女孩醒了,她仰起头,死湖般的眼里落进一个金色光团。
“珑巫,回去!别跳下来!”回去哪儿?回到那个黑暗的监牢?回到杀机四伏的房间?回到唯一的光明要靠一根蜡烛来给的日子?他宁愿死也不愿这么活着!!
风吹起布满鲜血的皮毛,萤黄兽瞳中火焰明灭,沙哑的吼声,哀伤绝望。僵硬石的脸竟然皱起眉头,苍白如死的手一展一颗银光四溢的魔珠自手心幻出,看着苟延残喘的禾之,珑梵心里划过一丝不安。
以后这个女孩会做出什么事让他不高兴的,所以??????
一个银色的光圈从珠子里飞出向女孩砸去。
野兽如同被刀割了一样咆哮起来,光圈在禾之的脑侧停住了。她只是个没成年的普通人,不像血脉法师从生下来就三魂俱全,吸走了这女孩的人魂和灵魂,她就会没命。
“好吧,我不杀她。但那怪物许久没进食了,怎么办呢??????”深陷的眼里邪光闪过,这个异种的血脉石混合了魔法师和野兽的的血统,珑巫一死,在他身体里的血脉石就同一般石头无异了,只要他愿意自行取下这块异石,最后是死是活珑梵才懒得管。
兽瞳里血丝遍布,野兽烦躁地刨着屋顶,破碎的砖块轰隆隆地往下掉。他无法相信阴险的父亲,他如何能确定在转身进屋的那刻禾之能安然无恙呢?
黑袍逆风飞扬,一头似蛇非蛇的九爪异兽从袍里腾空而起,长约十米,无目无角,身披金甲,声若魔灵,尖叫刺耳。只见珑梵身后的黑海之上黑雾聚集,露出徒手而立的百万玄盔士兵,黑雾被九爪异兽吸进肚里,金甲异兽顿时暴长数百米,背上四对披甲龙翼狠狠一鼓,狂风肆虐,飞沙走石,百米异兽直入云端,穿破银色的太阳露出巨大的脑袋,珑城在它面前就像一只蚂蚁。异兽额上尖角嶙峋,张开嘴露出三排牙齿,尖啸不止。金色九爪异兽从云端飞下,卷起狂风,低头匍匐在黑袍男人脚前,珑梵把手中魔珠往上一抛,魔珠嵌入异兽头颅变成一只银光巨眼。银眼渐渐被黑雾笼罩,这黑雾不是别的,正是百万士兵的魔魂。
这东西是他在落魂骨山找到的宠物,名“燥”。驯服顽劣傲慢的异兽只有剜了它一双银眼,一只为己所用,另一只送给珑玥当九岁生日礼物。珑梵咒术噬取魔、人、灵三魂,燥以三魂为生,银眼可以净化黑**魂,它的存在恰好弥补了咒术反噬的缺点。
浴血野兽从高空一跃而下,金色光团如日陨落。法杖嘶鸣燃起熊熊绿焰,少年面目狰狞,眼底血浆奔涌而出,白色短靴被血水淹没,身上的血肉一块一块掉下来坠进脚底血池,只剩森森白骨,那个冰冷邪恶的少年化成碎骨,骨片以绿焰法杖为中心时聚时散,杖上玄珠分成六瓣旋转不停,散发彻寒香气的血雾顿时汹涌如洪淹没百万士兵。珑梵跃上燥首,四对披甲龙翼卷起呼啸狂风,异兽尖啸,直入云端。
被下了血咒的士兵变成一堵堵血肉之墙,往上飞去。从高空坠下的金色光团砸碎了一道人墙,下一道人墙毫不犹豫地补上。人命是粪土!这是咒术真正的恐怖!黑色的眼中血雾扩散,无助和恐惧压迫着她脑里最后一根弦。天上地下,血水瓢泼,血锈里诡异的香味侵入几乎停滞的心脏,她爬在地上无法移动,腥黏的血瀑从头顶直冲而下,她的额头不受控制地一下一下撞向坚硬的土地??????
七百堵人墙,一百三十万人性命变成潺潺血河,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一个血红的肉团倒在地上抽搐着,珑梵一脚踩住肉团的尖耳说:
“没我珑梵庇护着,你早被洛家五马分尸躺在实验室里了!忘恩负义的东西!”
珑梵张开五指一抓,银珠从异兽眼处剥落,渐渐变小落在苍白的手里消失不见。燥尖啸一声凭空消失,黑袍上金色异纹隐约浮动,黑袍一展,他狠狠捏住女孩的下巴,苍白如死的皮肤染上猩红。他很高兴,因为这双眼里那讨厌的倔强终于不见了,空无一物如同死人。
“我越来越期待你的表现??????下次死的可就不是这些猪狗了。或许是你的朋友?”珑梵狂笑着,面部扭曲如鬼,邪魔的声音来自地狱,回荡在寂静的天地间。
正当珑梵得意之时,血雾未散的空中划过一道星痕,晶莹透明的蓝色水流倾泻直下,裹住地上伤痕累累的野兽和女孩。
魔鬼眼珠凸起,他慌忙伸手想抓住女孩。
“怎么会这样!!”珑梵疯狂地大吼起来。那个禾之!她竟是透明的绿色人魄!!这怎么可能!!既然如此??????珑梵抽出一把锋利的长刀,毫不犹豫地往珑巫心口剖去!一道绿光比长刀更快,落在珑巫身上变成一层绿色的保护膜,在星辰水的庇护下,野兽和人魄消失不见。
日光如噬,天昏地暗,狂风肆虐,黑袍猎猎,珑城死寂一片,血腥浓烈未散,只听一声要把仇人碎尸万段的怒吼:
“他日我必屠尽你洛城!!”
洛溟睁开眼,整个人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沟壑遍布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星辰天河水救得了珑巫一时,救不了一世。只能祈求上苍,把那两人带到安全的地方。他洛溟为了抑制珑梵处心积虑半辈子,在死前却救了珑梵的儿子,也当真可笑。若没有猜错,珑巫身边的那个丫头将是唯一能拯救洛城的人。此后种种就交给上天吧!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