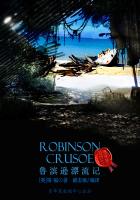当晚,天仁回到窝里,一宿难眠,忽而想到丹尼,忽而想到自己赔出去的钱。哎,丹尼的事情改天再仔细问问丽丽,可赔出去的钱怎么才能弄回来?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儿啊。
天仁从口袋里掏出钱老板的身份证,再看住址:广东省河源县……走,找他去,抓住他,先要他把我的钱还我。他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先揍一顿再说,但下手不能太重,记住八打八不打:一打眉头双眼,不打太阳为首。二打唇上人中,不打正中咽喉……
早上起床,天仁顾不得去向黑人点卯,直奔罗湖口岸长途汽车站,上了开往河源县的中巴。时近中午,车到河源县城,天仁下车,几个摩的司机围上来。天仁拿出钱老板的身份证,示意自己要去身份证上的村子。
一个小伙子一把夺过,一看,操广东话说:“哦。这条村我知啦,在万绿湖边啦。20块钱,我载你去啦。”
天仁坐上小伙子的摩托车后座。不多时,摩的风驰电掣,来到万绿湖边。天仁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放眼望去,好一派湖光山色,忍不住口占一绝:
涛涌南海起萍末。
峰接五岭止湖滨,
合当秋风明月夜,
扁舟一叶钓大鲸。
天仁任清风吹拂自己的脸面,身心回归大自然。一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就好像忘记了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我将来不愁吃喝了,也隐居到这湖边来算了。
摩的停在湖边一个村口,小伙子说:“到啦。”
天仁下摩的,付了20块钱,独自向村子里走去。几个小孩子放学回家,闹闹嚷嚷,跑过天仁身边,天仁连忙叫住,掏出陆玉明的身份证,问:“小朋友们,认得这个人吗?”
小孩子们围上来,一看人头,嚷:“不认得。”
天仁念:“陆玉明。”
“陆玉明?陆爷爷?认得,认得。”小孩子们齐声嚷嚷。
“能带我去找他吗?”
“好嘞!”小孩子们闹哄哄带上天仁,走向村边一块菜地,菜地里一个老头正在挖地。
小孩子们老远就喊:“陆爷爷,有人找你啦!”
老头停住锄头,眯起眼睛,从草帽下观望天仁。天仁谢过小孩子,独自朝老头走去,拳头握得紧紧,越靠近那个老头,越觉得不对劲儿。走到近处一看,哪里是姓钱的?分明是一个老农夫,皮肤黝黑,慈眉善目。旁边,一只威武的大狼狗坐在他身边,目光炯炯,精神抖擞。
天仁疑惑起来,难道老农夫与钱老板……不,与陆玉明同名?
老头主动打话,用当地客家话问道:“后生仔,你搵我做咪吔?”
天仁掏出钱老板的身份证,递给老头看。老头接过一看,火冒三丈,一把把身份证扔到地上,抬脚便踩,还没等脚踏下去,又连忙收住腿,弓腰捡起来再看,火气更大,扔下身份证,一锄头挖下去,满口连珠炮般骂不绝口:“叼你老姆嗨……叼你老姆嗨……”天仁手一抬,刚欲阻止老农夫毁灭证据,大狼狗嗖地立将起来,两道红外线光柱从大狼狗眼中射出,仿佛两根钉子牢牢地把天仁的一只手掌凭空钉在空中。钱老板的脑袋早被老头的锄头下砸成冤鬼。
老头骂够了,砸累了,这才停住锄头,恨恨地喘粗气。大狼狗收回自己的两根钉子,斜躺下去。天仁的手掌得以松动,耷拉下去。天仁从老头那一通客家土话海骂中,连蒙带猜,听出大体意思来:两年前,老头自己背上米,到钱老板的工地上打工干活,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工程一完工,钱老板人跑了,百十来个农民工大半年的工资血汗钱也被一同卷跑了。老头留在钱老板手里的身份证,被钱老板偷梁换柱篡改冒用了。
老头歇一阵气,再次问天仁:“你搵我做咪吔?”
天仁比比划划说了大半天,老头终于明白了,应道:“后生仔,你也被骗了钱。”天仁点点头,老头摇头叹息。
天仁失望之极,跟老头对望一阵,心想,语言交流也不顺畅,还是回去吧。天仁转身离去,老头拄着锄头,目送天仁。
天仁来到万绿湖边高高的护堤上坐下,望着一湖碧波发呆。哎,我找错地方了,这一方灵山秀水,怎么可能出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张假的身份证真的就是钱老板做的?那他又何必扔在办公室里为别人留下线索?莫非是想把别人引入歧途?听眼镜讲,钱老板以前是开猪饲料厂的,怎么又成了包工头?眼镜的情报准确吗?因为鸿发公司索赔,钱老板逃债?可他那么大老板没必要卷了新来的员工那一点点钱啊。要不就是他发现眼镜给他戴了绿帽子?不对,眼镜给他戴的也不能算是绿帽子,李美人本来就不是他的老婆。按照阿Q的哲学,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你钱老板家里有老婆,不是和尚,李美人更不是尼姑。站在茅坑不拉屎,不,拉屎的次数不多,眼镜不也早说过老板用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吗?茅坑经常空着,茅坑也空虚,你让人家李美人怎么受得了?可李美人怎么会看得上眼镜?李美人向钱老板摊牌自己要嫁给犬子后,钱老板撤藩逃跑?犬子向李美人下的订单本来就是聘礼,钱老板卷了聘礼逃跑?钱老板发现李美人肚子里有了孩子,为犬子留下个勤王嬴政?钱老板发现李美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撒手不管,溜之乎也?李美人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挖地老头说的话真是我猜想的那个意思……
天仁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刚入行就遇到棘手案件的公安局刑侦人员,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一瞬间,脑袋里就涌现出十万个为什么,心中感到无比地空旷和无助。哎,算了,人是世界上最看不透的动物,就这么个小小的钱老板捐款潜逃的案件都把这么多人牵连了进去,每个人的心里又潜伏着看旁人看不透的心机,就算请福尔摩斯前来,恐怕也理不出个头绪。我的钱,舍了就舍了吧,谁叫你自己一时冲动,自己充冤大头的?手里刚有几个钱,就不知天高地厚想当慈善家。慈善家是你天仁配当的吗?人家那么多有钱人都缩头乌龟似的往后躲。你倒好,两个卵蛋打架,把你挤冒了出来,你到底算哪根葱?
忽然,天仁听到脑后有异响,回头一看。啊?!大狼狗正闪电般朝自己冲来,后面老远跟着的老头,也正拼出浑身老力朝自己冲来。天仁本能地“嗖”地站起身来,往后一退,“扑通”,一脚踩空,掉进湖里。“扑通”,大狼狗也跳进湖里,一口叼住天仁的衣领就往岸边护堤低矮处拖。老头赶到,也“扑通”一声,跳进湖里,拽住天仁一只胳膊就拖。天仁拼命挣扎,也摆不脱大狼狗和老头。
大狼狗和老头合力把天仁拖上岸。老头扔下天仁,拍拍大狼狗的头,表扬道:“赛虎,我明天买笼心肺给你吃。”转头数落起天仁来。
天仁惊魂初定,恍然大悟:天哪!赛虎以为我要跳湖自尽,冤枉啊冤枉。天仁哭笑不得,连连解释:“老伯,是赛虎把我扑到湖里的。”
老头连珠炮似的当地客家话又出口了,天仁连蒙带猜,明白了老头的意思:赛虎把你扑到湖里的?笑话。那你再让赛虎扑扑看,明明是你自己先跳下去,我们赛虎才跳下去的。我们赛虎最通人性啦,你往那儿一坐,它就知道你想做咪吔?
老头再次拍拍赛虎的头,赛虎把头往老头身上蹭蹭,又目光炯炯地盯住天仁,生怕天仁再次投湖似的。
天仁有口难辨。赛虎啊赛虎,你到底是个畜生,你我语言不通,我可如何向你解释?你这个畜生可比人善良多啦。天仁模仿赛虎,甩甩头上的毛发,洒下一圈水珠,也拍拍赛虎的头,眼眶里一阵酸涨,说:“赛虎,哥哥我明天也买一笼心肺给你吃。”老头不容天仁分辨,拉起天仁就往村子里走。赛虎跟在天仁身后,押俘般把天仁押进村子。
当晚,天仁住在老头家里。老头一家大小,左邻右舍,呼啦啦来了四五十人。这拨走了,那拨又来。天仁也懒得再解释了,越抹越黑,似懂非懂地听凭大家开导、劝慰、鼓励、责骂。哎,这些村民宁肯相信赛虎这条狗,也不愿相信我这个人,没办法,人是造物主所创造的生灵中最不可信赖的物种。
一个老阿婆语气坚定地说:“这个后生仔肯定是遇到鬼了。”找来了纸钱点燃了,衣兜里装上一大把米,嘴里叽叽咕咕,念念有辞,去房前屋后到处打鬼。天仁暗笑,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就这位老阿婆说对了,我遇到骗人鬼了。
几个白天碰见的小朋友也来了,手拽着大人的衣襟,胆怯地望着天仁,怕得要命,不敢近前。天仁心想,我在这几个孩子的眼里,已经不是他们白天遇到的那个朝自己问陆爷爷的大哥哥了,而是刚刚从湖里捞起来的那个大哥哥的尸体,要不,就是那个大哥哥变成的水鬼。
第二天早晨,天仁要走了,几乎全村的人都赶来相送。老头不放心,跟着天仁走,赛虎也跟来。
村庄渐去渐远,天仁忍不住回头,见那些男女老幼还站在村边,一动不动,在薄薄的晨雾中凝固成一排黑黝黝的剪影。经过湖边护堤时,天仁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坐下。一旦坐下,那一排剪影立刻就会像田径场上听到发令枪响的运动员们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我冲来。天仁一路听着老头数落,默默地低着头,感到老头简直就是客家人的守护神伯公转世,紧紧地护佑着自己。跟在天仁身后的赛虎,更像是一头恪尽职守的牧羊犬,忽左忽右,看护着自己的羊儿,经过湖边时,一纵身跳到靠湖一边,双目炯炯,监视着自己的羊儿,生怕自己的羊儿再次调皮捣蛋跳进湖里。
一轮红日从东边山冈缓缓升起,淡淡的晨雾为山岗下的平原罩上了一层薄纱。大地寂静无声,绿色的庄稼生机盎然,唱着无声的歌。
天仁默默地走着,有力的脚步,踏着大地,只感到这是伯公的土地——厚重而坚实,养分充足得很。不信,你今天种下块砖头试试,明天地上就会长出一栋大厦来。
太阳出来啦,大地撒满金光。
来到公路边,天仁又第N遍信誓旦旦地向老头保证:“我不会做傻事。”老头还是不放心,颤巍巍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死活要塞给天仁。
天仁坚辞不受,熬不过老头,只好接过,低头一看赛虎,说:“老伯,麻烦您老用这张钱帮我为赛虎买一笼心肺。”赛虎一听,一蹦老高,一口叼过天仁手里的百元钞票,跑离十几步才转身站定,望着天仁,尾巴轮得溜圆。
老头又气又恼,手指着赛虎,眼望着天仁,嘴里骂个不停。天仁又连蒙带猜,老头的大意是: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狗东西,一听到你说要给它一笼心肺吃,它就一点礼貌都不讲啦,畜生啊畜生,就知道吃,哈哈哈。
天仁也忍不住笑:“哈哈哈。”
“汪汪汪,汪汪汪。”赛虎应答两声,又赶紧低头,叼起飘落地上的百元钞票,尾巴抡得更圆。
一辆中巴过来,天仁上车。车开出老远,天仁从车窗伸出头来,见老头和赛虎依然站在路边,身上罩着一圈金色的光芒,仿佛是两尊雕像。天仁的眼圈潮了,滚下两行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