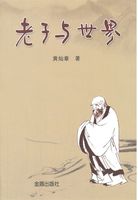总而言之,现代中国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是一个开放的人格形象,具有这样一些总体性特征:追求知、情、意的统一,尊崇竞争、功利、个性、自由的现代价值观念,注意人格与现代性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人格的自我认识与反省,承认多样化的平民化人格培养途径,以人格的关怀寻求生命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平民化人格话语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从梁启超到胡适、鲁迅、冯友兰,再到马克思主义等等,经过几代哲学家的诠释和论辩,现代中国的平民化自由人格形象日渐丰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圣人人格形象。如果说传统儒家理想人格范型的中心词是:“圣人”与“德性”,那么,相对于此,现代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中心词是:“平民”(现世、民主)和“自由个性”。人格中心词由“圣人”到“平民”、由“德性”到“个性”的转换体现了人格的现代性取向,表明了现代中国哲学家关于平民化人格的“想象”。一句话,现代理想人格范型的总体特征是:由圣入凡,由圣人走向平民。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圣人”被逐出“伊甸园”。可以说,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思想是中国现代人格建构之可能性话语的结晶。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家贡献于世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在探究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哲学家已经提出不少富有创见性的思路,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继续思索并解决这些问题,将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当代自由人格的建设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包括:人格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第一章)、个性与他性的关系(第二章)、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的关系(第三章)、人格与制度的关系(第三章)、自我认同与社群认同的关系(第四章)、德性之知(人格认识)与闻见之知(科学认识)的关系(第四章)、对话与人格培养的关系(第五章)、日常生活与人格培养的关系(第五章)、人格的平民性(现世性)与超越性的关系(第六章)、自由人格与责任人格的关系(第六章)等。这些开放的、启人思的问题将伴随人类的实践与时间进程呈现出不竭的新鲜意义。
二、人格认同危机与平民化人格的当代意义
从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看,平民化人格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性意识的发生存在着同步性。因此,只有把人格建构话语放在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才能体会其深意。
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有形的、物质的层面上,而且表现在精神气质与人格特征上。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由具有现代性人格特质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一个共同体需要一种精神气质,这个气质常常体现在人格上。缺乏自觉的人格意识和精神面貌的个体很难说是一个称职的现代性社会成员。现代性社会的实现自然包含精神生活质量与人格素质的提升。所以,不能撇开人格的现代性来谈论社会的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人格的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内在尺度。
社会进入现时代,超验世界及其主宰者退隐了,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趋势不可扭转。神圣的东西悄然消退,感性的、情感的东西大张旗鼓地登场。海德格尔称此现代性现象为“弃神”。①在此过程中,几种现代性制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当其冲的是媒体。各种媒体上充塞着流行的、时髦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话语,以舒服的、休闲的方式控制着大众,大众变成符号化的个体,享受的是同一口味的美食,穿戴着同样风格的饰品,大众的欣赏趣味、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其次是专业化的分工制度,这是以专家符号的形式出现,背后的支撑者是科学知识。专业化制度在造就专家的同时,也控制着现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制造着大众对科学知识及其对科学家的信任,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控制着大众。这些现代制度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格观念。用心理学家荣格(Car1GustavJung)的话来说:“人,这个所有历史发展的鼓动者、发明者和推动者,这个所有判断和决策的发出者,这个未来生活的设计者,在现实社会中却必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化个体。”②这是后启蒙时代个人生存的困境。当个人变成“数量化个体”的时候,个性或人格也就隐匿了。
鲍曼(ZygmuntBauman)分析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初看起来,大屠杀与我们所讨论的人格的现代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大屠杀不是看作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看作一个文化符号的话,那么,它表征的是一种恶(或灾难性)的符号,它告诉我们:现代性(及其制度)出了问题。上面提到的媒体、专业化制度多少带有“大屠杀”性质的符号意义。所以,作为文化符号的“大屠杀”涉及到人格的现代性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参与了“大屠杀”,也有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的人格在“大屠杀”的进行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遮蔽或消解,人格的独立性或多或少丧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惨剧?这是值得深思的关于现代性文明的弊端的问题。
①《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886页。
②荣格:《未发现的自我》,张敦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第28页。
“大屠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的问题,本质上,这是一个现代性文化的问题。鲍曼指出:“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这种文化强调理想生活的设计源于理性。在施行园艺工作之前,园艺者已经有一个方案。现代的“大屠杀”工程就是类似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如果花园的设计有对杂草的界定,那么有花园的地方就必然会有杂草。而且杂草必将被清除。”①何谓杂草何谓香花的界定出于理性的先验界定。
官僚制度也是这种现代园艺文化的一个实例。“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②现代官僚制度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工具理性精神。现代人在园艺文化下屈从于理性设计的安排,自我或人格的自主性多少有所失落。在这样的现代性文化下,自我的认同,或者说,人格认同出现了危机。
①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124页。
②同上,第24—25页。
人格认同危机的实质是意义世界的遮蔽。置身危机之中,人们有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缺乏一种框架或视界以确定他们是谁、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这是“痛苦和可怕的经验”。①人们在作价值选择时常常无所适从,缺失可供参考的理想维度。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看,中国人的人格认同危机感可能比西方人更强烈,因为我们不仅面临着类似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更面临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文化记忆的丢失、当代社会文化的结构转型等地方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在价值与伦理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一个主要困境便是人格(自我)认同危机问题,或意义的掩蔽问题。
现代中国哲学家们显然不满足于险象环绕的西方现代性观念,试图挽救认同危机。他们对平民化人格的思考是一种重建现代意义世界的努力,把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的建构看作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现代性要求给平民化人格的建构提供了一些新的向度,使平民化人格具有现代乃至当代的品格。因此,平民化人格的思想凸现出对当代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批判性识度。
①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37页。
意义世界的遮蔽对现代中国思想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堪的事情。他们觉得有责任来“拯救”这个不可或缺的意义世界。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既认同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文明,同时也注意到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局限,即科学实证主义的张扬导致人文精神的遮蔽和意义世界的失落,这在梁漱溟、张君劢等现代新儒家的著述中清晰可见。“拯救”的一个基本途径是重释传统。“五四”以后的不少中国思想家重拾传统文化,和近代初期的思想家提倡“中体西用”不同,如果说他们还带有守护传统的意味,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那里,这种意味已经大大淡化,弥补西方现代性的意义缺陷是他们考虑的一个主要议题。他们不是消极地回归传统,为了传统而回归传统,而是在正视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积极的创造,回归传统以吸取传统精神资源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可与守旧同日而语了,其实这恰恰展现了他们的创造性、革命性的一面。“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①因此,重新检讨与审视传统是解决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途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是广义的。“传统”与“古代”并不同义。如果说“传统”有古代与现代之分,那么,现代中国的平民化人格理想无疑构成了现代精神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②这个现代“传统”自然将成为我们反思和检讨的一个内容。
当代人格认同危机是与现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体现在:一方面,这种危机是现代平民化人格话语危机的逻辑延伸。当代人格建构的困境主要涉及到下面几对紧张关系: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式人格、个性化人格与奴役性人格、人格分裂与人格整合、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等,这些内容在现代平民化人格话语里也有所体现。另一方面,现代平民化人格话语又蕴含着克服当代人格认同危机的可能性,隐含着走出危机的理论指向。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中国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是集体思想的结晶,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与精神生活的完善无疑富有启示意义。中国哲学家在现代性背景下努力阐发出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多重意义世界,视平民化人格为存在意义的承当者,力图“挽救”人格的认同危机。我甚至认为,由现代中国哲学家开启的平民化自由人格不仅是当代人格建设的一个方向性提示,而且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范型。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家视野里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具有深刻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不仅通过上文论述的人格话语框架结构(如心理学、价值观、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和超越论等六个维度)表现出来,还通过平民化人格范型的总体特征和中心词的转换表现出来。
①《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506—507页。
②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第5页。
上文已经指出,当代中国的人格建设危机主要表现为意义的遮蔽问题。正是在危机中孕育着转机的可能。我认为,解决危机的实质是要使个人重新获得人格(自我)认同,不是将人格交付给集体秩序的认同,也不是交付给关于“上帝”的信仰体系,而是建构真正属己的自我认同。现代的平民化人格话语使得在当代中国达成这样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得以可能,这就是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认同。从人格认同的视角来看,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应该主要围绕着“谁之人格”、“何种人格”两个问题展开。“谁之人格”的问题涉及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的关系。“何种人格”的问题可以区分为实质性、形式性、过程性三个层面的问题,实质性层面的问题涉及自由人格与个性化人格的关系,形式性层面的问题牵涉人格分化和人格整合的关系,过程性层面的问题牵涉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关系,其中,实质性、形式性层面的分析是静态的,而过程性层面的分析是对自由人格的动态把握,三个层面合起来构成“何种人格”的基本内容。
第一,“谁之人格”: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是一个大众化、又绝对信任专家的时代,是一个去贵族化、又崇尚英雄的时代。王公贵族被逐出历史舞台,人人都是平民,追求平民化的人格,但是,人人又都有明星的梦想,有获取他人承认、被他人关注的欲望,追求英雄化的人格。在个人的人格欲求中,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的追求并存,两者的紧张关系由此而产生。这构成当代中国人建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第一个“难题”。
换一个角度看,上述紧张关系恰好辩证地内在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允诺了这两种可能性的人格。在现当代,平民所希冀的不是圣人,而是明星或成功人士,我们暂且把他们称为大众时代的英雄。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巫去魅的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新的神话。现代社会需要的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英雄,而是为大众服务的英雄,而且使每个平民都有可能变成英雄。现代性社会制度的一个功绩就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同时,现代的英雄也有可能成为平民,随着影响力的消退,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古代社会塑造的圣人人格是恒久的,是万世之楷模,具有崇高性。现当代社会的英雄是临时性的,今天还星光灿烂,明天有可能销声匿迹。一旦没有市场、没有观众,英雄就会变成普通的百姓。英雄化人格是由大众的趣味、情调、知识和思想决定的。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是,实质上,他没有自主性。在古代的思想传统里,圣人人格影响、滋润着平民;在现当代的社会语境里,大众的知识、趣味影响着英雄化人格。因此,平民化自由人格本身兼有平民化人格与英雄化人格双重维度。两者的紧张关系恰好构成了平民化自由人格完善自身的一个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