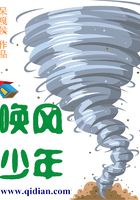六月无可奈何被阖池君擒到赤何面前。
赤何君一袭白袍丰神俊朗,一双挑花眼瞟着她微微上挑,面如冠玉,活脱脱一付好相貌……如此公子,六月真是想不到他披袈裟敲木鱼的模样。
“伸出手来。”
“啊?”
赤何君看着她颇有些不耐烦,“你相公急急把我招过来不是安胎把脉么?小爷心急火燎来了,还不给小爷伸出手来。”
她一脸委屈望着阖池君,阖池君朝她笑得十分和煦。
六月揣揣伸手。
赤何这脉把得许久,眉头皱了又舒舒了又皱,六月心下小鼓便随他捣个不停。
阖池君在一旁也有些忧心,“可有什么不同?”
他哂道,“也不知是如何了不得的大事,山高水远就要急急招我过来,”赤何君撒手挑起一旁凉茶,“无事。就是你重色轻友为了媳妇竟然要挟我,这点子我颇伤怀,遂也吊吊你的心焦。”
阖池君粲然一笑,朝他做辑,“确实是阖池不厚道了,你既来了,谢礼自会奉上。”
他走到书桌旁提毫研墨,六月倒还没见过赤何君写字的模样,倒是觉得他落笔姿势非凡俨然入画,颇有几分清俊雅仙的风流形态。
他把药方子递给阖池,“每日只管灌她一剂,保准日后你孩儿如你一般精骨清奇英雄盖世,闲得无事只懂醉卧美人膝。”
六月一脸黑线。
阖池君倒觉并无不好,笑道,“承你贵言。”
赤何君吊儿郎当接着饮凉茶。
阖池君照医嘱乖乖煎药去了。
六月左顾右盼若无其事。
赤何君冷不丁开口,“虽是时日久远,但未足月便搭得出散脉,你以为小爷我那屋子医书都是白读的?”
她就知道就知道……六月低头,“我倆虽苦大仇深,但此番,我是真真切切的谢你。”
赤何君搁下手中茶盏,不禁渭叹,“你与阖池,一个蠢笨,一个眼瞎,倒是堪堪相配。”
他看她悲切样,转头,“前些日子我外出游历,阖池托我将你以前一些札记顺道送往华胥山,那里有一位神尊在凌霄顶上结庐而居,想必你还记得一些吧?”
六月涩然,“阖池他……”又是何必。
赤何君眉目含星,摇头晃荡,“既是前事,本也没什么。不过我到那里倒是遇见一个人。此人门第府高,可惜如今不幸已沦为邪仙,算得做你累世的仇家,再细细算,与阖池之间,也有那些仇怨在里面。”
她讶然,“你是说琉音?”
“我与阖池乃是挚友,论起道义,应是亲自将她擒来清算各种纠葛。可天道伦常因果报应,她那时闯到华胥山遇见息渊帝君时,已是入了魔障。”
六月闻言一怔,“你是说琉音疯了?”
赤何君默默点头。
“神识已灭,再来计较前尘往事,她也是无知无觉,又是何必纠葛不休……息渊帝君看她处境凄凉,尚顾念旧情央我找到病灶,我遂以灵识游于十二周天,窥她往事……”
她一脸苦瓜相,“你都知道了。”
赤何君见她伤怀,一时无言以对。
这世间痴男怨女,为了一个“情”字,不知种下多少孽障。
良久后,她问他,“琉音呢,你可有治好她?”
他缓缓摇头,“息渊帝君说,她若是疯了,是尚存人知;她若痊愈,倒是一点悲悯都不存了,还不如不治……而后不久,长空寻踪而来,如今已携她归去,此刻应不知处身在九州六合三千世界中哪一处了。”
六月心底一片苍凉。
其实,她除了可惜,早就不恨了。是非对错,本就不是道义戒尺便可轻易衡量的……而她,也早有了阖池,愈合心底所有伤口。
她的结局,有了他的情深不许,绝不悲哀。
她坦然一笑,“赤何,从今以后,我六月认你这个朋友。”
赤何君见她傻头傻脑不免嫌弃,“与你这蠢妖为友,小爷我实在是不甘心。”
公子如玉高阳,浊世混沌里一抹清汪。往事疏忽大意,鲜衣怒马也曾惹沧桑。无量海里飘渺一粟,袈裟将换白袍,经年成伤,贪看远道白光。
六月看着他眉开眼笑。
赤何眉目收敛,眸光低垂,袖袍口里递出书信一封,“我离开华胥山时,那人站在凌霄顶端,素衣宽带,种灵蕴仙,嘱咐我捎带给你。”
她接过,看到信封上“六月亲启”几字,一如往昔的笔锋清勁。
有那么一瞬,她几乎就要灵识混沌。
八百年前,她睁开眼,就是面前的姣姣神君……她会记得他的诺言,沧海不倒,不复相见。
其实,岁月过去了多久早便不重要了,沧海桑田倒不倒也无关要紧……因为他们早已心疼彼此的心事,为了彼此的感伤而感伤,成为了亲人,就不会再无知伤害。
赤何君识趣陪着阖池君一块煎草药去了。
她慢慢拆开信封:
琅琊,
我予你灵识,习你法术,
待你,自以为问心无愧。
可你命盘因我而起,
兜兜转转,我醒悟,轮回一世,终究欠你良多。
……………………………………
她看得有些怅然若失。
阖池君端着汤药走过来,收起她手中的书信。
问她,“药已煎好,你喝是不喝?”
她睁着朦胧的眼看他,阖池君眉目处处温润,袭着身后的一缕夕阳,落寞深刻,仿佛就是地老天荒。
她笑道,“怎的不喝?夫君花了大力气得来的方子怎的不喝?夫君喂我就喝!”
碧海苍穹,阖池君在夕晖下朝她笑得温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