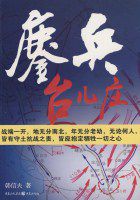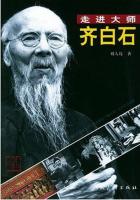田松已经来了两天了,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整理个人物品。
自曲连长那铜锤一样的大嗓门儿在走廊里吼了句“各班可以组织新同志写写家信!”后,有好些人摆出了写信的架式,像以前的书生大考一样在咬着笔头或抓着脑门写信了。
田松所在的新兵二连三班9名新兵已经全部到齐了,因为班里只有8个铺位,所以有一名北京籍的小胖子新兵与一名河北籍新兵和其他几个在本班住不下的新兵一起住到了排部(就是排长住的房间),他们每天必须自行到各自班里集中。
在填写新兵个人信息表的时候,因为田松填得最快且字迹也还工整,所以被唐班长指定为表格填写“临时辅导员”,负责指导和审核其他8名新兵填写表格。在辅导过程中,田松发现,有的新兵写了个姓名、出生年月和性别后,就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了,查了一下至少有三名。
最后没办法,田松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只好由“辅导员”升级为“书记官”,如实地帮那三名无法被“辅导”的新兵记录他们的情况,结果有一位名叫韦通的黑龙江籍新兵,田松问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憋了半天也说不上来,在田松“篮球、足球、唱歌”以及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循循善诱下,他终于急中生智,嚅嚅着的嘴唇突然张开大叫一声“赚钱!”,然后呼出了一口气,仿佛得到了什么解脱一样。
田松越来越自然的诱导声就像紧急刹车一样顿时停住,其他的新兵包括唐班长在内七双眼睛的目光“刷”的一下就向田松和韦通聚焦而来,田松感觉自己的头皮像被夏日里9点多钟的太阳光刺挠着,而韦通,本就有些泛红的脸上又有了一层红色弥漫开来……
通过辅导填写新兵个人信息表,田松知道了本班所有新兵的名字,张由、刘起生、马良(住排部的小胖子)、赵大军(住排部的)、潘金岩、韦通、王正武、潘晓松。
据可靠消息说,这一周就二连休整,一个是让大家适应一下,给家里写写信报个平安;另一个就是还有部分女兵没到齐,不好统一组织训练云云。
这些消息也不一定是空穴来风,因为楼下一连的新兵已经不休整了,有的在练习叠被子,有的在练习站军资。
到了第三天,二连有些人也已经主动地在压被子了,不过都是在自己的床铺上,没有像一连那样直接放到走廊上压(要想叠成豆腐块一样的被子,把被子先压结实是基础)。
田松班上今天好像约好了一样,大家都在压被子,住下铺的由于脚站在地上能多受点力,所以压被子的动静很大,弄得整个床铺都在摇晃并随着压被子的节奏发出“哐铛铛——哐铛铛——”的声音。
但也有偷懒的,不仅田松班上,其他班的包括一连在走廊上压被子的个别新兵,有的是压了一下后发现别人都在忙,没人注意到他,于是出工不出力地“摸”几下被子,一有动静马上恢复正常;有的则基本以“摸”为主,除非干部或班长注意到他了,他才像被紧急启动的马达一样疯狂运转一下,至于达到了什么效果,只有天知道了。
“班长好!班长好!……”田松和其他同志一起迅速站起来大声喊道,由于第一天刚到的时候有些大意,头撞到了铁床档并起了个包,到现在还没消掉,所以自那次以后田松都是小心为上,再也没有碰到过头了。
“你们继续!”唐班长推开门后走了进来,他是到排部去看看马良和赵大军压被子的情况的,据说孙排长老不在房间,所以那个房间的“杂牌军”们“摸”被子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二连的四个男兵班长经协商后采取了轮流去“指导”的方法,才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
“是!”经过数次磨合,大家的回答基本上能达到异口同声了。
几天下来,田松这些“白菜”们经过初步的“加工”,已经知道了见到领导和班长要立正问好,他们要是到班里来,包括自己的班长,站着的要直接立正问好,坐着的或做其他事的要起立并立正问好。
不要跟领导和班长抢道走,也不能与他们争论、解释以及争抢水龙头等,就是在厕所里也要让他们优先,自己无论有多急也要全力忍住,做到“宁可待会换短裤,不让领导不舒服”。
如果有什么事要暂时离开班长指定的活动场所,那么必须请假,回来后要打报告销假,如果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回来后一定要如实报告。
大楼里热水供暖效果很好,再加上大家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所以不管是房间里还是走廊里温度都很高,洗漱间和厕所也是一样。
压了一阵子被子了,尽管已脱掉了棉衣和作训服外套,田松还是浑身冒汗,尤其是裤裆和腋下,像是有三盆火在那儿烤,看看其他人,估计跟他差不多,一个个脑门儿都是亮晶晶的。
这会儿趁着班长进来,田松和大家一样借“礼节礼貌”时机歇口气,所以响亮地答“是”以后,大家都不是继续压被子了,有拿军用大牙缸倒水喝的,有请假去厕所的,反正是想了各种办法让自己缓缓,散发散发越来越多的热汗。
田松跟潘金岩、韦通一起请假去厕所小便,厕所在内走廊的东头,而二连男兵四个班在内走廊的西边。走廊两侧分别为一、三、五、七、九班和二、四、六、八、十班,单数的房门朝北,双数的向南。
所以,田松他们一出门右拐就要经过所有的女兵班。因为在第二天晚上有某个男兵穿个裤衩且因尿急高搭着“帐篷”急匆匆地去上厕所,结果成功的引起了一名也去上厕所的女新兵响彻楼道的高分贝的尖叫后(也不知道是因为惊讶还是惊吓,反正声音大的把一个连的人都从床上惊醒,而据说那位“去不逢时”的新同志的尿意也被吓回去了大半,最后到底上没上厕所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领导要求不管男女不管何时去上厕所,都要把衣裤穿戴整齐,帽子可以不戴,脚上必须要有鞋,就是拖鞋也行。
因为这,田松穿上外衣并认真地检查了一番,确认上衣扣好了下面的“大门”也关好了才出去,这一耽误,就比潘、韦两个要慢了些。
一出门,田松就发现潘金岩和韦通早跑到了厕所那里并往里进了,一前一后两个后背一闪就没了人影儿。
“还挺快的。”田松不由得自言自语了一句。
田松刚走到五班门口,就看见五班的门突然打开,然后一名齐耳短发的女兵走了出来,紧跟着里面响起了“班长慢走!”的一片女声。
由于太过突然,虽然田松已经紧急刹车了,但还是差点撞上这名女兵班长,结果把双方都吓了一跳。
“班长好!”反应过来后的田松立即大声问好。
本来到此也就罢了,可是田松觉得刚才可能“冒犯”了这名女兵班长,所以问过好后他就用自我感觉比较得体的微笑站定在那里看着她,大概想用“此时无声胜有声”来冲淡一下刚才的“冒犯”吧。
就是这一“画蛇添足”的举动,让田松这个下午都处在了“煎熬”之中。
这名女兵班长先是被田松吓了一跳,又被田松“班长好!”的叫唤声当面“震”了一下,现在还被田松这种在她看来十分欠揍而又“放肆”的微笑注视着,顿时觉得自己作为新兵班长的权威受到了一名小新兵蛋子的挑衅。
于是,她浅浅地淡笑了一下。
结果这一笑被田松看成了他的举动起了效果,心里不由得舒了一口气。
“哪个班的?”
“报告班长,三班的!”田松赶紧收起了微笑,一本正经地大声回答。
“好!隔壁的。”
“是!”
“郭班长,怎么回事?”这时候,唐班长听到动静走了出来,向这位女兵班长问道。
“哦,老唐,没事,我觉得这个小家伙需要操练操练,你不会有意见吧。”
“嗯?田松怎么了?”
“他莫名其妙的看着我笑,比较放肆。”听到这话,唐班长转过头来,很是意外地看着田松。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田松还不知道这位姓郭的女兵班长为什么会对他笑一下还貌似关心地问询他的一些问题,那真可以打一脸盆水跳进去淹死算了。
“对不起……,郭班……长,唐……唐……。”田松的声音细到后面像发育不良的蚊子。
唐班长很有意味地看了田松一眼,仿佛在说“你小子自求多福吧”就回班里去了,进去前对郭班长说了句“你随意吧!”
“班……”听到自己的班长这么说,田松额头的汗“噌”的一下冒了出来,“班长”两个字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就见唐班长进了房间并关上了门。
“班什么班?!”
“是!”
“你叫田松?”
“是!”
“胆儿挺肥的。”
“是!啊,不是,报告班长,我胆瘦,不是,是胆小。”
“咯咯咯……”郭班长忍不住暴发出一串银铃声,然后突然又像六月天气一样迅速绷起了脸,向五班门里大叫一声“赵春红!”
“到!”随着一个好听的女声,一名面色红红的女新兵跑了出来站到郭班长面前,房间里还隐隐约约地传出一些低低的柔柔的窃笑声。
“去把我床头柜抽屉里的针拿两根来!”
“是!”那个叫赵春红的答完后返身就跑,返身时与田松照面的瞬间,她抿着嘴对田松报以幸灾乐祸的一笑,虽然田松心里五味杂陈,但他觉得那一笑啊还真是挺好看的,让他稍微有点儿愣神儿。
“田松!”
“到!”
“去服务部买副扑克。”
“是!”田松条件反射一般回答并转身,但马上又返过身来问:“报告班长,我要不要向我们唐班长报告一下?”
“不用!”郭班长忍不住想给田松一耳光,不过看他那样子不像是故意调侃,让她升腾起的一股火没发出来,但从那被军装裹得严严实实的胸脯随着呼吸一动一动的频率来看,她被气得不轻。
“是!”田松撒腿就跑,早忘了自己上厕所的事,甚至因为紧张,他连潘金岩和韦通什么时候从厕所里回来的也没注意到。
那天下午,是田松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下午,他把扑克牌买来后,郭班长还让他将他自己的棉帽拿出来并且翻过来让他顶在头上,同时,让他挺胸收腹提臀收下颚呈立正姿势站好,背朝墙但不准靠墙,身体稍向前倾约15度。
为了让他的脖子挺直且不能随意活动,赵春红拿来的那两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被郭班长刺过田松下巴两侧的衣领,让针尖抵在了脖子上。
为了让田松两腿保持竖直,两手四指并拢、拇指贴于食指第二节紧贴在大腿两侧,那副田松自己买来的扑克牌派上了用场,郭班长只用了六张扑克牌,即田松的两膝之间夹住了两张,两手中指尖与大腿接触处各放了两张(中指尖仅按住两张扑克的上沿中部,两张扑克的大部分在下边垂着),就让田松一下午都“定了型”。
为什么每处要用两张扑克而且还要新买的呢?这个问题田松站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后来才知道,新兵按照上述标准被罚站一段时间后,身上会不断地出汗,过不了一会儿汗水便会从里向外透出来,如果用旧扑克,透出来的汗水很快就会让扑克潮湿,这样被罚站的新兵不需要用多大的力就可以保证扑克不掉下来,特别是两手出汗后,中指尖的汗水能将一到两张旧扑克牌粘住,而新扑克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除了不容易吸水外,两张扑克牌之间还非常光滑,摩擦力很小,稍有放松里面的那张扑克牌就会掉到地上。
由于田松站到吃晚饭前才被“解冻”,期间,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兵都被动地“认识”了他,所以在他所在的新兵二连一下子就出了名,许多连班长和排长都没认全的新兵,都知道他是谁,甚至在楼下的新兵一连中,他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因为他下楼经过一连的走廊口时,后面就有一些一连的新兵对他指指戳戳并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着。
田松“成名”后,随后的几天里,因为他进一步的小心谨慎起来,再加上所谓的“名人”效应,倒是相对安全平稳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