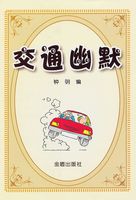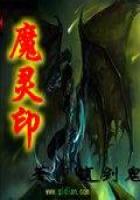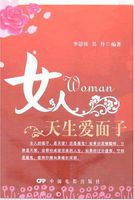谢天开
摘 要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四川交通近代化从经济技术层面上引爆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并也在此层面运作了此次事件。四川保路运动的表面为地方与国家路权的博弈,在深层次上则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调适,而且也与川人的蜀道集体记忆相关联。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大波》作为“大河小说”则是为信史,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从心态史、物质文化史、民俗文化史,尤其是在四川交通近代化等方面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关键词 交通近代化 保路运动 信史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无论是被誉为“反映时代的超长篇小说”即“大河小说”,或是历史小说,都可以看做为一部鸿篇巨制的“信史”。
戴执礼主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为记载辛亥史实的权威著作,其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引用书报目录”专门提及“《大波》,李劼人撰。描写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小说,民国二十六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三卷,三册”。
其中引证资料:
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1]273
宣统三年七月一日(1911,8,24)
(一)勿在街头群聚。
(二)勿暴动。
(三)不打教堂。
(四)不得侮辱官府。
(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能守秩序便是公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
——《大波》卷上,第二四六页。一九三七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该书系章回小说,李劼人撰。
如此一部权威的史料专辑,而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为史料引用,这是极为罕见的。
作为互证,在《李劼人晚年书信集》里:“致蓝子玉一封(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中称:
以为我颇熟悉前川汉历史,事实殊不尽然。我比较熟悉者,为争路事件,而于川汉铁路本身历史,则知之甚少也。关于此项记载,我所收集抄录虽有若干,然于公之编写,都无裨益。兹特介绍二种文件如后,庶几略有帮助:
一、《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前川汉铁路公司主任管事彭兰棻于民国二十二年撰印;
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戴执礼一九五九年篡辑,科学出版社印行。
前书大约不易求得,我处尚存一册,可以奉借。
戴执礼为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专家,其编修是极为严谨的,而将《大波》作为引用文献,这足以说明《大波》作为信史的价值所在。况且,戴执礼还在其书后记中道:“本编承李劼人、刘培芝、李元伯、舒群实先生供给一些史料,并校阅了部分稿件。”这也间接地说明,作为小说家的李劼人是极为重视史料的收集与参考的。
作为信史的《大波》由于文学的丰富性,也可以视为当时那个社会时代的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交通近代化史等等。
为了集中与方便,本文主要论及与四川保路运动相关的,辛亥四川交通近代化的状况,主要指铁路、水运与电话及电报。
什么是交通,按《辞海》(1999版)释词:交通,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即人和物的运转与输送,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的传递播送。对此条释词最好的诠释互证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清政府推行官制改革中,谕令设立邮传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名为邮传部。
《大波》里现代交通主要为船运与铁路及电报和电话。在这样的描述里既突出了保路运动的四川历史地理文化背景,也写出了蜀人对蜀道天堑变通途的惊惧与期盼;如此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置于更为广阔的国家历史地域文化的背景之中。
一、川汉铁路与蜀道情结
1903年,清王朝拟定修建川汉铁路,从四川成都经重庆到湖北汉口。
1909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率领人马集结宜昌准备修建川汉铁路。同年10月,宜昌至秭归段曾一度动工修建。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废除商办法案,然后向外国列强借债修路,出卖路权,引发了四川人民针对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保路运动,可以看做一场借洋款筑路的清政府中央政策与四川咨议局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且四川的城市精英与下层社会民众都一致地视保路为保川,进而为保国。殊不料竟成为一场百年的铁路梦想。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朝李白著名诗句成为川人对蜀道的集体记忆。四川保路运动除了川人的蜀道情结之外,更有对近代交通的渴求,即为交通速度的企盼。
这样的企盼在《大波》里,分别描述提及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铁路。
沪杭铁路,实际上就是沪杭甬铁路[4]231,自上海南站起,经松江、嘉兴、杭州,然后跨钱塘江折而东行,经绍兴、曹娥、余姚,最后抵达宁波,全长357.03公里。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城际铁路,分段施工,1909年5月沪枫段建成,同年7月杭枫段也建成。描述这条远在江南的城际铁路,很容易让联想到当时的成渝铁路。而在《大波》里,也专门将川汉铁路与成渝铁路做了容易与艰难的经济与政治成本的比较。
京张铁路[4]64,是大清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修建的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1905年5月,清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采纳了直隶总督、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的建议,决定不靠外资,不用洋匠,利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建京张铁路。同时决定设立京张铁路总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
川汉铁路最初的操作,无论组织机构、所聘用的技术人员,还是资金的筹措,都可以说是以京张铁路为蓝本参照并有所改进的。在《大波》里,以京张铁路明喻了川汉铁路的修建难度。以京张铁路衬托川汉铁路,也是铁路自建的民族主义保路保权的地方自治宪政思想的社会民间诉求。
戴执礼主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集有《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宣统三年七月一三日(1911,9,5)》史料;成书在前的李劼人所著《大波》亦引用《川人自保商榷书》[5] 第一部341:
(十)铁路。(十一)轮船。说明:铁路务在先修成渝,辅以川轮,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开门揖盗之虞。宜夔一段,则宜量势渐图。至于铁路所需材料,为四川富有,取之无穷,如铁轨、木枕、石炭等,既办炼铁制材两厂,即可渐次不购于外,而人工尤以四川为最廉,甚则或可以工代赈。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朝大诗人李白诗句,应当为蜀道水路与陆路艰难的双重比喻而成为川人关于交通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
四川独特的交通地理,除却西北秦岭的雄伟之外,更有东南长江三峡之瞿塘峡的峻急、巫峡的雄秀、西陵峡的开阔。百年前长江三峡地理空间如此奇特雄险,浩浩汤汤,深刻影响了川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从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大波》,到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洪波》,再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无一例外的都以此为描述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重大借喻。
二、蜀通轮与历史文化隐喻
(一)蜀通轮的出现
清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七日(12月29日) 蜀通轮由沪抵渝,这是峡江航道上行驶的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的第一艘客货轮船。时有当地绅民“穿衣顶帽倾城出现”,欢呼国人自营轮船第一次入川抵达重庆。
1907年在中国航业史中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这年年末在重庆由四川官商合办发起创办了一家“川江行轮有限公司”,而且居然是由赵尔丰的胞兄、当时的护理川督赵尔巽委派四川商务总办周善培及川东道陈遹声创办的。
向英国订购一只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蜀通”号轮船(总吨数196吨,载重80吨,机械动力600匹马力,时速13海里半,拖运为时速11海里),及一只拖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统舱可容一百数十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坞组装完毕,开始航行。[6]410
蜀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浬,从宜昌到重庆只需65小时。
然而,快捷的蜀通轮初航不久,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从中作梗,借口川江行轮容易碰撞民船占夺民生,和将引导外国轮船接续航行等,横加阻挠。一面要求清廷制止,一面电达四川总督,不准蜀通轮进入湖北境内。后经多次调停,订立免碰章程十条,赔偿章程八条,又向宜、渝两关各缴存押款一万两,以备赔偿碰损民船之用,直到1910年3月中旬,川江轮船公司才得营业,蜀通轮往返水路在宜(宜昌)渝(重庆)两地,这是作为经济行政技术层面关于“蜀通”号轮船的表述。然而作为文学的描述,《大波》开篇:
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激,丢一件浮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
机器仓、煤仓占了轮船本身一多半。机器的轰隆声特别大。火仓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嚓嚓地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在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轮船不同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而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两部。舵也一样,主舵外还有两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
……
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即是从那个英国籍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水手。一百多位旅客,则全部挤在用钢绳绞绑在轮船左舷的另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仓船中间。[5] 第一部3
《大波》 虽说是以川汉保路争路为中心,却以大量笔墨描述峡江的水路,并以此为文学隐喻那一场波澜壮阔的辛亥保路死事运动。
《大波》关于西方的现代轮船绞绑中国铁皮包裹的木仓船的文学描述,表现出文学的歧义性与多义性;让人联想到晚清的洋务运动,一场西方世界工业社会对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的胁迫,改良是由外部引起的;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当代历史学家唐德刚提出的中国“历史三峡观”。
(二)蜀通轮与辛亥三峡水运
1.蜀通轮的社会影响。
1910年3月蜀通轮正式定航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二次。这是三峡川江有史以来定期航行班轮之始。
《大波》中借周孝怀自我表白,说明了蜀通轮在清廷地方官员心目中是列为首要政绩的,也为四川的交通现代化的象征[5] 第一部238。
《大波》[5] 第二部289借一个制伞匠之口,还表述了当时民间社会对峡江水路运输的一般陈旧概念,反衬蜀通轮对于四川交通现代化的重要性:
一个时候,他硬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从早到晚都在打听岑春煊的消息。消息得不到,就四处问人,由上海坐轮船到宜昌,要几天几夜?由宜昌坐民船到重庆,又要多久?(虽然蜀通小火轮已在川江行驶了两个年头,但一般人尚未把它摆在脑子里,只要说到川江交通,大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靠纤绳牵挽着逆流而上的木船。)
2.蜀通轮的政治关系。
《大波》[5] 第二部338蜀通轮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赵尔丰还有另外一种为别人所不及知道的忧愁,那便是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的重大事情。
这封密电报,是他派去迎接端方的候补道谢廷麒,于八月二十二日,端方由万县乘坐蜀通轮船到重庆的这天,他探闻之后,立即打出的。
电报由赵老四亲自译出,送到赵尔丰跟前来时,老四还从容不迫地说:“武昌革党起事。”
此段描述,可以窥探出当时四川的交通,蜀通轮的水路消息与电报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
《大波》[5] 第三部45对端方入川到重庆时,在朝天门码头摆排场的政治作秀,以起到震慑官民的作用,也是通过蜀通轮来完成的。
3.蜀通轮的军事作用。
这是历史的吊诡。在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期间,清廷钦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步队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全标及三十二标之第一营(缺两队)官佐,共约二千兵力,于1911年9月15日起程武汉,向四川进发。
作为运兵的蜀通轮其军事作用属于清廷的“命门”,无奈偏偏又遭到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员们焦急万分,于是清廷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为此驰电频繁。
《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宣统三年七月(1911,9)》[1]322;电文中称:
端方连日赶办公所要件,并布置入川事宜,确已就绪,即日乘轮赴宜昌。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屡电饬令设法出浅,迄未办到。如由宜遵陆,约须经月,始达成都,殊嫌迟缓。
《瑞澂致盛宣怀成都情形危急鄂军到渝须有二十余日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一日(1911,9,13》[1]339电文中亦称:
至鄂军赴川,由汉乘轮至宜昌后,须看有无入蜀轮船,临时定夺。即有轮亦不能一批齐进。计舟行至万县,由万陆行至重庆,最速须二十余日左右,方可抵渝。
由于搁浅,致命的蜀通轮,让邮传部大臣、四川保路运动始引发者盛宣怀乱了方寸,而向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询问办法,遂有《盛宣怀致赵尔巽鄂军援川缓不济急四川何军可靠由陆军部电调进援成都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二日(1911,9,14)》[1]344、《盛宣怀致瑞澂成都绝援恐生奇变请赶运鄂军千人足可镇慑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二日(1911,9,14)》[1]339,电文语气几乎恳求:
资州电局二十一来电,成都十六闭城,……等语。若无外援,恐生奇变。鄂军总须设法用轮船分送。客军枪队,只须千人,便可藉资镇慑。此外有无良法,乞裁示。请转午帅。
《瑞澂覆盛宣怀川事除催援军星夜进发外别无他策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二日(1911,9,14)》[1]344电文又称:
鄂军入川,由宜而上,有轮亦只能抵万县,昨已电达。迨舍舟登陆而后,蜀道崎岖,有只容一人侧身而过者,无论如何,总属缓不济急。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端方所率鄂军水路入川,有无可行轮船,已成为军事上的最大瓶颈。而且在川的赵尔丰也利用此事向朝廷中枢建议另选几乎不可入川的岑春煊入川来查办路事,致使盛宣怀从中调协,遂有《盛宣怀致端方清帝已派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与其查办路事各不相碍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三日(1911,9,15)》[1]350,电文还询问:
蜀通何日修好,请饬查电示。
对于此重大的决定各方生死攸关的历史细节,作为信史的《大波》[5] 第二部236通过蜀中士绅的议论,专门点明了蜀通轮的军事作用:
“其实蜀通就不搁浅,端午桥还是会迟迟其行的。因为蜀通体积很小,我问过,充其量,一次只能装载二百多人。端午桥带的湖北新军一标之众,加上军需、军械、军粮,蜀通也委实载不完,仍然要用民船载运。川江的上水船,你们大概都知道,从宜昌到重庆,不走二十天,也要走半个月,而且凶滩恶水,危险万分……”
在《大波》[5] 第三部57又强调因为湖北兵轮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蜀通轮为长江上水唯一能运兵的轮船,可是偏又在忠州地面搁了浅,不能及时出险。
尽管四川保路运动局面复杂,各方面利益纠缠与阻碍,而蜀通轮搁浅这一偶然戏剧性的几乎改变了辛亥历史进程的细节,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仅率十几个随员,和几十挑古玩字画,带领少数卫队起旱,由水路改为陆路,其余人员、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拉上去。蜀通轮的意外搁浅,致使端方所率鄂军精锐延误至1911年10月5日抵达万县,10月13日到达重庆,11月下旬行驻资州,再至11月27日鄂军反正革命军诛杀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此时距离1911年9月15日从武汉起程已有两个多月之久,其间已爆发了武昌首义,成都围城,遂使四川保路运动大势成为燎原。
(三)四川水运交通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调适
1.对外国兵船心存戒惧。
身处辛亥年摇晃的中国,对于蜀通轮的搁浅,尽管清廷大臣们都力主外国势力介入,而清廷中枢却对借用长江上的外国兵轮心存戒惧。
时有电报可以证明:
《盛宣怀致电端方嘱借英国兵轮入川吴士已奏请川路改道由陕入川交阁议准令邮部查勘电宣统三年七月一六日(1911,9,8)》[1]322;
《瑞澂致电海军部请派兵轮赴宜昌、重庆保护中外商民电宣统三年七月一六日(1911,9,8)》[1]323;
《清帝令端方勿借用英国兵轮另行设法入川谕宣统三年七月一八日(1911,9,10)》[1]323;
《海军部通知萨镇冰允瑞澂就近调派兵舰并令沈统领派舰赴重庆电宣统三年七月一六日(1911,9,8)》[1]323。
2.成都少城公园船房的文化隐喻
他们在园里缓兜了一个圈子,来到那真正船房跟前。邓乾元指着那砖石砌的尖锐船头,和盘在石桩上的一条手腕粗细的生铁链,慎重其事地道:“硬是一只火轮船啦!去年中秋,我在宜昌看见我们川河头一只火轮蜀通,并不比这大多少,样式也差不多。……看!那楼顶上还有桅杆,还有烟囱!……”
岂只有桅杆,有烟囱,甚至楼房正面还悬了一块匾额,绿底粉字,题着“长风万里”。
船房的楼上楼下也在卖茶,并且看见有人在吃面条,在吃包子,一定还兼带卖点心。
两人正在商量要不要就在这里喝茶,忽然听见背后不远处有人说话。
“好恶俗的东西,真杀风景!我每回看见,总不免要打几个恶心。”
“为啥不模仿中国的楼船,偏要模仿洋船?又不像。我看见过洋船照片,楼顶是平的,还有铁栏杆,怎么会是两披水的人字顶,而且盖上了瓦,不晓得是那个人的手笔?”
“自然是那位胸无点墨的满巴儿了。”
“那便不要见怪了。听说颐和园里就造有一只石头轮船,主子做得,奴才正好学得。”[5] 第一部97
《大波》对成都少城公园船房中西结合的风格作了描绘,以此表明社会民间对于近代交通给四川这个中国内陆省份带来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调适下的种种心态。
自此,《大波》对于蜀通轮狭义的纪实文学隐喻已转化为广义的历史文化隐喻。
而《大波》作为“大河小说”,按李劼人的最初设想,将写到“后蜀通轮”时代的,那么极有可能写到即同为中国少年学会会员、李劼人在实业界的同行卢作孚与他的民生轮船公司了,当然这是另一部关于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鸿篇巨制了,可惜天年不假我们的文学巨匠。
三、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有线电话与有线电报
(一)有线电话
清末,由于邮传部的经营权限所在,有线电话的设置往往与铁路同行。又因为地方民众的近代交通知识的缺乏,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没有出现破坏电话线的事件。反而,地方政府对有线电话的使用相当畅通,有线电话唯作军事之用。[5] 第二部282
(二)有线电报
光绪六年(1880)八月李鸿章奏明朝廷,请旨创设中国电报局,分别官线、商线,委派盛宣怀总揽其事。自光绪七年(1881)至清末,全国大小都邑遍有电线,实达六万四千余里,可谓近代化程度在当时中国各方面实业之上。[7]309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有线电报的使用,除与京畿往来之外,由于鄂与蜀的关系密切,使用得最多的是汉口—沙市—宜昌—夔州—重庆—泸州—成都这条重要商线,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条商线亦为光绪十一年(1885)盛宣怀借官款经理创置的。
在电报往来中,作为“汉口—成都”商线“被官方作派”习气严重,地方官府多次无理扣压地方士绅电报,从而控制通讯。[5] 第二部211、242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官方的有线电报,因成都围城而电讯中断,与清廷的电报联系全由资州电局承担。遂有《盛宣怀致瑞澂成都电讯中断电宣统三年七月二○日(1911,9,12)》[1]338、《资州电局呈清廷各部述成都战争情形电宣统三年七月二一日(1911,9,13)》[1]338。
(三)“水电报”
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5] 第二部67
为了打破官方对电报通讯的垄断,在辛亥保路运动中,保路同志会居然在偶然的条件下发明了具有戏剧性的杉木牌“水电报”,并且借着百年前的成都锦江大水发至全川。
四、结 论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四川交通的近代化从经济技术层面上触发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并也在经济技术层面运作了这次事件。四川近代交通兴建的资本运作——集股与借贷: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形成了川汉保路权的利益共同体:地方士绅与民众的合力,以此而共生的地方自治宪政思想也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遗产。
四川保路运动表面为地方与国家路权的博弈,在深层次上则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并与川人的蜀道集体记忆相关联,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调适——四川地域历史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显现。
在辛亥年间,四川的近代交通尤其是蜀通轮搁浅的小事件,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重大细节,也让四川保路运动大势燎原而转变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参考文献:
[1] 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 张雨才编著.中国铁道建设史略[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
[5]李劼人.大波[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补白:
某日,张义奇先生手机告示:拙文《〈大波〉四川交通近代化》所引注的“李劼人.大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存有陋误:1958年,人民出版社根本未曾出版过李劼人著作,况且《大波》尚未写完,何来出版?
起初,还窃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可能出现如此低级之误。后来查阅李眉所订《李劼人年谱》:“1958年3月,《大波》上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0年重印时,《大波》上卷改为第一部,取消《关于重写〈大波〉》)。”
如此,虽证实了张义奇所指非谬,却于我有些迷惘:为撰写拙文特购此套布封精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本[在1册上印有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印数1—4000册,定价99.00元(全三册)],而存在如此瑕疵。
不过,又转念一想,作家出版社亦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离出来,彼此存在某种谱系,前者如此标注,也属于一个版权的学术存疑。
但愿如此,否则难以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