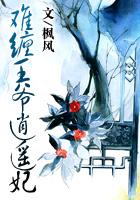“那除了你们之外,没人尝过这酒,也没人听过这名字吧?”
“嘿嘿!除我们之外,这酒也有人尝过,听过名字的也却不在少数。那一次,大师兄在江上漂了几天,有一个摆渡的老头见他看起来似乎很落魄,可能还生命垂危,所以一时善心大发,就把他拉上船。
“正要救治他,大师兄刚好就醒了,大师兄一时酒瘾上来了,就和那个老头一起拿葫芦对饮,半葫芦酒喝了个精光。那个摆渡老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以前喝过的好酒自然不少,可是跟大师兄分别之后,他对喝酒再也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在他眼中再也没有好酒了。
“后来他又遇上一些要过江的江湖人士,他们拿随身买来的美酒送给他喝,岂知他才喝了一口就还给他们,说这酒没味道。那些人说这是上等的高粱酒,乃人间极品,恐怕他这辈子也难得喝一回。老头说他曾喝过比这高粱酒滋味胜过百倍的好酒,所以这酒如今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奇天云好笑道:“他们见这老儿如此大言不惭,定会教他把他说的那种酒拿出来比较一番的,这样一来他们岂不是更加确信他是大言不惭?”
波浪子也笑道:“嘿嘿!他们刚开始也说他大言不惭,不过后来摆渡老头便带他们到他家去品尝,大师兄后来光顾他的渡船时送给他的酒,他们喝过之后也说自己以前喝的酒简直差太远了,结果还想花银子再喝几口呢!”
奇天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向他问道:“差点忘了,你大师兄失踪的那段时间,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你们找那么久也寻不到他的行踪呢?”
“说来也真是凑巧,”波浪子语气中不无感慨,“那天他沉入河中,沉到一半时,竟有一股潜流把他一直往下拉。本来他已深受重伤,运功疗伤之际,还要分心潜运胎息之术,以免窒息而死,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让自己往上浮,更没法应付水下的潜流。所以他只好任由潜流把他往下拉,任由自己的身体在下面翻翻滚滚,不去加以理会。也不知道他在水中到底翻滚了多久,不过庆幸的是潜流并没有让他一直待在水下,而是让他漂出水面,他在水面上漂了好久才睁开眼睛醒过来,结果发现身旁是一个无人荒岛。”
“唉!真是奇遇啊!换作是我,可能真得会淹死的。”奇天云叹道。
“嘿嘿!奇遇还在后面呢!你不知道,那股潜流拖着大师兄在水下载浮载沉,大师兄无力反抗,只好完全不作抵抗,让自己的身躯随着水流的形势流转,结果没想到这样做,却于他疗伤大有裨益,那股潜流的力量大得出奇,恐怕任何武功高强之人若要诚心与它相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浑身四周都是水,无处着力,却不断地有一股力量将他往上抛,或是往下拉,或是往前牵扯,由于他丝毫不使抗力,这股力量就自然而然地化作他自己的体能。这好比一位武学高人将他在空中不停地用力抛来抛去,并将抛掷时他身上自然产生的力道全注入他的体内助他疗伤,这样,他身上的伤,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大半。
“师傅听他这样说了这段疗伤的经历后,就叫他以后继续照这样修行,所以大师兄现在经常在水上睡上七八天,任凭水波将他带向哪里,他都不去理会。”
奇天云摸摸脑门,还是不大明白,“可是这只是疗伤的方式啊,那他不用练功吗,就这样睡在上面上?”
“他这样不就是在练功吗?”波浪子见他不解,只好简单解释一番,“他将潮起潮落、波涛澎湃的力量化作自己的功力,将风浪起伏流转的方式纳为自己的招式,这怎么不是在练功呢?而且他并不总是在水里修行,有时候也会去天上转悠一阵子,久而久之,他已经再不用剑了。所以,他现在不管与谁交手,基本上都可以空手对付。”
“哦!明白了!”奇天云刚明白了这一点,马上又被另一个问题缠住了,“那你师姐说什么她害大师兄受伤,还害他差点丧命是怎么回事啊?”
“咳!”波浪子忍不住笑了,“大师兄从小就很厌烦师姐,那年他武功稍有成果就急着下山去寻访他的恩人和仇人——”奇天云打断他道:“恩人和仇人?”
波浪子点点头,“在下山之前,大师兄曾开玩笑地说,从此以后终于可以不用再见到师姐了。而师姐因为这句话一直耿耿于怀,她还真以为大师兄那么急着下山是为了避开她呢,所以当大师兄出事之后,她老是责怪自己不该让大师兄这么嫌弃,以至于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奇天云恍然道:“如此说来,你师姐岂不是对你师兄一往情深?”
波浪子道:“那是自然,师姐虽然比我们早上山,却是我们中最小的,我们上山之前,她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呢,那时师傅在外奔波,所以大师兄算得上是她半个奶娘了。好了,不跟你扯了,我也要去寻她了,真怕她闹出什么事情来,奇兄,这就告辞了!”他起身一抱拳,转身就走。
奇天云也站起来,瞧了瞧已降临的夜幕,忽然想起什么事情,忙叫住他:“波浪兄先别走啊!”
波浪子诧异地望着他,正要询问,忽然笑了,“哈哈!差点忘了,于大捕头还不能动弹呢!”几步走到于彩瑶面前,低下头道:“于姑娘,你今天收获可不小呢,将你的对头的底细知道的一清二楚,你该怎么谢我呢?”说着不由分说地扳起她的身子,伸手在她背上拍了几下,便顾自上路了。
看着于彩瑶慢慢从地上站起来,奇天云便打算踏上漫无目的的征途。
才走几步,就听于彩瑶叫道:“喂!你叫什么?”
奇天云愣了一下,没有回头,“在下乃无耻之辈,说了怕脏了姑娘的耳朵!”他走地很轻快,好像随着波浪子说出了心中的难言的往事,他自己心中的沉重不知不觉间也减轻了许多,从未有过的轻松。
于彩瑶看着他渐渐离去的背影,回过头又眺望了一眼西边最后一道隐没的阳光,四周空荡荡的,只剩下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