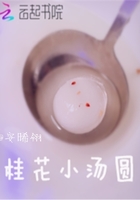连续好几个夏天,父亲都没有提起送我去大伯家的事情。我一直等待着,我想念大伯,想念文丽,甚至于,想去那个农舍看看,那些小狗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于是,我没有继续沉默。我对父亲说,我想去大伯家。
父亲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在看杂志,在研究他的新投资。
我只能重复,我要去大伯家。
他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皱了下眉,说,不可以。上次已经给他们添了那么大的麻烦,文丽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还不够吗?我坚持着,丝毫没有退却。
父亲没有说话,用眼神向母亲示意了些什么。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饿了,去吃点什么吧—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充当着保姆的角色,而非父亲背后的女人,或是教育我的母亲。
我没有动,还是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父亲。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我先和你大伯商量一下。
我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走出了书房。我相信大伯一定会让我去的,他是那样喜欢我。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父亲开车送我去大伯家,门口的植物都调令了,菜园里也长满了杂草,和记忆中的样子相去甚远。我丝毫没有感到失望,而是飞快地跑进大伯的房间,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大伯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瘪的老人,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身体的起伏即将平复在这张冰冷的床铺上。当我吃惊地看见他时,他也看到了我,他伸出手向我召唤,我认出了他的声音,是大伯……
半年前,他倒在了床上,疾病使他完全变了模样,文丽已经被送到了城里读书,只有伯母偶尔回来看看他。他固执地留在这里。这里空气新鲜,而且,他在这里长大。他坚持己见,不容许任何人改变。
“老子……”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
他那干涸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不住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动作是那样无力。
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那个在少年时,为我擎起一片天空的肩膀,已经单薄地随时像要垮掉。
“小子,你还害怕吗?”大伯的声音很微弱。
我却感到非常刺耳。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明白。
“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他的眼睛那样慈祥,“文丽没有看见的那个。”
那一声凄惨的叫声再度在我耳边响起。我惊恐地像要捂住自己的耳朵,却被大伯紧紧地抱住:“谢谢你,是你保护了她。”
一句迟到的感谢,滋润了我的眼睛,扑在大伯的怀里,纵情地大哭。
大伯的手臂却失去了将我抱进的力量,他只能不停地在我耳边重复着:“都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
大伯没有看见第二年春天,没有看见那一树树白玉兰,白得如此高洁。
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