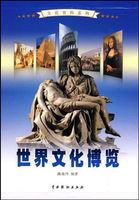奢厉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想不到这马族仅以如此轻便简单的披风便能制伏六浊中的汗狼。
果真是兽不可貌相。
汗狼想伸出爪子去抓破披风,然而自己的头却被控制得死死的,每每手刚触到颈部,便被黑马将披风一拽,牵扯得手不能近前,汗狼仿佛像一头拉磨的兽一样,被蒙着眼睛围着黑马团团转。
看似黑马占了上风,然而他并没有丝毫的得意,他正皱着眉头瞪着汗狼被披风裹住的头。
那汗狼天生爱出汗,裹在披风里的头已把披风的边缘浸得到处都是汗。
就是这样,汗狼仍然喘着粗气挣扎着,汗越流越多。
黑马一脸鄙夷,但仍然拿披风死死控制住他的嘴,怕汗狼一张口便咬破破风。
然而那汗狼绝非这么容易就被控制的兽,只见那黑马身后,夹杂着呼呼的风声,袭来的正是那汗狼的石矩。
原来刚才在黑马裹住汗狼之时,他便松手放出石矩。
那石矩在空中自转着,转成一个圆刃,一个回旋之后,便削向黑马的后脑。
黑马闻声大惊,连忙卸力于披风,以抵挡脑后的石矩,这时汗狼便欣欣然从披风中脱头而出,披风抽打在他的脸上,还是有火辣辣的疼。
在披风抽出的一瞬间,那风中旋转的石矩已经飞到了黑马的后脑,黑马想用披风抽打已来不及,只好一歪脑袋,石矩擦着他的面颊回旋而过。
那石矩在往汗狼手上回旋之时,正好经过黑马抽出的披风,于是,石矩被披风阻止,改变了路线。
黑马见状,也迅速改变了主意,改控狼为控矩,他暗自在披风上使力,想用披风缠住石矩。
哪知那石矩虽然改变路线,但仍旧只是在披风上跳将两下,依然往汗狼的手中飞回。
梆!——汗狼一把捏住石矩,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
黑马狠狠地抽回披风,横在眼前,伺机而动。
一丈二尺又半寸。——汗狼说着,擦了擦滴在石矩上面的汗。
你说什么?——黑马心中咯噔了一下,紧张的问道,其实在问话的那一刹那,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披风的长度。——汗狼说着,又拿手毛去擦擦石矩。
汗狼看石矩的眼神充满着无限的爱怜,相反,汗狼看披风的眼神便显得格外惊异。
被汗狼量出披风的长度,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斗战中,他无论用披风袭向哪里,都会被汗狼准确地预判出落点,从而进行有效的反击。
奢厉这时可以完全肯定汗狼是一名术尊了,他不像白泽那样的术尊一样,可以用术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是通过手中的石矩丈量感应,来预防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眼下之事犹未决,眼外之事他已解。
这是最可怕的术尊,因为一旦被他得到数据,那么他将无懈可击。
奢厉惊讶汗狼此兽的恐怖性质之后,更为惊讶的,便是那石矩在披风上弹了几下,他便知晓披风长度的能力。
果不其然,当黑马试图再度用披风袭向汗狼之时,汗狼招招躲得游刃有余,甚至想抓住披风反制于黑马。
黑马看出汗狼此时已知晓他的所有招式,因而渐渐地开始不用招式,像个疯癫状态的兽一样,乱甩披风,唯以速度取胜。
就是这样,那披风也不能伤害到汗狼的半根毫毛。
只有当汗狼想擦汗时,他会将掠过脸庞的披风轻碰一下,披风柔和地擦掉了他额头上渗落的大颗粒的汗珠。
此举,对于黑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污辱。
黑马攻势更猛,使得汗狼也不能暂时找到进攻的手段,只好依样学样地躲闪着。
五哥!——溃狈在一旁提醒说,快进攻啊!
二哥拿走了我的铁规。——汗狼边躲闪边回答,要不然,我早就刺破他的黑披风了。
黑马怒嘶一声,奋蹄袭来。
咯嚓!——那汗狼终于抓住了机会,于乱舞的披风中握住了黑马的蹄腕。
令奢厉想不到的是,那黑马居然定住了。
看黑马的表情,没有一点痛苦,然而却是满脸惊悸,一定是那汗狼对他施了什么术,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六浊风居轿下,汗狼握在踩在空中的黑马的蹄子,两兽一动不动地静立着,唯有黑马的披风在烈烈地随风舞动着。
吧嗒!——一滴汗掉落在两兽脚下的草地上,迅速蒸发成水汽升腾开来。
那滴汗不是从汗狼颊上流下,而是从那黑马的颊上流下。
这个局面僵持了大概有一弹指的时间,汗狼没有用利爪撕扯黑马的身体,也没有用嘴去撕咬黑马的蹄膀,而是轻轻了呼了一口气,虎口悠悠地张开,放开了黑马。
黑马一个趔趄,往后退去。
退了好几步,终于站稳。
奢厉仔细看着黑马,想看出来他和刚才有什么不同,发现他只是面色有些发红,别无他恙。
黑马又长嘶一声,恶狠狠地甩着披风袭来。
汗狼仍然像刚才一样不慌不忙地躲闪着,哪知他越躲动作越慢,躲着躲着,收起了石矩,竟然站定了身体,不动了。
这是因为那黑马袭击的动作越来越慢,袭着袭着,便向后一退,不动了。
黑马大口地喘着粗气,状态明显不如先前,他此时仿佛顾不得形象,拿披风擦了擦汗,带着哀怨而又未解的眼神看着汗狼。
一仞二丈三尺四寸五分六厘七毫八丝九忽十微暴汗术。——汗狼慢条斯理地吐出一串话来。
什么?——黑马又擦了擦汗,不解地问道。
我是说,——汗狼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道,你中了我的一仞二丈三尺四寸五分六厘七毫八丝九忽十微暴汗术。
会怎样?——黑马问。
你不能靠近我一仞二丈三尺四寸五分六厘七毫八丝九忽十微的距离,否则你会一直流汗。——汗狼悠悠地说道。
那又怎样!雕虫小技!——黑马说着,又甩着披风袭了过来。
哪知这时汗狼不慌不忙地抬起手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阻止的手势,除此之外,连眼睛都未眨一下。
只见那黑马便一扭头去,将披风抽打到自己脸上,疯狂地擦着汗。
奢厉知道,那是汗流到他的眼睛里了。
黑马擦完汗,气喘吁吁地攥着披风瞪着汗狼,许久,又擦一下,问道,你刚才说的距离是多少来着?
一仞二丈三尺四寸五分六厘七毫八丝九忽十微。——汗狼笑笑,说道。
奢厉看到黑马的脸红通通的,再加上黑色的毛发,整个头部,活像烧红的炭。
然而炭并没有冒烟,而是不断地向外渗着水珠。
倒是有些细碎的汗,直接在额上蒸发,成了水汽,达到了和炭一样的观赏效果。
这块黑炭像是被火星溅射了一般,在听完汗狼说的一串数据之后,迅速一个箭步,跳远了。
黑马一个马步,跳出汗狼有两仞的距离,这才重整姿态,准备迎战。
奢厉知道黑马已经没有了机会,因为看来看去,他的兵器便是他的披风,并非像孰湖般有弓箭有射,像赤骥一样有红枫可投,像渠黄般有黄蜂可飞。
因而黑马这个旭客,倘若缺失了距离,便是没有了机会。
被对手看透底牌,必输无疑,被观众看透底牌,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白马和渍豺二兽正斗得不可开交,铿锵有力。
那白马每对击一次蹄掌,便迸出火星,那火星伴随着白烟,一粒粒袭向渍豺。
渍豺个头虽小,却将那兽耳磬舞得虎虎生风,尽数将火星一一震开。
那火星弹在耳磬上,发出有韵律的节奏声。
渍豺看准一个袭来的火星,奋力一拍,火星朝着白马的面门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