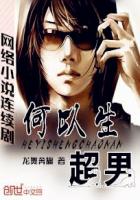“爹!你这般着急找我来所谓何事啊?”张榕慵懒得趟坐在张士钊的椅子上,懒懒的问道。
张士钊一脸严肃,道:“你是不是又做出对不起门风之事了?”
张榕未看张士钊一眼,自顾自地拿起桌上的一杯茶,喝了一口,“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张士钊气急败坏地夺下他手里的茶杯,狠狠地摔在桌上,“还不知错!你在临汾县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只不过将你的画给那人看了,那人第二日便走了。”张榕不以为然道。
“我是说,你对吴寅的女儿做了什么?”
张榕这才反应过来,稍许疑惑地问道:“以往别的女人,你都不会如此上心的,怎么对这个女人,你倒是突然关心起来了?”
“她就在刺史府客房。”
张榕听罢,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哦?没想到她居然跟来了!看来是被我降服了。”
“你最好不要负她!否则!”
“否则怎样?不认我这个儿子?”张榕一脸坏笑,“你这话早已说了无数遍,下回换句新的吧。”说着,他径直往门外走去。
抬头缓缓望向窗外,窗外的夜色如此迷人,天空中无数的星辰围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她低语,“你们是来给我指引方向的吗?”
说罢,她的门被推开,一股浓重的胭脂味道随着风飘入室内,张榕迎着月光走了进来。“这么晚了,怎么不掌灯?”说着,他款步走向她,“不过,本公子也不太喜欢掌灯。”
吴婉君不语,看着他走向自己。
“怎么?愿意跟着我了?”张榕一抹坏笑,单手支着她身后的窗台。
吴婉君欠了欠身,道:“不,我来,是为了送你一样东西。”
她从袖口中缓缓抽出那玉色簪子,紧紧握在手心。
张榕轻轻挑眉,俯身闻了闻她身上的味道,“哦?是何物?难道,是你吗?”
吴婉君摇了摇头,“不。”说着,她迅速将玉簪子插入他的胸口,“送你去死!”
不想,张榕的力气比她大了好多,他向后退了几步,马上甩开了她,然后将双手紧紧掐住她那细白的脖颈,道,“你还没那资格。”
他说着,力气越来越大,过了半晌,待她在他手中完全无法动弹之后,他才轻轻将她放下。
他一把取出胸口沾着血的簪子,将它别在了她的发髻之中,“你这又是何必?”
突然,一个身影窜入客房,夜黑风高,屋内并未掌灯,仅仅凭着月光,他并未看清那人的模样,那人用凳子将他击晕,而后抱着地上的吴婉君,往屋外奔去。
连续跑了十几里地,完全虚脱的他,才舍得将她放下,月光下的她那般洁白美好,就如同初见她的模样,美丽地就像天上的仙女一般。
她在他面前永远都是那般的温柔,往日她的音容笑貌犹在他的耳畔轻轻围绕,许久都未散去。
他摇了摇怀中早已断气多时的她,他希望这不是他见她的最后一面。
可是,事实却如此的残酷,她早已香消玉殒。
“你为何这般傻?”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一手捂住自己的脸庞,一手抚了抚她留有余温的脸颊。
或许只有此刻,他与她的距离才能如此靠近。
可是,他宁愿远远看着她。
只要,她还活着。
他将她抱回临汾县时,早已是第二日的午后。
满身狼狈的他将她放到床边的那一瞬,便晕厥了过去。
他听不到刘向龙的叫声,更听不到吴寅那惨绝人寰的哭声,他嘴角微微一笑,如若自己这般随她而去,那也是好的。
不知不觉,已过了数日,阿九在迷迷糊糊中醒了过来。
当他第一眼睁开看到的还是这个世界的时候,莫名地突然开始失望了起来。他宁愿一睡不醒。
他轻轻地下床,打开门,往灵堂走去。
灵堂门前,吴寅正拿着手中的遣调令默默地抹着眼泪。
“大人。”
阿九上前,问道。
吴寅收好手中的调遣令,拍拍他的肩膀,道:“阿九,谢谢你。要不是你跟在她后面,我们或许连婉君的尸首都找不到。”
“大人,小姐对阿九有天大的恩德,我理应要保护她的,只是……”阿九低下头,“阿九没用。”
“无妨。”吴寅重拾心情,“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到这种地步,朝廷对我颁布了调遣令,让我去柳县单任县令。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阿九沉默了半晌,道:“我想留在这里。”
“好吧,我也不为难你了,希望你与向龙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向龙是个老实人,我怕他做傻事。”
“刘大哥也不随大人而去吗?”
吴寅叹了口气,“不,他打算留下来陪着婉君。”
“大人,阿九有个请求。”
“什么事?”
“阿九不想呆在衙门里做衙役了。”
“好,从今日起,你便是自由之身了。”说着,吴寅便转身,向远处走去。
阿九也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去灵堂,不想见她,不想见她的他。他知道,她的心中是有人的,但是那人并不是他阿九,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只要在远处,默默的守护着就是了。
半年过去了,他在临汾县的街上游荡了好久,他似乎回到了他当初的模样,衣衫褴褛,身材瘦小,总是被人欺负。
这一日,他与往日一样在街上走着,突然,一阵鞭炮声在他身边响了起来,使他吓了一跳,他抬头看去,门前一个女子正向门外的各路客人作着揖。
那个久违的笑容,突然打动了他心中的某处,他上前乞求,那女子竟将他请进客栈。
那女子对他说道,“你有没有兴趣在我们客栈做事?我们客栈刚刚开张,正缺人手。”
他默默的吃着手中的馒头,直直地盯着她,她的笑容依旧灿烂,而他,早已不是当初的他了。